王鼎鈞:人生似江河奔流,悲欣皆為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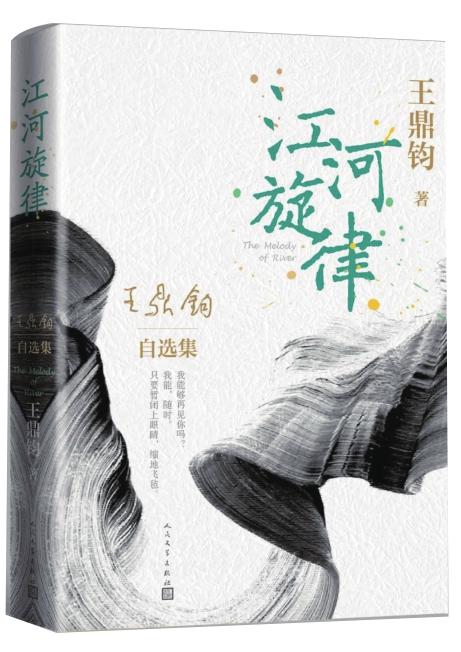
或許你曾聽說過王鼎鈞的“人生四部曲”,聽他用“一代中國人的眼睛”歷抗戰艱苦,看兩岸相隔,述人生悲苦;或許你也曾聽過他自命“聆聽哭聲的捕蝶人”,在黑白人世捕捉華美幻影,寫下《碎琉璃》《情人眼》《左心房漩渦》;或許你也曾聽過他在黑夜回顧往昔,在人心不古中祈望時間與上帝,寫下《活到老真好》《黑暗圣經》……
他的文字,氣質與沈從文最相契合,辭工旨豐,慧美豐贍。他是文學的赤子,膜拜故鄉,頂禮美善。他已是耄耋,對青年寄予厚望。所以,著名作家韓少功才說:如果有青年要學寫散文,我總是推薦中國臺灣散文一哥王鼎鈞。《那樹》《腳印》《活到老,真好》等堪為傳世經典,其積學靜水深流,其性情山明水秀,其才華排山倒海雷霆萬鈞,可讀得我一再目瞪口呆。
所以,與他并稱華人散文雙子星座的余光中才會說:海外作家鼎盛,風格多般,其旅外尤久而創作不衰者,詩人首推楊牧,散文家首推王鼎鈞。
這一本最新的王鼎鈞自選集,集合了他心儀的名篇,也表達了他溫柔的心緒。他說:大江東去,淘盡多少錦心繡口,我臨江打撈,這些,希望能為您留下。
留下什么呢?留下“人生似江河奔流,悲欣皆為序曲”,留下“縱使人間失格,愛與美仍是智慧”,留下“我的心是磁鐵,你的心是一塊鐵。有一天,你的心碎了,我把你的心一小塊一小塊吸過來,再重新組好。”
人啊人,人字只寫兩條腿。左看像門,右看像山,另有一說像倒置的漏斗,總之站得牢。人為萬物之“零”,符號十分簡單,人字只有兩畫,你看馬牛羊雞犬豕是多少畫!門供出入,人分內外;山有陰陽,人感炎涼;漏斗倒置,天地否極,看誰來撥亂反正旋轉乾坤。啊,人啊人。
這幾天我一直看他們幾個人的照片。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們!也許我的律師會說,你只是找到了他們的照片而已。我那以攝影師成名的朋友也許說,你只是找到了底片感光顯影定影放大沖洗而已。我那寫詩的朋友也許說,你只是見到一蝶,拾起一片花瓣而已。可是我要看,我更要看一生一世,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窮通榮辱,看他化蝶飛來,成一瓣落花飄下。看他縮小面積,壓去體積,濾盡過程,排除變化,成為案頭掌上之永恒。
看他們又是一場粉墨鑼鼓。看他們像看那場同樂晚會。看野地里豎起的柱子,看柱間連成橫梁,鋪上木板,看人在木板上捉弄世界。忽然眼前出現一個人,從未見過,完全陌生。沒有誰戴這樣的呢帽、眼鏡,留這樣的胡子,沒有誰站得這樣矜持,等他露齒一笑,那排牙使你恍然大悟,你馬上把他的面貌糾正了:這星期不是輪到他當采買管伙食嗎!你看又來一個人,老了,腰彎著,壽眉半白,瞇著眼東看西看,皮膚夠黑,臉上手上卻還有那么清楚的黑斑。這個人?難猜。看他一時疏忽睜大了眼睛,那烏溜溜的黑眼珠朝臺下一轉,哈哈,這家伙去年跟我同班!那次看表演如同一個預言,今天我看這些照片,從眉宇里搜尋真身,于今仿佛猶昔。只是這一次他們永不卸妝,他們看我料亦如是!
看來看去,想來想去,翻來覆去,死來活去。四十年前的留不住,四十年后的擋不住。人啊人,人字還是照寫,可是由瓶到酒都換了。人還是出出進進,上上下下,冷冷熱熱,顛顛倒倒。唉,可惜顛顛倒倒!小說家辛克來路易士六十大慶時,新聞記者請他發表生日感言,他說他心里有一個問題不明白,在六歲時就不明白,到了六十歲還不明白,什么問題呢?那就是:世界上為什么有窮人有富人?唉,我不是辛克來,我也有一個問題從六歲迷惑到六十歲,那是世界上為什么有好人有壞人?這問題你也不能解答。我們都有所不能,握住火把,握不住光;握住手,握不住情,不能掃起月色、揭下虹,不能將“酒窩”一飲而盡,我們都不能使獸變人。
但是據說人類可以帶著獸的血統和獸的性格,隱隱約約有獸的長長短短。人類征服洪荒,把野獸逼向死角,自己扮演虎豹蛇蝎兔狐豬狗。人為萬物之“伶”。袍笏不能保證文明,神話不能保證因果。十年一難,百年一劫,劫來了,所有的偉大都急速縮小,我們用兩只手恭恭敬敬捧著的東西都掉下來被眾人踐踏成泥。平時都說槐花是吊死鬼的舌頭,相誡不可從槐下走過,但饑饉之年大家搶著吃槐花,吃槐葉,吃槐樹皮。有一種蜘蛛,出生以后就把自己的母親吃掉。母獐相反,它如果聞見幼獐身上有陌生的氣味,為了安全,就把自己的親生兒女丟棄了。斷腕滅親也是空,賀蘭山上的獵人還是可以捕獐為生,蜘蛛為了自己的發育連母親也吃,到頭來仍是一只蜘蛛,也沒有長成老虎。
誰是虎而冠者?他們不是,我不是,料想你也不是。你說“我很累”,哪里是虎嘯?你寫的柳公權,“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昨夜還掛在我的客廳里。世上豈有莫愁湖,或有莫愁虎。你說“我很疲倦”,疲倦也是一種愁。你煩的是什么,憂的是什么,你遺忘了沒有,升華了沒有。李白的呻吟怎么到現在還裊裊不絕,該死的不朽。
當我處心積慮東尋西覓時,你沒有一句話贊成,沒有一句話幫助,你也不反對不禁止,只說“我很累”,這是你的風格。而我,我對言外之意充耳不聞,在你冷淡的眼神下興高采烈,這是我的風格。歷史是打碎了的瓷瓶,碎片由考古學家收拾,這掃地的工作么,你也懶得了。其實我也累,他們都很累。站在紅漆漆過的大地上,邁一步怕留下腳印,扶一下怕留下的指紋,空氣里充滿了油漆未干的辛辣,喘口大氣也難,那日子是會在肌肉里累積酸素的。大家都累了,像是童年時期的某種游戲一般,大家擠在一起,纏成一團,直到每個人用盡了力氣,睡在地上癱成一堆。這個游戲簡直是今生今世漫長生涯的縮影。真奇怪,童年做過的某些事情,往往是以后重大遭際的象征。
我想我們都太累,都還沒有恢復,完全恢復需要很長的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們想到夸父,不累;想到吳剛,不累;想到季子掛劍,不累。直到有一天,看見小花的微笑,不累;想起提琴的弦繃得那樣緊,不累;聽見瀑布晝夜奔流,不累。直到有一天我們能尊重含羞草,同情鴕鳥,贊美出土的化石,包容所有的上帝。
聚有時,散有時。由散的時代到聚的時代漫長,有涯。把葉子吹離枝頭的,是風,把葉子圍攏在樹根四周的,也是風。把花瓣從陌上沖走的,是水,把花瓣一個挨一個鋪滿湖面的,也是水。貧血的月,高血壓的太陽,癡肥的山,生銹的城,俱往矣。不要諷刺生命,當心生命會反諷你。人啊人,我要看人,給我更多的人看,給我標準化的人,給我異化的人,給我可愛的人,可恨的人,以及愛恨難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人。
(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