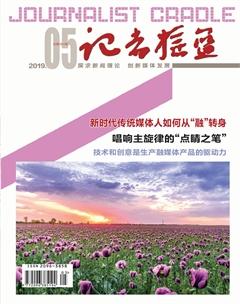唱響主旋律的“點(diǎn)睛之筆”
2019-08-01 08:10:17
記者搖籃 2019年5期
關(guān)鍵詞:電視新聞傳統(tǒng)媒體
移動(dòng)時(shí)代閱讀的興起、手機(jī)攝影功能的強(qiáng)大和信息發(fā)布渠道的擴(kuò)張,使得新聞攝影從理念到生產(chǎn)傳播方式都發(fā)生了蛻變。新聞與圖片正在向一個(gè)全新的關(guān)系轉(zhuǎn)型,圖片在紙媒報(bào)道中的地位將變得日益重要,越來越多的電視新聞報(bào)道也引入了大量的靜態(tài)圖片。
面對(duì)新媒體的沖擊,傳統(tǒng)媒體的視覺部門和專業(yè)攝影記者,既要堅(jiān)守為時(shí)代留影、為歷史存檔、弘揚(yáng)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的社會(huì)責(zé)任,又要主動(dòng)了解新趨勢,掌握新技術(shù),參與移動(dòng)媒介上的影響力再造。讓傳統(tǒng)媒體攝影功能在新時(shí)期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唱響主旋律的“點(diǎn)睛之筆”。
猜你喜歡
新聞傳播(2018年2期)2018-12-07 00:56:26
新聞傳播(2018年5期)2018-05-30 07:02:58
傳媒評(píng)論(2018年12期)2018-03-21 07:51:52
傳媒評(píng)論(2017年3期)2017-06-13 09:18:10
新聞傳播(2016年9期)2016-09-26 12:20:15
新聞傳播(2016年2期)2016-07-12 10:52:13
新聞傳播(2016年1期)2016-07-12 09:24:44
新聞傳播(2016年11期)2016-07-10 12:04:01
新聞傳播(2015年6期)2015-07-18 11:13:15
新聞傳播(2015年5期)2015-07-18 11: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