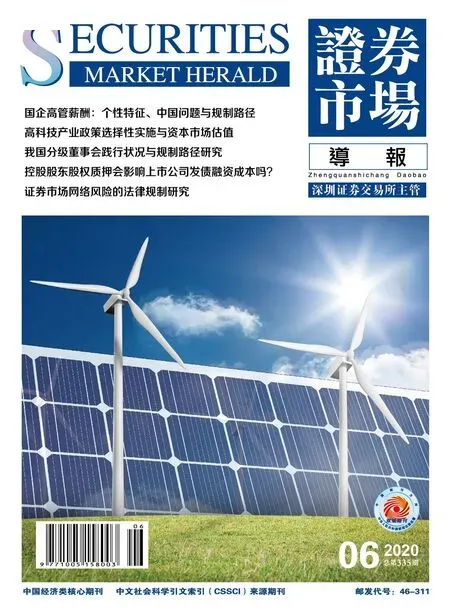我國分級董事會踐行狀況與規制路徑研究
林少偉 解軍
(1.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2.西南政法大學商會法律研究院,重慶 401120;)
一、引言
分級董事會(classified board),又稱交錯董事會(staggered board)、分類董事會,是指在公司董事會中,通過分級、分批安排的方式,交錯更換任期屆滿的董事。具體而言,公司通常在章程中規定,將全體董事分成若干小組,每個小組董事人數大體相當并且任期相同,不同小組的任期不同,每年只需更換任期屆滿的董事,這種模式與美國參議院的選舉相類似。1《美國標準商事公司法》及《特拉華州普通公司法》均有關于此項制度的相關規定。在章程中設置每年只能更換部分董事的條款,不僅可以保持公司治理的穩定性,也可以通過巧妙的交錯任期設置,減緩意圖收購者取得董事會控制權的進程,進而延長收購方取得公司實質控制權的時間。而在此期間,收購方不僅需付出巨大的時間和金錢成本,目標公司管理層更可采取增發股份等方式稀釋收購方的控股比例,進而達到阻止其收購的目的,在事實上發揮反收購的效果。2
因此,分級董事會日益受到我國上市公司的青睞。特別是在“寶萬之爭”后,上市公司紛紛祭出五花八門的收購防御條款,其中既有屢試不爽的“金色降落傘”和絕對多數表決條款,也有本文所要討論的分級董事會。然而,相較于域外的成熟規定,我國目前對該條款的規定存在立法和監管標準的雙重缺失,尤其在“愛使章程之爭”后,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效力爭議不斷,不僅無益于收購市場的健康發展,更不利于監管機構的引導。事實上,我國學者對分級董事會的研究也較為少見,在為數不多的9篇相關論文中,有4篇是純粹從經濟學角度探討分級董事會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從法學角度研究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寥寥無幾。故此,本文通過梳理部分A股上市公司的章程,檢視現有上市公司關于分級董事會的設置條款,揭示分級董事會在我國的踐行狀態,并探析我國分級董事會面臨的挑戰與障礙,以探尋具有中國特色的分級董事會規制路徑。
二、分級董事會的適用現狀
誕生于美國19世紀60~70年代的分級董事會,最初只是為了維護公司治理的穩定性以及管理的連續性,因而美國很多州的法律都認可這一做法。隨著20世紀80年代敵意收購浪潮序幕的拉開,分級董事會“無心插柳柳成蔭”地被視為強有力的反收購機制之一。據學者統計,2002年美國2421家上市公司中就有59%的公司設置了分級董事會條款,其中在1992年至1999年之間設置分級董事會的公司比例迅速增加,由34%增加到82%。3我國分級董事會條款首次出現于1998年“大港油田收購愛使股份”的過程中,大港油田通過在二級市場收購上海愛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使公司)的股份,意圖借殼上市,但就在其準備控制愛使公司董事會時,愛使公司通過修改章程對其設置阻礙,修改后的章程第67條對董事提名和改選均設置了嚴苛的門檻,其中對董事換屆改選人數的限制引起巨大爭議,最后證監會以行政介入的方式令愛使公司對該條章程進行了修改,大港油田因此取得董事會的控制權。“愛使章程之爭”使分級董事會開始進入國人視野,對其合法性的質疑之聲也由此發生。
時至今日,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對分級董事會的合法性進行明確界定,但實踐中,已有類似于域外分級董事會的條款引入上市公司章程中。因此,本文對深滬兩市主板上市公司章程設置的分級董事會條款進行逐一考察,以期挖掘當中存在的問題,并尋找可能的規制路徑。
(一)深滬主板公司設置分級董事會的數據分析
截至2019年7月20日,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深市)主板上市公司共473家,其中在章程中引入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有24家,所占比例為5.07%;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滬市)主板上市公司共1471家,有36家上市公司規定了分級董事會條款,所占比例為2.45%;深滬兩市主板上市公司共1944家,總共有60家上市公司規定了分級董事會條款,所占比例為總樣本的3.09%(見表1)。相比于在2002年分級董事會條款設置比例就高達59%的美國上市公司而言,中國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上市公司數量顯然偏少,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相較于反收購歷史悠久且實戰經驗豐富的美國,中國并購市場的發展時間較短,實踐經驗不足,且各方面制度也相對不完備;二是我國目前對上市公司設置分級董事會等反收購條款的合法性態度曖昧、立場不明,公司采取分級董事會需面臨不確定的法律風險。
此外,相較于深交所發布的《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況報告》中44家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主板公司而言,六年間有20家上市公司廢除了相關條款,采納分級董事會的上市公司比例也由原先的9.4%減少為5.07%。4有學者在2017年5月對深滬兩市主板上市公司中的分級董事會條款進行實證考察時,在總共1663家上市公司(其中深市449家、滬市1214家)中,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公司共有97家(其中深市32家、滬市65家),占所有主板上市公司的5.83%。5由此可見,近三年內,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公司急速減少,比例下降了近一半。究其原因,在2015年“寶萬之爭”后,隨著并購市場的一度活躍,600多家上市公司為預防惡意收購紛紛設置反收購條款6,其中就包括分級董事會條款,但這些反收購條款的引入,表現出過度防御、過于保護管理層的傾向,有侵害中小股東合法權益之嫌。故2016年深交所和上交所向很多設置反收購條款的公司發送問詢函或關注函7,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投服中心)也在2018年年初集中向北京238家上市公司發送了股東建議函,要求其對章程中侵害中小股東權益的條款進行修改,其中限制股東改選比例的14家公司赫然在列8,從而出現了主板上市公司紛紛刪除分級董事會條款,使其設置比例下降過半的情形。然而監管機構并未對此種條款的合法性以及設置標準作出明確認定,因此仍有一些上市公司設置了分級董事會條款。

表1 深滬兩市主板公司分級董事會條款規定情況
(二)分級董事會條款的設置內容
1.董事改選時間的限制
雖然60家采用分級董事會條款的上市公司大都采用直接限制董事改選人數或比例的形式,但章程中對于限制董事改選數量的時間規定較為混亂,主要有五種類型。第一種是限制董事換屆時的改選數量9,共8家,占比13.3%;第二種是在董事任期內限制改選數量10,共10家,占比16.7%;第三種是對換屆時以及任期內的董事改選數量都分別加以限制11,共4家,占比6.7%;第四種是不區分董事任期是否屆滿對改選數量進行限制12,共28家,占比46.7%;第五種則是在特定的情況下才對董事改選的數量進行限制13,共7家,占比11.7%。
2.董事改選比例的限制
在60家設置分級董事會的上市公司中,除了3家公司采取直接限制改選人數的方式外14,其余公司都采用限制董事改選比例的方式。在具體改選比例的章程規定中,限制人數最高的比例為全部董事人數的1/215;限制人數最低的比例為董事總人數的1/716;其余限制比例還有1/3、1/4和1/5,其中大部分公司都采用1/3的比例限制。在對換屆時與任期內的董事改選數量都加以限制的上市公司中,大部分也對兩種時間改選董事的比例進行了區分,且在換屆時的限制改選比例都高于非換屆時的限制改選比例。17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對于分級董事會條款的規定除了具有限制董事改選的比例這一共性外,其他方面均呈現較強的個性化色彩,無論是在限制董事改選的比例、時間還是內容上都存在較大差異。
三、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本土化困境
我國雖有部分上市公司設置了分級董事會條款,但在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本土化過程中,卻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困境,不僅其合法性遭受監管機關和投資者的質疑,其與美國傳統的分級董事會條款也存在迥異之處,可謂是“貌合神離”。此外,在其他相關配套制度缺失的情況下,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還可能會損害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故此,分級董事會條款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面臨一定的困境與挑戰。
(一)效力認定體系的缺失
1.立法層面效力規范缺位
我國《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法律規范雖然或多或少有涉及反收購措施的相關指引或規范,但大多數條款過于原則化、操作性不強,難以直接指導實踐。比如我國《公司法》第五條及第二十二條對反收購措施不得違反法律法規作出了原則性規定,第一百四十七條也規定了董事的勤勉義務和忠實義務,但頗為遺憾的是,《公司法》并未規定董事在反收購過程中具體義務的履行標準。18《證券法》第四章對上市公司的收購問題進行了規制,但當中并未涉及反收購的相關問題,同樣不具有針對性。作為專門規范收購市場的規范性文本,《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針對收購行為進行了詳細的規制,其中針對反收購措施的規制僅有第八條關于目標公司董事忠實和勤勉義務的規定,第三十三條對目標公司董事會在收購人作出提示直到要約收購完成前的行為作出的限制性規定,以及第八十條董事違反信義義務的責任和涉及控制權的條款違反法律法規由證監會責令改正的規定。
這些涉及不同法律文件的反收購規定,主要側重于董事義務,但在董事義務的具體內容及判斷違反董事義務的標準等方面,仍然存在操作性較低的弊端,并對反收購行為抱有一種“警惕”的限制心態。19同時,對于分級董事會條款等反收購機制的效力認定也存在缺失。這就導致上市公司章程中分級董事會相關條款不僅雜亂無章、形形色色,而且存在難以確定有效與否的法律風險,進而導致公司可能因此類條款的被迫取消而喪失反收購的抵御能力。反收購作為一種實踐性的行動,具有較高的自由度,法律一般不宜作正面性規定,而應采取反面性的做法加以規制。20故此,我國應當在立法中對分級董事會的效力認定標準予以明確,以回應現實需求。
2.監管主體定位的模糊
(1)證監會
證監會作為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根據《證券法》第七條的規定對全國證券市場進行統一的監督管理,其中也包括對反收購行為的監管。但在證監會具體的監管文件中,監管面向的主要是證券收購市場中的違法行為,甚少對反收購行為予以關注,更無對分級董事會等類似反收購措施予以定性定調。著名的“愛使章程”反收購事件中,在雙方針對愛使公司修改后的章程第六十七條的合法性爭執不休時,大港油田以此條款違法為由通過臨時提案的方式要求證監會對其章程行使檢查權21,其法律依據是《上市公司檢查制度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款,但證監會并沒有對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效力作出明確判定,而只是通過發函的形式要求愛使公司對其章程第六十七條進行修改。由此可見,證監會在缺乏法律指引的情況下,對于分級董事會條款的監管態度模糊,對相關條款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如何合法有效并沒有予以判定。
(2)證券交易所
證券交易所在我國作為非營利性質的自律管理法人,不同于證監會具有的法定行政管理職能,其主要是針對證券市場中的股票交易行為,通過《證券法》及相關部門規章的授權進行監督管理,并有權采取紀律處分措施和自律監管措施。22但在反收購市場中,證券交易所的監管職責和監管邊界都不甚明確,這導致其是否有權判定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效力存在不確定性,進而導致其在市場監管活動中“畏手畏腳”。此外,監管手段過于簡單化也是交易所的監管問題所在。在60家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上市公司中,本文發現,上交所和深交所通常是以“詢問函”或“關注函”的形式進行監管,要求上市公司對于其章程中設置的分級董事會條款是否侵害股東的基本權利以及做出此種設置的理由進行說明,除此之外,并沒有其他的“監管手段”或“溝通渠道”。在這樣模糊不清的“監管”模式下,有些公司出于種種顧慮最終刪除了相關條款,有些公司則“勇敢無畏”地不予理會,仍然保留此類條款。換而言之,交易所的“詢問”或“關注”,并沒有解決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效力問題,相反,該類條款最終去留的決定權始終掌握在上市公司手中。
(3)法院
法庭提供的救濟是證券市場執法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23司法介入在反收購市場中具有與行政監管相當的作用,目前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分級董事會條款合法性之爭的實踐中,并沒有最終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例可循。例如在大港油田與愛使公司的收購事件中,雖然兩家公司對于分級董事會條款合法性的爭論僵持不下,但在各方的協調下最終以愛使公司修改章程結束。寶能系旗下的前海人壽與一致行動人鉅盛華股份有限公司對南玻A發起收購行動時,南玻A企圖通過修改章程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等措施反收購,但雙方所達成的修改章程的決議也同樣沒有進入司法程序24,這也導致了法院作為司法裁判機構在反收購措施的效力認定方面有所缺位。
(4)投服中心
經中國證監會批準設立并直接管理的金融類公益機構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以維護中小股東利益為目的,通過持股行權制度代表中小股東行使表決權、質詢權等,以此來參與和監督公司治理。因此,投服中心在反收購措施的合法性監管方面也可積極作為。如投服中心2018年向北京二百多家上市公司發送股東建議函,要求這些公司對章程中侵害股東權益的條款進行修改,并判定其中限制董事改選比例的分級董事會條款違法違規。25投服中心雖然判定了分級董事會條款不合法,但因其行權的合法性存疑,在實踐中屢次被上市公司無視和質疑。究其原因,一方面,其監管行權的主體資格并沒有得到《證券法》等相關法律的授權,僅在證監會《持股行權試點方案》中有規定;另一方面,我國股權結構較為集中,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僅持有最低限度的100股,在公司治理上很難有話語權。26在缺乏法定的行權資格和行權依據的情況下,投服中心的地位較為尷尬,因而其監督上市公司治理的功能也收效甚微。
(二)本土與域外制度的“貌合神離”
我國上市公司設置的分級董事會條款,表面上似乎借鑒了域外的分級董事會制度,具有“貌合”之觀;但通過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其與域外制度存在某種“神離”之別。美國的分級董事會一般根據董事的不同任期,將之分為若干小組,每年只改選任期屆滿的董事。依此而言,每年改選哪些董事、改選多少名董事均是確定的。此種選任模式也完全符合我國《公司法》第四十五條關于董事任期的規定。然而,我國上市公司的分級董事會條款都是直接限制改選董事的比例和數量,對于改選董事的人選并不確定,尤其在換屆選舉時通過股東大會改選董事,股東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投票選舉時所有的董事改選幾率相同,對于如何保證按照條款規定的比例改選董事并無詳細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操作。同時,由于其直接對股東選任管理者的權利進行了數量上的限制,因此其效力在學界引起巨大爭議,導致合法性存疑。
在改選董事的時間上,域外傳統的分級董事會條款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限制改選董事的時間,即分別在每組董事任期屆滿時進行改選,保證每年都只有部分董事改選。我國由于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引,對于改選時間的規定五花八門,主要類型包括限制換屆時的改選數量、在任期內限制每年的董事改選數量、不區分換屆與否限制每年的改選數量、對一段時間內的董事改選數量進行限制以及限制特定情況下(例如惡意收購、公司控制權轉移)董事的改選數量,因而其中某些限制改選的時間在實踐中沒有可操作性且效力存疑。例如金地集團(600383)章程第九十六條規定,“為保持公司重大經營政策的連續性,董事會換屆時所更換、增加的董事數額總計不得超過上屆董事會董事名額的三分之一”,此種在董事任期屆滿時限制換屆的董事改選數量在實踐中幾乎無法操作。在我國,董事任期三年期滿后召開股東大會進行換屆選舉所有董事,而在收購方取得控股股東地位后,按照資本多數決的原則,其可以輕而易舉地使得前任董事“大換血”,即使在采取累積投票制的公司,也只能保證部分董事不被改選,很難達到章程規定的1/3要求。另外很多公司在設置分級董事條款時考慮不全面,僅僅規定了每年更換的比例。例如浙江富潤(600070)章程第一百零五條關于限制董事改選僅規定了“董事會每年更換和改選的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數的三分之一”,并沒有考慮到發生特殊情況時該怎樣操作。假如在董事自動辭職或者董事違反法律、法規及章程被解除職務后董事人數明顯不足時,即使只更換限制的人數也仍然達不到章程規定的最低人數,此時該條款的效力顯然存疑。
在相關配套制度上,傳統的分級董事會條款在規定每年改選規定董事以外,還加以有關股東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限定,防止收購方取得公司控股地位后通過股東大會罷免董事27,以達到反收購的效果。尤其是美國所采用的“董事會中心主義”的公司治理模式,在章程條款修改方面大多將權力賦予董事會28,從而可以很好地避免收購方通過召開股東大會修改相應的分級董事會條款。反觀本土化后的分級董事會條款,由于我國《公司法》并沒有關于股東不可隨意罷免董事的相關規定,因此一些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章程往往沒有與之相配合的“股東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規定,這就使得收購方有了“可乘之機”,并可借此在實質上推翻該條款。我國《公司法》第一百條第三款規定了單獨或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請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且我國股東有權選任非由職工代表擔任的董事,由此一旦收購方成為公司大股東后,其很有可能通過請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方式將有關限制董事改選數量的條款刪除,隨后在股東大會上選舉出自己的董事從而達到入主目標公司董事會的目的,由此,相關配套制度的缺位,會使得分級董事會的反收購效果大打折扣。
(三)對累積投票制的抑制
起源于美國的累積投票制,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或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選董事和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不同于直接投票的方式,累積投票制源自公司民主的理論29,目的是使小股東也有機會選任董事,防止大股東利用持股優勢長期把持董事會。我國《公司法》第一百零五條和《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三十一條對累積投票制作出了規定,以許可立法的形式賦予了股份有限公司在選舉董事時選擇適用的權利,當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的控股比達到30%時才強制采用累積投票制。而公司是否采用累積投票制,一般是以“普通決議”的方式予以定奪。本文發現,所有設置分級董事會的上市公司均無一例外采納了累積投票制,然而,分級董事會與累積投票制之間存在某種可能勢不兩立的矛盾,即二者的同時施行可能會損害累積投票制的原本功能與效果。此外,累積投票制適用于至少有兩名以上董事需要改選的情況,如果分級董事會條款規定每次只改選少于兩名董事,那么中小股東的權利更是大受損失30,至此,累積投票制已名存實亡,淪為公司裝飾門面的花瓶。
四、分級董事會之論爭
雖然不少國家或地區采納或承認分級董事會,但該制度本身仍有不少爭議,特別是隨著股東積極主義的崛起,將分級董事會寫入章程的提案也未必能順利獲得股東會通過,分級董事會條款是否具有存在的價值存疑。此外,沒有明確采納該制度的國家對此則存有效力之爭,既有認為其不合法而不具有效力之說,也有認為其并不違法因而具有法律效力之理。
(一)制度之論
反對分級董事會的觀點主要基于管理層自保說,即認為分級董事會只是管理層維護自身私人利益的輔助手段而已,因為股權結構分散的公司容易出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此種分離使得持有公司少量股份的管理層不足以全心全意為公司利益服務,因此與股東利益產生沖突。而分級董事會條款的設置使得目標公司管理層以犧牲股東的利益作為代價,通過談判使自身利益最大化。31已有實證研究證明,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上升,公司業績呈現先上漲后下降的趨勢,原因在于,當管理層的持股比例達到某一水平而不再上漲時,將逐步減少考慮公司利益,分級董事會的設置使得管理層獲得與收購方談判的籌碼,而逐利性使管理層談判時會以自身利益出發,這不僅會增加收購方的收購成本,也會損傷目標公司股東的交易機會。32有學者基于此理論進一步提出,如果市場已反映出目標公司的管理層經營不善、資產運用效率低下,則收購方以溢價提出收購表明其有能力通過收購改善公司管理經營,由此不僅能使目標公司股東獲得溢價,也能使違反信義義務的管理層得以替換并受到懲戒,因此,分級董事會作為反收購措施并不利于整個社會效益的提升。33
贊同設置分級董事會的則以股東利益說為代表。該理論認為類似分級董事會的反收購措施一方面能夠將分散在非理性、無知股東手中的對公司的管理權集中起來,以便更高效地管理公司;另一方面在面對外部惡意收購威脅的同時,分級董事會能夠提高管理層的議價能力,以此對潛在低價收購者施加壓力,為股東爭取溢價收益。34再者,有學者認為分級董事會可維護公司治理的穩定性,通過延長董事的任期,使之與公司建立長時間的合作關系,有利于公司經營政策的長期施行,并激勵管理層為公司的長遠利益考慮。35此外,利益相關者理論也為分級董事會的設置提供了理論支撐,認為該設置不僅能夠使股東在收購交易中獲得溢價,還可以克服股東的短視,進而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36
從不同角度而言,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的觀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從實證研究來看,分級董事會同樣存在爭議之處。有學者利用1996~2000年五年間美國的敵意收購數據分析了分級董事會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結果顯示雖然分級董事會確實具有強大的反收購力量,但數據表明分級董事會的有效性降低了目標股東的回報。37然而,更早的研究則呈現出另一番風景,有學者對1979~1985年649家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公司進行了研究,通過綜合分析其資本結構、營利能力和支出成本等因素判斷分級董事會對公司價值的影響,結果顯示分級董事會與公司的價值成正相關,符合股東的利益。38最新的研究與之前的又不一致,Cremers et al.將公司價值與采用(或取消)分級董事會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分級董事會并沒有明顯對公司產生有益或有害的結果,或者說,分級董事會對公司的影響應具體而論,不能一概斷之。39綜上所述,無論是從理論依據或施行效果來看,對分級董事會這一制度存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至于是否采納或設置則需依據具體情況判斷。
(二)效力之爭
我國公司法并沒有對分級董事會作出明確規定,但根據《公司法》第45條的規定,公司可以在三年的范疇內自行規定董事任期,且無需任期相同。40因此,如果只是每年改選任期屆滿的董事并沒有違反我國法律的規定,不存在效力之爭。41但我國上市公司所設置的分級董事會條款與域外傳統的分級董事會規定存在較大差異,主要是以直接限制董事改選為特征,因此可能涉嫌違反《公司法》的相關規定以及否認股東選舉和罷免董事的權利,這也是分級董事會在我國存在巨大爭議的原因。根據艾森伯格的觀點,公司法規范可分為結構性規則、分配性規則和信義性規則三種。42結構性規則和信義性規則作為公眾公司的核心規則,應將其認定為強制性規范。以此而言,股東選舉董事的權利作為結構性規則,也歸入強制性規范范疇,公司章程不得隨意加以限制,而分級董事會恰恰是不當地限制了這一股東權利。
本文認為,在我國沒有對分級董事會作出明確立法表態的情況下,判斷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效力應當采取“基本標準”與“輔助標準”相結合的審查方法。具言之,審查我國分級董事會的效力問題應當解決兩大要素:一是識別判斷分級董事會是否違反我國公司法強制性規范這一基本標準,如有違反則認定無效;二是在不違反或者難以識別的情況下,考慮該條款是否遵循《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八條指引的董事信義義務以及是否符合公司及股東的利益等,以作為輔助標準。只有通過這種全方位審查的綜合標準判斷,才能更為全面地探析分級董事會的效力問題。
第一,就基本標準而言,關于公司法規范屬性的類別劃分存在多種學說43,但無論哪種分類,分級董事會所涉及的股東對董事的選舉,不僅歸屬于公司的結構性規則,也屬于(上市公司)有關權力分配的普通規則,因此屬于公司法強制性規范無疑。而我國《公司法》僅在第四十五條指出“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規定,但每屆任期不得超過三年。董事任期屆滿,連選可以連任”。44根據這一規定,傳統意義上的分級董事會每年只改選任期屆滿的董事,并沒有違反上述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合法無疑。而對于我國上市公司以直接限制董事改選比例為主要內容的分級董事會條款,本文認為,該條款同樣沒有剝奪股東會選舉和更換董事的權利,只不過是對這一權利施加了一定限制,這種限制恰恰是股東會通過行使其本身的決策權修改公司章程所作出的決定,是股東自由意志的體現。根據艾森伯格的分類理論,純粹對股東改選董事的權利予以限制(但不剝奪)并不意味著是對“股東選舉董事”這一強制性規范的違反,因此也不能推斷分級董事會條款因違反強制性規范而無效。
第二,在分級董事會條款沒有違反強制性規范(或難以識別)的情況下,有必要拷問其是否遵循董事信義義務并符合公司及股東的利益等。首先,分級董事會條款規定每年只能改選部分董事,并沒有剝奪股東罷免不稱職董事的權利,由此也依然能夠敦促董事在任職期間認真履行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并切實為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服務。因此,分級董事會并沒有違反董事信義義務。此外,從公司整體利益和股東利益的角度而言,分級董事會能夠使有經驗的董事得以留任,協助新任董事了解公司事務45,進而可以避免董事潛在的短視近利,激勵其制定有利于公司長遠發展的計劃,也可使公司在經驗傳承中穩步發展。其次,分級董事會條款延緩了收購方取得董事會控制權的時間,在此期間,收購方為降低收購成本必然要主動和目標公司董事會進行談判,借助分級董事會條款,董事會擁有較大的談判優勢,可以借此提高收購價格,進而獲得最大收購溢價。46最后,由于部分股東不可避免地存在短視主義,在面對收購活動時,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由于對公司信息掌握不全面,不能對其真正目的作出判斷,也很難有效識別其中的不利因素,此時分級董事會條款給予目標公司董事會充足時間對收購行為作出判定,并與公司股東進行溝通,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維護公司的整體利益。有鑒于此,無論域外傳統的分級董事會制度,或是本土化后以直接限制董事改選比例為主要內容的條款,其法律效力應當予以肯定。
五、分級董事會本土化的構建路徑
在我國部分上市公司已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背景下,如何克服分級董事會本土化的種種困境,并使之發揮應有作用,無疑值得深思。本文認為,應當細化配套制度,以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分級董事會制度。
(一)明確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效力審查標準
分級董事會條款是否有效之所以富有爭議,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對此缺乏正式的效力性回應及判斷標準。故此,應在立法中明確分級董事會的效力審查標準,以此作為監管機構的法律指引。首先,可以借鑒美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的做法,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確分級董事會設置的標準模式,就直接限制董事改選數量的條款內容、改選的時間點等予以模板化的指引,以供公司在章程中自由選擇;其次,如公司在分級董事會條款法律指引以外作出相關配套規定,對于此種配套規定的效力審查應在法律中明確具體的審查標準,如前述的“基本標準”與“輔助標準”相結合的審查方法等。根據此種原則性的審查標準指引,監管機構及司法裁判機關可在具體條款審查中進行個案判定。
考慮到諸多上市公司在設置分級董事條款時一般均將“惡意收購”設定為此種條款的觸發條件,在相關法律上明確惡意收購的概念也關乎分級董事會條款的效力,以防止管理層利用“法無明文規定”的漏洞隨意以主觀標準判定惡意收購是否發生,進而觸發分級董事會條款故意排除“善意”收購。故此,本文認為,可將惡意收購行為與違法收購行為相結合,通過負面清單的方式列舉違法收購行為,以此為標準判定惡意收購行為,不僅能夠規避公司管理層的道德風險,也能有效維護股東及公司的整體利益,并隨著實踐中新情況的出現而不斷完善負面清單。
(二)提高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表決比例
根據我國《公司法》第四十三條和第一百零三條的規定,做出修改章程的決議需要經(出席會議)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相較于普通決議的過半數通過而言,修改章程的表決比例顯然要高得多。除非是在初始章程就規定分級董事會條款,否則該條款一般是通過修改章程而設置。由于初始章程是各發起人股東協商一致的產物,反映了發起人股東的共同意志,即便是后加入的新股東,也是在充分了解公司章程各項內容尤其是股東固有權利的基礎之上而選擇加入,因此在初始章程中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公司,不存在壓迫中小股東或不公平損害之說。而在通過后續修改章程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公司中,由于分級董事會是對股東選舉董事這一基礎性權利進行限制,從而改變其基礎權利的配置結構,因此在對是否設置這一條款進行表決時,實際上是股東對歸屬于自身固有權利是否選擇予以限制的表決,如果將之與普通的章程條款修改的表決程序等同,則不僅會在形式上危及股東的投資預期47,也容易導致我國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小股東愈發“淹沒”在大股東強勢的聲音中。有鑒于此,本文認為,應當提高設置限制股東改選董事權利條款的表決比例,以更好地維護中小股東的固有權利以及其加入公司時的預期利益。
(三)設立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規則
分級董事會條款通過限制董事改選的數量,在反收購時可以起到延長收購方控制目標公司董事會的時間,以此為目標公司取得最大利益爭取時間,由此產生反收購之效果。國外法律在明確分級董事會條款設置的具體模式時,考慮到收購方可以利用股東罷免董事的權利對此項措施進行反制,從而導致其喪失反收購效果,因此在相關法律中明確了“股東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規定。例如美國《特拉華州普通公司法》就規定一般情況下持有表決權過半數的股東可以罷免全部或部分董事,但在設置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公司中,則需要具有法定原因才能罷免董事48,而公司控制權轉移并不是股東罷免董事的法定理由。此種“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限制性規定,可有效避免收購方在獲得目標公司較多股權后通過股東大會隨意罷免董事,進而消解分級董事會的內生目標。只有確立“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規則,并與分級董事會條款相結合,才能延緩收購方入主目標公司董事會的時間,進而實現某種程度的反收購目的。
我國《公司法》刪除了此前舊版中“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規定,以此反映出我國立法不對股東能否隨意罷免董事設限;新修改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規定董事“可在任期屆滿前由股東大會解除其職務”,采用“可”這一表達實際上也是明確授權股東享有任意罷免董事的權利,雖然這并不禁止公司在章程中作出其他限制性規定。有鑒于此,分級董事會的本土化實現,宜增加沒有正當理由不得隨意罷免任期未屆滿董事的配套規定,且將公司控制權轉移排除于正當理由的范圍,以保證分級董事會條款的反收購效果。
(四)增加累積投票制的配套規定
累積投票制通過改變傳統的直接投票模式,將股東的每一股份與待選的管理者掛鉤,從而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少數股東對管理者的選任。然而,正如之前所述,假如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那么當董事改選同時采用分級董事會條款與累積投票制時,分級董事會中限制董事改選數量的條款將直接抑制累積投票制保護中小股東投票權的作用。一方面限制董事改選數量的增加會導致中小股東選舉董事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在累積投票制下所產生的董事也可能在分級董事會后期改選時因改選人數較少而容易落選,進而無法實現累積投票制保護中小股東的立法目的,導致分級董事會條款因侵害中小股東選舉董事的權利而無效。因此,在引入分級董事會條款時,還應考慮到解決此種沖突的配套規定。
本文認為,可借鑒《美國標準商事公司法》和《特拉華州公司法》的相關立法例,在相關法律中規定配套制度。比如對是否采用累積投票制的公司進行區分規定,在采用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的公司,若反對罷免累積投票制選出的董事的表決權足以選出該董事,那么除非一次改選全部董事或有正當理由足以罷免該董事,則該董事不得被罷免;在沒有采用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的公司,則采用沒有正當理由不得無故罷免董事的規定,以此最大限度地保護董事不被隨意罷免,進而保障分級董事會的實施效果。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司法》私人執行之檢視”(編號:17CFX072)、霍英東教育基金(編號:171079)]
注釋
1. See Dore G M. The Iowa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s staggered board requirement for public corporations: a hostile takeover of Iowa corporate law[J]. Drake Law Review, 2012, (60): 1.
2. 參見王建文, 范健. 論我國反收購條款的規制限度[J]. 河北法學, 2007, (7): 99.
3. See Bebchuk L, Coates J, Subramanian G. The powerful antitakeover force of staggered boards: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J]. Stanford Law Review, 2002, (54): 895-896.
4. 參見深交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2012年深市上市公司治理情況報告[R]. 深圳: 深圳證券交易所, 2013.
5. 參見曹清清. 我國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購條款法律規制研究[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 2018: 101-108.
6. 參見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 上市公司反收購章程不應超越法律[N]. 證券日報, 2017-05-27.
7. 例如山東金泰(600385)、伊利股份(600887)、諾德股份(600110)、雅化集團(002497)就分別于2016年收到了上交所或深交所的問詢函或關注函。
8. 參見新浪財經. 投服中心對北京238家公司發送股東建議函[N]. 中國證券報, 2018-02-23.
9. 例如東旭藍天(000040)章程第一百零一條規定:“董事換屆時,每次更換董事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人數的1/2”。
10. 例如中航資本(600705)章程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在對董事會不進行換屆選舉的股東大會和臨時股東大會,擬補選的董事會成員名額在原則上一年內不能超過三名(即不能超過1/3)”。
11. 例如方大集團(000055)章程第九十八條規定:“董事局任期屆滿前和董事局換屆時,新的董事人數合計不超過董事局組成人數的1/3”。
12. 例如深天地A(000023)章程第九十六條規定:“董事會每年更換和改選的董事人數最多為董事會總人數的1/4”。
13. 例如宏達礦業(600532)章程第九十六條規定:“在發生惡意收購的情況下……新改組或換屆的董事會成員應至少有2/3以上的原董事會成員繼續留任”。
14. 中視傳媒(600088);涪陵電力(600452);海立股份(600619)。
15. 中國寶安(000009)章程第九十六條規定:“董事局換屆時……每屆更換董事人數不得超過董事局構成總人數的二分之一”。
16. 長城動漫(000835)章程第九十七條規定:“每年改選的董事不得超過董事總數的七分之一”。
17. 中國寶安(000009);中國天楹(000035);河北宣工(000923);福星股份(000926)。
18. 參見鄭佳寧. 公司收購中目標公司董事的忠實義務研究[J]. 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4, (6): 79.
19. 參見陳霖. 上市公司修改章程設置反收購條款的合法性檢視與監管探討[J]. 證券法苑, 2017, (19): 102.
20. 參見王建文, 范健. 論我國反收購條款的規制限度[J]. 河北法學, 2007, (7): 100.
21. 參見呂紅兵. 大港油田收購愛使股份的操作實錄與法理探析[J]. 中國律師, 1999, (6): 52.
22. 參見吳燕妮. 證券交易所一線監管的淵源、屬性及應用[J]. 金融與經濟, 2019, (5): 67.
23. 參見湯欣. 私人訴訟與證券執法[J]. 清華法學, 2007, (3): 99.
24. 參見丁銳. 險資舉牌之“險”——寶能舉牌南玻A事件的法律思考[J]. 公司法律評論, 2017, (17): 342-343.
25. 同注8。
26. 參見張巍, 鄧峰. 公司章程的多層次審查: 投服中心的初始貢獻[J]. 投資者, 2018, (3): 206.
27. 《特拉華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十一款。
28. 《特拉華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款。
29. 參見張心悌. 董事分期改選制度之研究——從德拉瓦州最高法院Airgas案件為出發[J]. 東吳法律學報, 2015, (3): 11-12.
30. See Rosenhaum D. Classified boards in Missouri[J]. Missouri Law Review,1967, (32): 251-265.
31. See Baysinger B, Butler H. Antitakeover amendments, managerial entrenchment, and the 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J]. Virginia Law Review, 1985, (71): 1258-1260.
32. SeeFrakes M. Classified boards and firm value[J].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2007, (32):113-117.
33. 參見[美]弗蘭克·伊斯特布魯克,丹尼爾·費希爾. 公司法的經濟結構[M]. 羅培新, 張建偉,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192-208.
34. SeeCohen A, Wang C. Reexamining staggered boards and shareholder valu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5): 67.
35. See Koppes R. Corporate governance out of focus: the debate over classified boards[J]. The Business Lawyer, 1999, (54): 1025-1047.
36. 參見湯欣. 公司治理與上市公司收購[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172-173.
37. 同注3。
38. See Jarrell G, Poulsen A. Shark repellents and stock pric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7, (19): 127-168.
39. See Cremers K, Sepe S, Masconale S. Is the staggered board debate really settled[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2019, (167): 43.
40. 參見王建文. 我國公司章程反收購條款: 制度空間與適用方法[J]. 法學評論, 2007, (2): 138.
41. 參見王莉. 交錯董事會制度在我國的合法性與功能分析[J]. 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 (2): 53.
42. 參見[美]M.V.艾森伯格著.公司法的結構[M]. 張開平, 譯.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 390-413.
43. 參見[加]布萊恩·柴芬斯著.公司法: 理論、結構和運作[M]. 林華偉, 譯.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233-280.
44.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6條規定:“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者更換,并可在任期屆滿前由股東大會解除其職務。董事任期【年數】,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
45. 參見阮秋盛. 董事分期改選制度淺析[J]. 證券服務, 2018, (664): 116.
46. 同注35。
47. 參見曹興權, 黃超穎.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的底線:權利配置基礎結構維持原則[J]. 財經法學, 2017, (3): 100.
48. 《特拉華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十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