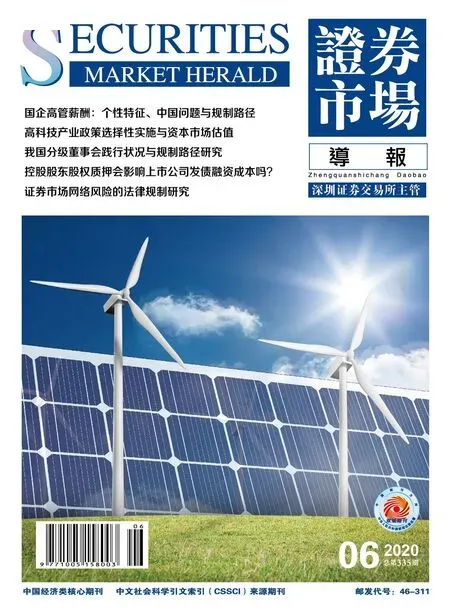國企高管薪酬:個性特征、中國問題與規制路徑
樓秋然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29)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未來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應當完成從“管人管事管資產”到“以管資本為主”的轉變。此種具有鮮明“市場化”特征的改革理路,不僅是對建立“政企分開”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再強調,也有助于促進混合所有制改革與市場經濟相融合、回應競爭中立原則以適應國際競爭。其中,國有企業(以下簡稱國企)高管薪酬的合理確定對于市場化改革意義重大。一方面,與公司業績掛鉤的高管薪酬,可以促使高管自覺追求“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目標的實現。在內外部治理機制均有所欠缺的背景下,可以“自我執行”的薪酬激勵是市場化改革不可多得的制度資源。另一方面,不同形式、結構的高管薪酬,對于高管回應市場競爭需求、不當政治干預的行為模式亦有不同影響。例如,當經濟收益而非政治晉升構成高管行為的主要驅動力時,政企不分問題便可能迎刃而解。
然而現階段,國企高管薪酬卻不斷暴露出“無效率”和“不公平”的問題:第一,高管薪酬漲幅超過公司業績提升,存在“過高”之嫌;第二,高管攫取“灰色收入”、進行高額“在職消費”的新聞屢見報端,薪酬激勵未能抑制貪腐現象;第三,高管薪酬與職工工資差距拉大,給人“不公”之感。可見,就國企公司治理而言,高管薪酬有其兩面性:用之得當,國企改革事半功倍;用之失當,則反而加劇“內部人控制(分享)”問題。2001年安然丑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針對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問題,在公司、證券和稅收等層面重拳出擊,所采行的諸多改革政策已經或可能為我國所借鑒。然而,中國國企的高管薪酬有其獨特的“制度背景”和“問題表現”,若無法對此加以精準認識,則任何原創或舶來的改革舉措都無法做到對癥下藥。有鑒于此,本文將從梳理中國國企高管薪酬之“制定與規制特征”“特殊問題表現”入手,結合比較法、實證研究的知識啟示,提出符合深化改革之方向的政策建議。
一、國企高管薪酬的制定與規制特征:以美國為參照
(一)薪酬制定:最優合同v.董事會俘獲
盡管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大蕭條已經將“過高”的高管薪酬納入法律規制的視野之內1,有關高管薪酬的學術討論卻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后才逐漸飽滿起來。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提出,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而公司法的最大任務則在于減少乃至消弭由此產生的“代理成本”。2Jensen and Murphy(1990)主張公司應“按業績付費”,亦即將高管薪酬與某些客觀標準掛鉤。31993年,美國進行稅法修改,高管薪酬超過100萬美元且不與公司業績掛鉤的部分,不得用以抵扣稅負。4這一規定使“按業績付費”成為通行做法。
然而,“按業績付費”迅速拉大了高管與普通職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飛速增長的高管薪酬促使學者反思其正當性。部分學者認為,飛速增長的高管薪酬是公司與高管之間簽訂“最優合同”的結果;最優合同促使薪酬安排最大化股東利益。5其他學者則主張,公司董事會實際為高管所“俘獲”,飛速增長的高管薪酬是由高管自己決定的,既無效率也不公平。6迄今為止,究竟何者更為準確地描述了美國高管薪酬制定現實的問題,仍無定論。
然而,就中國國企而言,“董事會俘獲”理論更貼近有關其高管薪酬制定的實踐。《公司法》第46條規定,(國企)經理、副經理和財務負責人的報酬事項應由董事會表決通過。《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暫行辦法》第17條更是要求,國企法定代表人/其他負責人的年度薪酬方案應交國資委批復/備案。從應然視角出發,通過國資委和監事會的治理制衡,董事會與高管達成的薪酬安排會是“最優合同”。但是,至少由于以下原因,應然與實然有所疏離:
第一,由于所轄企業數量龐大、事務千頭萬緒,國資委難以對待批復、備案的薪酬方案進行精密管理。截至2019年底,國資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業共有96家。以每家中央企業設置1名董事長、1名總經理、5名副總經理、1名黨組紀檢組組長、1名總會計師計算,國資委所需受理的央企負責人薪酬方案至少為864份。每份方案又包括“應付年薪”“其他貨幣性收入”“年度任期激勵收入”等6項子內容,所需受理事項其實至少達到5190項。在尚需處置國企其他重大事項、人力和技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國資委難以對董事會與高管的薪酬協商進行精密監管。
第二,由于“地位低下、資源匱乏”“缺乏適當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受制于高管/控股股東”等因素7,監事會(獨立董事)在現實中大有淪為雞肋之感,難以發揮《公司法》所托付的監督職能。
第三,國企董事會缺乏進行“最優合同”協商所必需的“獨立性”和“信息流”。盡管國企董事會遵循一人一票的表決原則,但實踐中董事長往往居于支配地位。一方面,董事長可以利用其“召集和主持會議”的“形式”職權,決定決議的“實質”內容;8另一方面,董事長由于具有較高的行政級別且一般兼任黨委書記,在董事會中享有高度權威。若此,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或CEO職位時,董事會對其薪酬難以進行公平協商。而當董事長不兼任其他執行職務時,高管又可以通過扭曲或者隱藏薪酬制定必要信息的方式,使其個人利益的滿足凌駕于公司價值最大化之上。
由此可見,國企高管薪酬的制定具有明顯的“董事會俘獲”特征。而此種“程序性”缺陷,使得針對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無需進一步考量高管薪酬的“實質”合理性,即是否確實與公司業績掛鉤。
(二)薪酬規制:程序正義v.實質公平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21世紀接連發生的安然丑聞和金融危機,都被認為與過高的高管薪酬有著內在關聯。危機的擴散和民眾的不滿,使得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在美國成為當務之急。一系列旨在矯正高管薪酬畸高問題、實現薪酬安排“實質公平”的改革舉措被相繼提出。其典型代表有以下兩項:第一,在大蕭條時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試圖建立、運用“浪費”規則,以宣告過高的高管薪酬無效。在“Rogers v. Hill”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當公司的獎金支出與高管工作價值缺乏關聯時,該項獎金支出構成對公司資產的浪費,應為無效。9第二,在三次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均曾考慮通過“懲罰性稅收”和“工資帽”實質性地調整高管薪酬。例如,1932年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曾提議對高管薪酬超過75000美元的部分額外征稅80%,并不允許公司就此項薪酬支出申請稅收抵扣;羅斯福新政時期,國會要求對接受聯邦援助的行業、公司的高管設置工資帽,比如鐵路行業為6萬美元、航空郵遞業為17500美元。10
然而,這些強調實質公平的改革舉措并未成為主流。一方面,浪費規則在大蕭條之后便極少為法院所使用。特拉華州最高法院在“Brehm v. Eisner”案中指出:法院不會對包括薪酬制定在內的董事會決定展開合理與否的實質判斷;與之相反,法院的判準在于其決策是否遵循了正當程序。11另一方面,出于保護自由市場競爭的考慮,懲罰性稅收從未轉化為立法;而工資帽則始終僅對接受聯邦援助的公司適用,并在援助結束之后自動失效。真正得到廣泛支持的,是有關加強薪酬信息披露、董事會獨立性和股東決策參與權的法律變革。由此可見,有關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在美國呈現出強調“程序正義”的特征。
與之相反,受多重因素制約,中國有關國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更多地著眼于“實質公平”,其突出表現即在于對國企高管薪酬進行封頂。而這種強調“實質公平”的法律規制的成因,則至少可歸結為以下兩個維度:
一方面,自1993年《公司法》通過以來,國企改革便進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全新階段。然而,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獨立董事等現代企業之“形式”要素的引入,并不必然形成制約平衡的公司治理“實質”。公司治理存在的形式化傾向,與“所有者缺位”一經結合,便會由于“內部人控制”引發嚴重的代理成本問題。基于此一現實,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便難以依托于對“程序正義”的強調,否則,無異于在沙灘之上建造城堡。
另一方面,國企高管薪酬法律規制手段的選擇,還受到“人事管理制度”和“社會文化”的雙重約束。首先,盡管監管者一直力主對國企“去行政級別”,但現實中,國企高管往往仍按部、廳、處等級別享受待遇、評價職務調動。與此同時,為增加工作激勵、加強國資委與其他政府部門的監管能力,國企高管往往存在向黨政機關“晉升”、進行“掛職鍛煉”和“崗位輪換”的情況。受此種行政化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影響,國企高管的薪酬便應當在“實質”數額上加以限制,否則,無法與其他行政職位進行有效銜接。其次,由于市場化改革前國企內部的薪資分配較為強調平等性,廠長、干部與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大,因此,高管薪酬的過快增長可能會對既存的勞動、人事和分配制度產生沖擊。另外,高管薪酬的快速增長、與企業職工或者社會公眾平均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也與消除兩極分化、解決分配不公的和諧發展觀念有所抵牾。正是受以上收入“平等”“公平”觀念的影響,國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也必然更加傾向于對“實質公平”的強調。
綜上所述,與作為參照的美國不同,中國國企的高管薪酬實踐在“制定”和“規制”特征上均呈現其個性。此種個性特征,不僅形塑了中國國企高管薪酬的“特殊問題表現”,更成為對既存法律規制手段所展開的一切檢討反思、未來改革方案構建所不容忽略的起點。
二、國企高管薪酬的特殊問題表現
1978年之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的經濟活動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嚴格調控。彼時,由于高管(廠長、干部)和普通職工(工人)之間的薪酬差距甚微、以物質獎勵引導生產的觀念尚未普遍化,針對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并不必要。1978年之后,包括“利潤留成”“盈虧包干”“利改稅”等在內的政策舉措相繼推出,政府開始使用薪酬激勵的手段推動國企改革。然而總體而言,由于尚未采取包括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權在內的“激勵薪酬”,高管與普通職工之間的薪酬差距并不顯著,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問題仍不突出。1990年代開始,為滿足境外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治理的要求,更好地在香港、紐約等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國有控股的“紅籌”公司開始對其高管提供包括股票期權、限制性股權在內的激勵薪酬。12伴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不斷深入、與國際接軌以便參與全球競爭的需求加強,原本僅在境外上市的國企中采行的股權激勵,開始向在境內上市的國企開放。市場化的改革方向、股權激勵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國企高管的薪酬,拉大了高管與普通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然而在同一時期,國企的經濟績效雖有所提高,但卻在各項主要經濟指標上全面落后于私人企業。自此,高管薪酬的“不公平”和“無效率”問題,使得針對其的法律規制變得極為必要。然而,高管薪酬在國企實踐中呈現出遠較“不公平”和“無效率”更為復雜的“特殊問題表現”。
(一)漂浮的高管薪酬:零薪酬與被壓抑的股權激勵
1.零薪酬
“過高”或者“過快增長”的高管薪酬是法律規制的典型對象。然而,在中國國企實踐中,卻出現了另一種極端現象,即高管“零薪酬”。一份針對約3400家上市公司的統計數據顯示,“有近300家上市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2015年的薪資為0”。13但是,零薪酬并不意味著高管確實提供了無償勞動。就國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而言,其事實上或者兼任其他關聯公司的高管職務,或者本身具有政府官員的身份,可以從其他渠道獲得收入。此種薪酬安排至少從兩個方面扭曲了國企的公司治理:
第一,國企往往處于企業集團這一錯綜復雜的網絡之中。以中央企業為例,由國資委控股或全資持有的控股公司往往延伸出3~9個層次的子、孫公司,形成一個龐大的企業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企業集團往往通過剝離(注入)不良(優質)資產的方式,助推部分公司上市;并在之后,從控股公司或關聯公司中派遣人員擔任上市公司的高管,以便進行控制。在這一背景下,上市公司高管不從本公司、而從控股公司或者關聯公司領取薪酬的安排,可能模糊其信義義務的承擔對象。由于薪酬多少并不與本公司業績掛鉤,高管更可能從企業集團的整體利益而非本公司利益出發作出決策。
第二,本身具有政府官員身份的高管,其收入、職業前景不與本公司業績掛鉤,可能加劇“政企不分”問題。一方面,其在進行公司決策時,會更多地考慮所在地方或者部門的利益,促使本公司進行無效率的地方性投資或者為社會穩定雇傭冗員,從而加重國企的社會、政策負擔;另一方面,作為政府官員,其往往更加看重政治晉升而非經濟激勵,因此其企業家角色淡化而更不易于抵御不正當的政治干預。
2.被壓抑的股權激勵
包括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權在內的股權激勵的引入,往往被認為是高管薪酬飛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同時,有關股權激勵無法切實促進公司業績增長、易于引發高管財務造假的研究,亦不斷揭露其可能產生的無效率和不公平問題。然而,在國企實踐中,股權激勵還另外呈現出兩副面孔:
第一,盡管按照《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等文件的要求,國企高管的薪酬組成應當包括股權激勵在內的“中長期激勵”,但實證研究顯示,“截至2015年年初,開展股權激勵的國企上市公司有21家,僅占總體的11%”。14近年來,在國資委的重點推進下,“雙百企業”(國資骨干企業)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的比例也僅達到19%。15由此可見,即便股權激勵確實在美國引發了嚴重的高管薪酬無效率或不公平問題,這些負面影響在中國國企中其實并不顯著。
第二,在已經實施股權激勵的國企中,還可能由于“行權禁止”和“行權收入交公”等因素的存在,股權激勵的制度功能大打折扣。在一項針對“紅籌”公司(前任)高管的采訪中,受訪者表示:其薪酬構成中的股票期權、限制性股權,其實并不能由自己決定行權;即便行權,行權收益也需要上交控股公司。16此種說法,還可以從其他軼事證據中獲得支撐。例如,中海油前任董事長傅成玉便表示,自己并未真正行使過作為高管擁有的股票期權;17中海油控股股東亦曾澄清“有關薪酬只是‘名義收入’,且會全數捐贈予母公司”。18
股權激勵在國企中的“低采用率”和“名實不符”,至少在兩個層面上扭曲了公司治理:一方面,大量國企甚至國有上市公司,可能仍然未為高管提供有效的經濟激勵,從而不利于國企對經濟目標的追求;另一方面,名實不符的股權激勵,減損了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真實性,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資本市場本就孱弱的監督功效。
(二)另類的錦標賽:在職消費和政治晉升
盡管高管與普通職工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容易造成直覺上的“不公平感”,但這種不公平有時卻是實現經營效率的必要代價。除去“按業績付費”這一種解釋之外,為實現效率而容忍不公平還可以從“錦標賽理論”中得到說明。該理論提出:對企業內部不同層級的員工設置較大的工資差距,并使員工事先無從得知誰會最終得到提拔,可以對其提供努力工作的激勵;19另外,伴隨晉升空間的不斷縮小,高層級員工之間的工資差距應當進一步擴大。20然而,在國企實踐中,錦標賽很大程度上不以工資差距的方式展開,轉而以“在職消費”和“政治晉升”的方式呈現。這種另類的錦標賽同樣會削弱高管薪酬的激勵作用,并最終扭曲公司治理。
1.在職消費
所謂在職消費,是高管憑借其特權在工資之外所獲得的“非貨幣性”收益。21盡管部分在職消費屬于高管履行職務之必需、外國/私人企業高管亦享受較高的在職消費,但國企高管的在職消費構成其主要收入的現象則頗為反常。一份針對處于壟斷性行業的A股上市公司(絕大多數為國企)的實證研究顯示:高管在職消費的均值是貨幣性薪酬均值的50.6~79.2倍。22高管在職消費金額高企的成因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公司為內部人所控制,資源被任意揮霍以滿足高管個人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市場化程度不高、股權激勵受抑制等因素,國企高管自認薪酬并未達到市場價格,出于“嫉妒”心理通過在職消費抹平差距。無論基于何種成因,國企高管所享受的高額在職消費都必然溢出于履行職務之必需的范圍。此種不合理的、僅能為高管所獲取的非貨幣性收益,雖然也能在企業內部促成錦標賽,卻會嚴重敗壞公司治理。
第一,與貨幣性薪酬不同,在職消費的合理性難以被查驗、糾偏。以股權激勵為典型代表,貨幣性薪酬總是需要與公司業績相掛鉤。如此一來,高管的貨幣性薪酬總是能夠借由“客觀指標”進行查驗、糾偏。與此不同,在職消費的合理性則體現出需要主觀判斷的特征。對于高管使用的50平方米辦公室是否過于豪華、出席會議是否必須乘坐頭等艙等問題,其實難以給出準確答案。即便股東、監管機關有所不滿,亦很難證明其不合理性。第二,超出合理范圍的在職消費,會為高管的不正當行為提供“正當化”激勵。當高管出于嫉妒心理,利用不合理在職消費消除與外部同行的薪酬差距時,其往往認為此種不正當行為是“本質正當”的。此種“道德”正當化過程可能促使高管進行更多不正當行為——因為其可以借助“消除(不正當的)薪酬差距”這一理由對之加以正當化。
2.政治晉升
在國企內部,政治晉升亦能通過引發錦標賽向高管提供工作激勵。一方面,伴隨政治級別的晉升,不僅高管的貨幣性薪酬獲得提升,而且其享受在職消費的機會、規模亦隨之增加;另一方面,國企高管向黨政部門的晉升可以進一步提升其社會地位和聲望。將政治晉升納入錦標賽范疇,有其積極效應。如何向最終獲勝者(如CEO)繼續提供有力的激勵,對于錦標賽理論十分重要。在一般企業中,可選的方式只能是向其提供更高的經濟報酬。然而,由于效用邊際遞減,經濟報酬的激勵作用終將消退;而向黨政機關的政治晉升,則為錦標賽提供了另一種激勵形式。然而,政治晉升引發的錦標賽亦可能產生嚴重的負作用:
第一,重視政治晉升而非經濟報酬,可能加劇國企的政企不分問題。當政治晉升成為主要激勵,國企高管不僅會更加愿意接受政治干預,從而維持與上級之間的良好關系,為未來的晉升創造條件;甚至會在日常經營管理中,自覺注意迎合地方或者部門利益,從而加重國企的社會和政策負擔。第二,重視政治晉升,還可能不利于國企內部管理模式的轉變。例如,對于處在充分競爭領域、重視創新和員工積極性的企業而言,強調去等級和速決策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可能更有效率。然而,由于過分重視政治晉升,該種企業反而可能更愿意保留“等級式”的內部管理模式。
三、既存法律規制手段的反思
針對國企高管薪酬的無效率和不公平問題,一系列法律規制手段被相繼推出。這些規制手段,或者聚焦于“實質公平”,例如《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關于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高管薪酬進行(有彈性的)封頂,《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以下簡稱《八項規定》)則對高管的在職消費提出限制;或者聚焦于“程序正義”,例如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由“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擬定,并“強制”要求公開薪酬安排的詳細信息。然而,就嚴厲程度和實際效果而言,聚焦“實質公平”的規制手段,在當下顯然仍處于核心地位。就國企高管薪酬的特殊問題表現而言,以上規制手段似乎可謂對癥下藥:薪酬封頂直擊“過高”和“過快增長”的高管薪酬問題;《八項規定》約束高管進行不合理在職消費的攫取之手。但事實上,既存的法律規制手段,不僅不能有效回應國企高管薪酬的特殊問題表現,反而可能使之進一步惡化。
(一)“一刀切”:“意外推高”與“逆市場化”
根據《意見》的規定,國企高管的薪酬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任期激勵收入”三個部分組成。其中基本年薪以上年度中央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為限,績效年薪以基本年薪的“2倍”為限,任期激勵收入以年薪總水平的“30%”為限。考慮企業所處行業和規模、高管崗位職責和風險承擔等因素,《意見》允許國企根據實際情況“在限額內”進行自主安排。例如,副職負責人的基本年薪按主要負責人的“0.6~0.9倍確定”,以此在企業內部形成經濟激勵方面的錦標賽。“一刀切”的高管限薪自然有其優勢:一方面,“一刀切”的法律規制可以最快速度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一刀切”的法律規制還可以節約國資委本就有限的“執法”資源。自2003年成立以來,針對國企的公司治理問題,相較于通過股東會或董事會機制行使“股東權”,國資委仍更多使用“紅頭文件式”的行政管理手段。這其中自然有“政企不分”的緣由,也內涵著“執法”效率的考量:與強調一企一策、精準施策的股東權行使不同,面向全體國企的行政權行使可以通過形成“規模效應”節約“執法”資源。然而,“一刀切”的高管限薪卻可能帶來更多的負面效應:
第一,高管限薪可能意外地推高高管薪酬。限薪的本意在于抑制“過高”和“過快增長”的國企高管薪酬。根據《意見》的規定,國企高管的年薪最多不能超過普通員工年薪的8~9倍。對于原本薪酬差距超過這一限制的國企而言,《意見》當然可以起到降低高管薪酬的作用。然而,對于其他國企而言,《意見》反而可能推高高管薪酬。其原因在于:《意見》在限薪的同時,也正當化了高管薪酬與員工年薪之間8~9倍的差距;原本薪酬差距未達這一限制的國企,反而可能以此為依據為高管加薪。如此一來,《意見》便可能意外地促成更多“過高”和“過快增長”的國企高管薪酬的出現。
第二,行政管理色彩濃厚的限薪,還可能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有所違背。一方面,高管薪酬的快速增長,不僅有董事會俘獲的原因,也有管理人才供不應求的正常市場因素。在這一背景下,限薪可能導致國企高管薪酬“過低”,而“過低”的高管薪酬在加劇國企高管嫉妒心理的同時,也不利于招攬市場化的管理人才。現有的折衷方案是允許通過市場招聘的高管不受《意見》約束,但由此導致的內部薪酬差距亦可能借由“嫉妒”和“不公平感”而影響公司經營管理。另一方面,“過低”的高管薪酬亦將使高管收入與公司業績發生“脫鉤”,此時,包括績效年薪、任期激勵收入在內的薪酬安排便無法發揮其促使高管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努力的目的。
(二)“兩頭堵”:“薪酬補償”與“擠出效應”
限薪雖然在“表面”上降低了高管的貨幣性收益,但并不會使高管自愿接受“過低”的薪酬安排。與之相反,高管可以通過享受更高的在職消費的方式進行“自我補償”。事實上,在《意見》出臺之前,國企的高管薪酬便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這些限制及其所造成的高管薪酬的“外部不公平”,使得國企高管轉而將在職消費作為“薪酬補償”。若此,隨著限薪的進一步收緊,薪酬補償造成的負面影響將進一步惡化。正因如此,中央試圖通過落實《八項規定》限制不合理的在職消費。然而,同時實施限薪令和八項規定的“兩頭堵”策略,亦有其副作用:
第一,如前所述,在職消費的“合理性”極難查驗、糾偏。《八項規定》所提出的“厲行勤儉節約”的要求,在執行中亦面臨相同難題。盡管包括“住房、車輛配備”等在內的部分“工作和生活待遇”確實可在事前進行精細界定,但在職消費的形式多種多樣,難以全部客觀化、指標化。《八項規定》在實際落地過程中所呈現的各種問題,恰為這一判斷的最佳注腳。例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便指出,在國企對《八項規定》的落實過程中,不僅違規現象仍然層出不窮,而且“一些‘四風’問題改頭換面、潛入地下,呈現出由明轉暗、逃避監管等隱形變異現象”。23
第二,“兩頭堵”策略,還可能產生不利于國企市場化改革的“擠出”效應。假設《八項規定》在實踐中確能得到完全落實,則“兩頭堵”策略將會限縮錦標賽的開展形式。一方面,限薪可能造成高管薪酬“過低”,從而導致以工資差距為內容的錦標賽無法進行或效果不彰;另一方面,嚴格受限的在職消費使得高管進行薪酬補償的努力無從實現,導致以享受在職消費為內容的錦標賽失去意義。此時,錦標賽僅能圍繞政治晉升而展開,國企的高管職務亦將因此對重視政治晉升而非經濟報酬的人員更具吸引力。伴隨時間的推移、人員的更替,市場化人才將被逐漸擠出國企。若此,則前述“逆市場化”問題亦會有所加劇。
(三)缺乏實效的程序性構建
除聚焦“實質公平”的規制手段外,我國近年來亦借鑒美國經驗,引入了一系列提升“程序正義”的政策措施,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薪酬委員會”和“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然而,從實踐來看,這些政策措施或者本就存在設計缺陷,或者并未切中肯綮,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1.沒有“牙齒”的委員會
盡管《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僅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可以”設立“薪酬委員會”,但由于《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以下簡稱《準則第2號》)的規定,薪酬委員會的設立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已是一項“硬性”要求。在上市公司中引入薪酬委員會,并要求其多數成員由獨立董事擔任,自然是希望通過提升高管薪酬制定程序的“獨立性”來克服其無效率和不公平的問題;然而實證研究表明,這一制度目的并沒得到完全實現。一方面,就整體而言,“薪酬委員會的設置并沒有顯著影響上市公司薪酬業績敏感性”24;另一方面,與民營企業相較,國企薪酬委員會的治理能力較弱。25制度目的與實際效果之間的疏離,顯然可以被歸結于薪酬委員會的力量缺乏。
第一,根據《準則》的規定,薪酬委員會雖有“研究和審查”高管薪酬方案的權力,但該方案的最終批準權仍為董事會所掌握。如前所述,國企存在突出的“董事會俘獲”問題,此種權力分配難以解決高管“自定”薪酬的問題。第二,與美國《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要求薪酬委員會“完全”由獨立董事組成不同,《準則》僅要求薪酬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當“占多數”。若此,內部董事亦可以充任委員會成員,并可能對委員會決議施加影響。第三,薪酬委員會為董事會的“下設機構”,其成員在實踐中往往由“董事長、二分之一以上獨立董事或者全體董事的三分之一提名”,并最終由“董事會選舉產生”。考慮到突出的董事會俘獲問題、委員會成員當選或連任與否系于董事會意志等因素,薪酬委員會難以發揮實效也就完全可以預見。
2.不充分的信息披露
有關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法律規制,在過去十余年間已大有完善。2003年修訂的《準則第2號》僅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年度報酬總額”、金額最高的前三名董事和前三名高管的“報酬總額”;而2017年修訂的《準則第2號》則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每一位”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稅前報酬總額及其全體合計金額。此種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細化,當然有助于提升高管薪酬的透明度,增強資本市場和高管聲譽機制的監督作用,然而,既存的信息披露制度其實尚難以回應國企高管薪酬的特殊問題表現。
第一,高管“零薪酬”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未得到消解。盡管根據《準則第2號》第55條的規定,上市公司需說明其高管“是否在公司關聯方獲取報酬”,但上市公司無需進一步披露高管在關聯方所獲報酬的具體情況。就國企而言,這一規定不僅繼續認可了其高管在關聯企業甚或政府部門獲取報酬的實踐,更使其實際所受激勵的結構和數額無法為外部市場所知。第二,資本市場無法借助信息披露對不合理的在職消費進行監督、糾偏。根據《準則第2號》第55條的規定,上市公司雖然需要披露“每一位”高管的薪酬,但亦僅需披露“總額”;至于構成總額的基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等形式、數額究竟如何,仍不為公眾投資者所知。如前所述,在高管薪酬受到“限薪”和“八項規定”的“兩頭堵”時,其往往通過在職消費進行“自行補償”。若上市公司無需詳細披露高管的非貨幣性收益信息,則因不合理的在職消費所引發的公司治理問題便無法得到緩解,更遑論消除。
四、國企高管薪酬規制路徑的再構建
(一)思維轉換:從“一刀切”到“精準施策”
根據《意見》的規定,國企高管薪酬被“一刀切”地限制在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8~9倍之內。對于此種規制手段在實踐層面所可能引發的負作用,前文已有所論及。然而,其作為一項規制手段在應然層面上的“不可欲性”,則仍有待進一步檢討。
第一,無論立法抑或司法機關,均難以為“過高”提供精準界定。“一刀切”的規制目的在于抑制過高的高管薪酬,其正當性必須建立在對如下兩個問題的回答之上:其一,5~6倍甚或3~4倍的薪資差距,何以不構成過高;其二,9~10倍甚或10~11倍的薪資差距,又何以構成過高。對于以上兩項問題,其實均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意見》出臺之后,關于國企高管薪酬究竟“過高”抑或“過低”的討論持續發酵,為其注腳之一。而“一刀切”的規制手段在美國法上的式微,則可以提供另一種視角的參考。如前所述,在三次危機時期,美國均曾提議或者采納“一刀切”的規制手段,然而這些措施最終都沒有成為主流。至于其原因,則可以從美國法院對“浪費規則”的態度中窺見一斑。在“Rogers v. Hill”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過高的”薪酬屬于無效。但是,其并沒有就如何判斷“過高”設置明確的標準,而是將案件發回重審交由下級法院解決。該案最終以原被告和解而結案,法院也因此無須提供標準。而在“Brehm v. Eisner”案中,特拉華州最高法院則拒絕對高管薪酬的實質合理性進行討論,而強調對“商事判斷規則”的堅持。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法院根本無法對何謂“過高”進行精準界定。
第二,由于所處行業、發展戰略、管理人才稀缺度等因素,高管薪酬的確定本就因公司而異,無法在事前進行“一刀切”的法律規制。對于這一點,針對《意見》實效而展開的實證研究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撐。一份針對2007~2017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表明:《意見》對“成長性較好樣本公司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顯”,其原因即在于該類公司更需要通過高薪酬來激勵高管努力工作。26另一份針對《意見》之前其他限薪政策的實證研究指出:對壟斷性的國企進行限薪,可以在不影響公司業績的前提下提升內部公平感;然而,處于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則可能因此遭受效率減損。27事實上,《意見》及其他限薪政策并非對該問題全然沒有體察。例如,根據《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負責人基本年薪的確定應考量“企業經營規模”和“經營管理難度”等因素,但此種“彈性”為國企適應個性需求預留的空間仍然太小,不足以克服“一刀切”式法律規制的弊端。
若此,針對國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應當完成從“一刀切”到“精準施策”的轉變。至于精準施策的含義,必然是要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在充分考量“個體”國企具體情況的基礎上,對其薪酬安排作出“個別”回應。若此,則各級國資委必須借助“股東會”和“董事會”等內部治理機制,而非“紅頭文件”對高管薪酬進行監管。然而,由此產生的問題在于:如前所述,紅頭文件式的行政管理可以節約國資委的“執法”資源;則“精準施策”是否會導致國資委力有不逮?事實上,在“一刀切”的規制思維得以轉變后,法律規制的重點亦必將從實質公平轉向程序正義;此時,借助內部治理和信息披露機制的完善,國資委反而可以依托其他制度資源更好地履行其出資人職責。
(二)側重轉移:程序正義及其保障
既然國企的高管薪酬不應進行“一刀切”的事前封頂,則其具體數額、結構、形式便應交由公司自己加以確定。此時,國企高管薪酬制定所呈現的“董事會俘獲”特征,便成為必須克服的障礙。而此種克服又主要可以借助“薪酬委員會”和“信息披露”兩項機制加以實現。
1.為薪酬委員會“賦權”
若欲使薪酬委員會制度克服“董事會俘獲”問題,并最終達成關于高管薪酬安排的“最優合同”,便需要賦予其充分的“權威”。此一賦權至少需從如下方面進行:第一,薪酬委員會的職權,應從“研究和審查”薪酬政策與方案,擴充至“制定和批準”薪酬政策與方案。若認為這一方案過于激進,則至少應規定由薪酬委員會擬定的薪酬方案,董事會無正當理由不得修改。第二,薪酬委員會的人員構成,應從“獨立董事應當占多數”,改變為“應當全部由獨立董事擔任”。盡管《準則》規定應當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主席),從而對薪酬委員會的獨立性有所幫助,但內部董事兼任委員仍然能對決策過程、結果直接施加影響,有損委員會的功能發揮。第三,薪酬委員會成員的選任方式,應由“董事會選舉產生”改變為“全體獨立董事選舉產生”。另外,還應當對薪酬委員會成員的解任設置“有因解除規則”,以避免其在行權過程中遭受不當干預。28第四,鑒于獨立董事的選任本就受制于高管的客觀現實,似乎還應考慮建立獨立董事人才儲備庫,從中隨機抽取獨立董事以組成薪酬委員會的方案。
在權威賦予之外,還必須給予薪酬委員會制定薪酬方案所必需之信息,否則,其權威無從真正實現。而當薪酬委員會成員完全由獨立董事擔任時,其信息匱乏問題便更加嚴重。此時,存在兩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一是允許高管參與薪酬委員會討論,以向后者提供與其薪酬制定相關之信息,但禁止其參與薪酬的最終制定;二是設置可以行使(1)接近公司各類職員、(2)調查公司各類內部文件、(3)參加各種董事會或者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各項職權的“監察使”(Ombudsperson)一職29,為薪酬委員會提供必要信息。
2.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再細化
第一,盡管“零薪酬”在國企大多以“企業集團”形式構建,在政府部門履行出資人職責的現實下無法被直接禁止,但其可能導致的信義義務承擔對象的錯位問題,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有重大意義,必須予以詳細公開。《準則第2號》應進一步要求上市公司說明該高管在關聯方取得報酬的數額和具體構成形式,并披露該關聯方的實際控制人等。通過此種詳細的信息披露,投資者可以提前獲知高管信義義務承擔對象的可能錯位問題,并做出不購買或者折價購買股份的決定。
第二,在職消費有“合理”與“不合理”的區分,然而其邊界、查驗和糾偏卻較難進行。此時,通過信息披露施加“聲譽”懲罰比訴諸正式的法律訴訟程序更有效率。根據《準則第2號》的規定,上市公司僅需公開每一位高管從公司中所獲取的各種形式的報酬“總額”,而不必就各項內容的個別數額進行詳細披露。若此,則高管是否、以何種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在職消費的情況,根本無從為公眾投資者所知曉。《準則第2號》應當在未來進一步要求上市公司詳細公開高管所享受的所有無法被劃歸為基本年薪、年度績效和中長期激勵的貨幣或非貨幣性收益,而無論其數額。
在法律規制的側重從實質公平轉移至程序正義之后,國資委僅需關注國企是否搭建了規范的內部治理機制、進行了足夠的信息披露。此時,國資委可以借助獨立董事、證監會、資本市場和聲譽機制等制度資源輔助其履行出資人職責。若此,則國資委的“執法”資源不會由于需要進行“精準施策”而捉襟見肘。
(三)結構優化:股權激勵和績效年薪
第一,股權激勵的“廣泛化”和“真實化”。自20世紀70年代 Jensen and Meckling提出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范式以來,以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權為典型形態的激勵薪酬便被認為是一項可能的治理機制。盡管過去實踐已充分暴露出其弊端,但其促成高管與公司利益連接、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應然)功能亦得到廣泛認同。事實上,伴隨內外部公司治理的不斷完善,股權激勵的優勢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如前所述,就現階段而言,股權激勵在國企中存在“低采用率”和“名不符實”的問題。因此,與美國正在經受的股權激勵的巨大負作用相比,我國國企的股權激勵尚需首先完成“廣泛化”和“真實化”的制度創設工作。這一創設工作的總體方向自然應以“分類改革”為基礎。至于股權激勵在個別國企高管薪酬中的具體比例,則一如前述,應交由該國企通過內部程序加以決定,并依托信息披露等制度設計接受監督。
第二,績效年薪的“去中心化”。根據《意見》的規定,國企高管薪酬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和“中長期激勵”三個部分組成。按照中長期激勵不超過年薪的30%、績效年薪最多為基本年薪2倍計算,高管薪酬中的“績效年薪”最多可占年薪的46.7%。若此,則績效年薪這一“短期”激勵在國企高管薪酬中占據“中心”地位。盡管存在“延期支付”和“薪酬追索”等約束機制,但是績效年薪的中心化,仍可能造成嚴重的“短視”問題從而損害國企長遠發展。其原因至少可被歸結為如下兩點。一方面,相較于公司的中長期表現,與績效年薪相掛鉤的公司年度業績數據更容易被偽造、篡改;另一方面,相較于中長期激勵,績效年薪的兌現更快,從而具有更高的“現值”。考慮以上因素,未來的國企高管薪酬應當完成績效年薪的“去中心化”,而放開對中長期激勵比例的限制。至于中長期激勵,尤其是股權激勵所可能帶來的無效率和不公平問題,則應交由公司治理機制的完善加以解決。
五、結語
就國企的市場化改革而言,其高管薪酬的合理確定問題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面,有效率的薪酬數額、結構可以為高管自覺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提供動力;另一方面,無效率、不公平的薪酬則不僅有損國企利益,更削弱、動搖民眾對國企乃至公有制的信心。盡管在過去四十余年,尤其是近二十年里,一系列旨在解決國企高管薪酬之無效率和不公平問題的法律規制手段被相繼提出,但這些規制手段,或者由于本身存在設計缺陷,或者對國企實踐中呈現的“本土化”問題缺乏回應,不僅未能徹底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高管薪酬的不公平和無效率。未來國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必須進行整體性調整:一方面,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應當完成從“一刀切”到“精準施策”的思維轉換,并由此應當更加關注包括薪酬委員會賦權和信息披露細化在內的“程序正義”構建;另一方面,在摒棄對高管薪酬數額、形式的硬性限制的基礎上,高管薪酬的法律規制應同時關注薪酬結構的優化問題,以避免短視主義的危害。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9年度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公司股利分配法律制度研究”(19SFB3032)的研究成果]
注釋
1. See Rogers v. Hill (Hill III), 289 U. S. 582 (1933).
2. See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3(4): 305-360.
3. See Jensen M C, Murphy K J. CEO incentives—it's not how much you pay, but how[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 (May-June): 139-140.
4. See Stout L A. The toxic side effects of shareholder primacy[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2013, 161(7): 2009.
5. See Core J E, et al. Is U.S. CEO compensation inefficient pay without performance?[J]. Michigan Law Review, 2005,103(6): 1142-1185.
6. See Bebchuk L, Fried J.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參見郭靂. 中國式監事會:安于何處,去向何方——國際比較視野下的再審思[J]. 比較法研究, 2016, (2): 76-78.
8. See Kershaw D. Company law in context: text and material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250-251.
9. 同注1。
10. See Wells H. “No man can be worth $1000000 a year”: the fight over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1930s America[J].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2010, 44(2): 751-754.
11. See Brehm v. Eisner, 746 A. 2d 244 (Del. 2000).
12. See Chen Z, Guan Y, Ke B. Are stock option grants to directors of state controlled Chinese firms listed in HongKong genuine compensat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5): 1555.
13. 參見2136家企業高管薪酬上漲 近300位高管“零”年薪[EB/OL].[2020-04-11]. http://finance.sina.com.cn/trust/xthydt/2019-04-30/doc-ihvhiewr9038961.shtml.
14. 參見王勇, 鄧峰, 金鵬劍. 混改下一步:新時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思路[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8: 172.
15. 參見杜雨萌. 國資委:央企所屬“雙百企業”19%已實施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EB/OL]. [2020-04-11].http://www.zqrb.cn/finance/hongguanjingji/2020-04-03/A1585885812375.html.
16. 同注12。
17. 參見傅成玉回憶在中海油年代:千萬年薪一分沒動 都上交了[EB/OL].[2020-04-11].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lian ghui/20130308/7747017.shtml.
18. 參見中海油稱所有執行董事自愿放棄去年薪金及獎金[EB/OL].[2020-04-11]. http://news.cntv.cn/20120415/120358.shtml.
19. See Bognano M L. Corporate tournament[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1, 19(2): 290-315.
20. See Rosen S. Prizes and incentives in elimination tournamen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4):701-715.
21. 參見萬林華. 國外在職消費研究述評[J]. 外國經濟與管理, 2007, (9): 39.
22. 參見楊蓉. 壟斷行業企業高管薪酬問題研究: 基于在職消費的視角[J].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5): 139.
23. 參見通報數據顯示國企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仍有短板——對癥下藥,釋放監督剛性力量[EB/OL].[2020-04-14].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1810/t20181011_181221.htm.
24. 參見高文亮, 羅宏. 薪酬管制、薪酬委員會與公司績效[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11, (8): 84.
25. 參見姚成. 薪酬委員會特征對高管薪酬粘性影響的實證檢驗[J]. 統計與決策, 2019, (17): 176.
26. 參見黃賢環, 王瑤. 國有企業限薪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嗎?[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2020, (1): 35, 45-46.
27. 參見潘敏, 劉希曦.“限薪令”對企業內部薪酬差距激勵效果的影響研究[J]. 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3): 71-72.
28. 參見樓秋然. 董事職務期前解除的立場選擇與規則重構[J]. 環球法律評論, 2020, (2): 102-117.
29. See Dallas L L.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 the dual board and board ombudsperson[J].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1997, 54(1): 13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