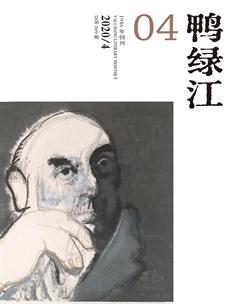書寫即記憶,即抵抗
直到這次新冠肺炎爆發,許多人才驚覺到,SARS竟然已經過去17年了。這也提醒我們一個事實,17年來,除了須一瓜的《白口罩》和畢淑敏的《花冠病毒》,竟然沒有多少以SARS為原型的文學作品。在這期間,我也讀到了一些師友和普通人的記錄。他們的文字樸素平實,有點點滴滴的生活,日日夜夜的守候,而沒有廉價的感動和煽情,也沒有悲憤的怨恨和控訴。這次疫情出現了許多讓人心碎痛苦的場景。問題是,在我們看過聽過經歷過如此多之后,我們如何去講述,如何將事實融入虛構,又如何在虛實的共同指認中去檢省、去清理我們自己和社會的病灶?
1
在世界文學史上,疾病(此處指傳染病)書寫不在少數。從視之為神的懲罰,到具有敬畏心的實錄,到充滿信念地以行動相博弈,再到以之為文明危機的指喻符碼,這是一個歷時性的過程,也是一個文學思想和書寫的變化發展過程。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中,瘟疫皆因世人壞了倫理綱常而觸怒天神所致。瘟疫襲擊了忒拜城,“田間的麥穗枯萎了,牧場上的牛瘟死了,婦人流產了”,家園一片荒涼,冥土充滿了悲嘆和哭聲。俄狄浦斯王憂心如焚。在神的諭示下,他追尋弒父兇手,真相大白后刺瞎雙眼放逐了自己,這是一個在道德倫理上進行自我更新和贖罪的過程。1350年,薄伽丘以1348年發生在佛羅倫薩的鼠疫為背景創作了《十日談》。由于人們無法認識疾病的源發性原理,只能視之為“天體星辰的影響”或“多行不義,天主大發雷霆”的降罰。這是前現代的敘事方式,神秘主義元素對應著命運的變化無常,我們今天當然不應也不會去提倡這種寫作。我們早已科學地認識了傳染病的發病原理,也深知它們帶給人類的巨大危害。因此,對于疾病書寫來說,如果做不到在虛構中進行指認,那么至少應當學會誠實和敬畏,學會甄選真實的史料記下所見所聞,比如笛福的《瘟疫年紀事》(1722)。這部小說以發生于1665年英國的瘟疫為背景,通過鞍具商H. F.的回憶展開敘事(有一說H.F.是笛福的叔叔亨利·福)。瘟疫漫卷而來時,H. F.選擇留在倫敦,并決定記錄下自己和周圍人經歷的一切。他說寫作此書是為了給后人留下一份備忘錄,萬一再有類似的災難降臨,可以提供一些指導。這場瘟疫“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而光”,他看到人們一天天無助地死去,尸體堆積如山,政治、權力、財富都讓位于生存。瘟疫全面引發了信仰和道德危機。政府捂著消息導致謠言滿天飛,王室干脆避禍于鄉間,全國治安大亂。1665年瘟疫發生時,笛福才五歲,應當對災難沒有太多記憶,但這并不妨礙他尋找并篩選史料,假敘述者之口將史實和盤托出。為了達到求真的效果,笛福淡化了作家的身份,而返回了他從事過的記者行當。他研究了很多醫學論文、官方小冊子、1665年的《死亡統計表》,采用編年體方式進行講述,從1664年9月到1665年底,幾乎是逐月報道瘟疫的進程和影響。笛福非常喜愛倫敦的街道,他讓H.F.總是在街上游來蕩去,敘述基本上也是以H.F.所在的地理位置展開的。據統計,小說中一共提到了175處以上的街道、教堂、酒館、村莊、濟貧院、菜市場、市政廳等地理坐標。有的地名兼具隱含意味,如貝爾胡同(Bell Alley,bell一意為“喪鐘”)。H.F.對街道的了如指掌突顯了瘟疫的恐怖程度:它將已知變成了未知,將通行之途變成了死亡之地。H.F.所熟悉的倫敦已經完全陌生。我們跟隨這位姓名不詳的敘述人游歷街道,帶著心酸、痛苦、絕望和恐懼,重新認識這個死亡空間。有人為了避免聞到房子里飄出的臭味而行走在街道中央。有人在街上大叫:“再過四十天,倫敦就要滅亡了。”有人在街上裸體狂奔哀號:“噢,無上而威嚴的上帝呀!”有病和無病的人被同屋隔離,江湖醫生和星相家詐騙錢財,護理員悶死患者奪走財物,病人疼痛難忍跳樓或開槍自殺,運尸車通宵忙碌,教堂里滿是哀吟祈禱的人……一幅末日景象。
《瘟疫年紀事》的價值首先是史實的真實性,其次才是文學的可讀性。文獻、數據、圖表、符箓、廣告、政府公告被鑲嵌在文本之中。這種近似于非虛構和報告書的方式使小說不太像小說,這正是笛福的創作動機所致。他就是要讓小說像是親歷者的回憶錄或匿名抄本,如小說開篇故弄玄虛的題記:“由始終居留倫敦的一位市民撰寫,此前從未公之于眾。”這種寫法有著堅實的可信度,含納著不斷重返過去的令人心碎的熟識感。就像編輯辛西婭·沃爾在《導言》中所說:“紀實因故事而得以充實,故事由于紀實而得到保證。”其實,描寫這場瘟疫的書不少,但最后,只有笛福的這部小說流傳了下來,被人們視為“大疫年”的百科全書。事實上,在瘟疫次年,倫敦發生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火,城市的五分之四被燒毀,昔日街道悉數消亡。《瘟疫年紀事》因此具有了雙重價值:它是病理學的紀實,也是地理學的記錄。
2
如果想要了解人類如何與瘟疫進行搏斗這一主題,加繆的《鼠疫》(1947)當屬“樣板”。小說詳細描寫了奧蘭城發生的烈性傳染病,塑造了封閉隔離空間之下各種各樣的人:失控的人、恐懼的人、麻木的人,還有勇敢的人、純潔的人、高貴的人。通過對“人”的切片取樣和具象微觀的考察,加繆讓我們重新認識到了“人”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小說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里厄醫生,敘述自始至終貫穿著他的視角。他看到老鼠搖晃著,口吐鮮血并倒地身亡,他聽到老鼠垂死掙扎的輕聲慘叫,他注意到發燒死亡的病例短時間內大為增加,他意識到這就是曾經吞噬過一億人的鼠疫。他向政府提出“不合時宜的堅決要求”,使省府同意召開衛生委員會會議。他和里夏爾醫生、卡斯特爾醫生向省長說明嚴重性,強調必須立即采取嚴厲的預防措施。省長糾結于這究竟是不是鼠疫,一直猶豫不決,直到疫情不斷惡化,醫院很快爆滿,才不得不正式宣布封城。一旦城市封閉,大家只能是“一鍋煮”。人們被放逐在自己家中,過一天算一天。消息不通,外援難以進入,醫療和物質資源嚴重匱乏。各色人等紛紛上演著死神追逐之下的本性。病人精神錯亂,商人囤積居奇,警察疲于奔命,官僚在等待上級的命令,市民們在瘋狂搶購據說可預防傳染的薄荷糖,垂死者懷著仇恨和無意義的希望拼命纏著活人。鼠疫在生活龐大的體表上劃出了一道長長的裂縫,裂縫不斷擴大,直到成為深淵,遂使整個現實都沾染上了地獄的瘴氣。在奧蘭城這個封閉的空間里,不同的人各有行動,“人”的層次感清晰而飽滿,每個人都構成了鮮明的某一類型、某種典型。醫生里厄忙著救人,神父帕納盧忙著布道,公務員格朗忙著推動衛生防疫工作,志愿者塔魯忙著記錄疫城的生活。兩個逆襲的例子是,性情孤僻多疑的科塔爾走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外地來的記者朗貝爾最開始一心要出城,在得知里厄醫生的妻子因染病被送到外地救治時,他自愿留了下來。他說,一個人如果只顧自己的幸福,那是羞恥的。加繆是一個行動主義者,他將這一理念投射到了里厄醫生身上。醫生與瘟疫博弈,時常感到孤獨無力。妻子病亡,他沒有辦法接她回來。母親擔憂他的安危,他也沒有辦法安撫她。在他要隔離病人被罵心冷心硬時,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決定。因為他一直堅定地認為,作為醫生的責任就是與病毒做斗爭,使盡可能多的人活下來,使盡可能多的人不至于永遠訣別。里厄醫生從來不認為投身于抗疫工作就是英雄。他說自己對英雄主義和圣人之道都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做一個真正的人。他還說:“同鼠疫做斗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這樣的話,我們何等熟悉,但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我們卻要一再付出生命的代價。
3
《鼠疫》的現實指認很清晰。加繆以封閉的奧蘭城指喻1940年以后被納粹占領的法國,以鼠疫病菌象征法西斯及其統治下的恐怖時代,以奧蘭城人民忍受的絕望隔離象征當時法國人民經受的生離死別。這種指喻性在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1995)中體現得更為普遍,更具文化和文明危機的警示意義。在《失明癥漫記》中,一種奇特的傳染病發生了:失明癥,僅通過目光對視就可傳染。它是一種“白色眼疾”,染病者仿佛是睜著眼睛沉入了明亮濃密的牛奶海里。第一個失明的是一個司機,“那人的眼睛似乎正常,虹膜清晰明亮,鞏膜像瓷器一樣又白又密”,然而他卻沖著人們絕望地喊叫:“我瞎了!我瞎了!”送他回家的路人立刻被傳染了,這個路人實為偷車賊。車到手后,他沒有走出30步就失明了。眼科醫生是第三個受害者,當時在診所里的其他病人無一幸免。眼科醫生把病情報告給自己醫院的醫療部主任和衛生部官員,但他們粗暴地拒絕相信。失明癥迅速蔓延,城市陷入了恐慌和絕望。當局下令將所有患者趕進一個廢棄的精神病院進行隔離。一排房子住失明者,另一排房子住失明癥嫌疑者。如果一個疑似者真的失明了,他會立即被同伴趕進對面的房子,所以無須操心患者的挪移問題。當局派出士兵武裝把守,規定如果有人想離開就開槍打死,如若出現起火、騷亂、斗毆,無人會去救援,死者由患者直接就地埋掉。小說中的城市沒有明顯的地理特征,人物也都沒有名字,只有身份、性別或外形特征的命名:男人、女人、醫生、醫生的妻子、斜眼小男孩、戴墨鏡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等。他們是被隔離的人,是被瘋狂射殺的人,是在尸體旁邊吃飯的人,是遭受屈辱踐踏的人,是在污穢骯臟中茍且偷生的人,是摸索著鐵鍬埋了別人爾后又被別人埋了的人。這種毫無主體確定性的修辭暗示著,他們就是你和我,是我們每一個人。《失明癥漫記》包含著豐富的想象、比喻的筆法、結實的細節,這使得抽象的恐懼和形而上的指喻具有了可感知的外形,敘事的可信度和情感的黏合度如影隨形。它在實證主義層面上雖不可能發生,但卻是完全有可能的一種令人恐懼的“未來”。在這個黑暗的絕境里,人性所有的原始之惡都被激發出來:食物被霸占,婦女被強奸。強者欺壓弱者,野蠻戰勝了文明。人性骨子里被規訓的“野獸”掙脫了文明秩序的桎梏,人之為人的尊嚴和廉恥喪失殆盡,千百年來培養的教養禮儀猶如風中之燭頃刻滅跡,轉眼就回到了蠻荒時代。看完這本書,大概每個讀者都會暗自慶幸:還好我沒有失明,我還看得見。可是,誰又能保證自己的“看得見”就是“看得見”呢?“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這是《失明癥漫記》的題記,取自于《箴言書》,而小說中提到的“能看但又看不見的盲人”在生活中大有人在。這個句式我們也可以改成“能聽但又聽不見的聾子”“能說但又說不出的啞巴”。器官和功能都正常,但就是沒有辦法行使“真”的權利。“失明癥”只是薩拉馬戈的想象,但這想象造就的寓言卻與現實息息對映。世界確實感染過或正在感染諸種惡疾,無數人在災難中失去肢體、器官、至愛、親人和生命。加繆在《鼠疫》結尾提醒過我們:“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瘟神再度而來并不可怕,最可怕可悲的是,在科技和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竟然在遭遇相似的傳染病時還會犯下相同的錯誤。這或許是因為長久以來我們深陷于繁榮和發達的幻覺之中,從而使得厄運的重復降臨有如初見,攜帶著新鮮的猙獰和死亡。就像老黑格爾所說,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這一次,希望我們能夠留下一些生命的呼吸、節奏、顏色、狀態,留下一些人們之前不甚了解的“謎語”。這樣,在下一次災難到來時,我們或許會少一些狂妄和傲慢,多一些誠懇和謙遜。
【責任編輯】? 陳昌平
作者簡介:
曹霞,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文藝爭鳴》等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專著兩部。曾任教于日本愛知大學。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入選天津“五個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