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地產過高的租售比形成原因及化解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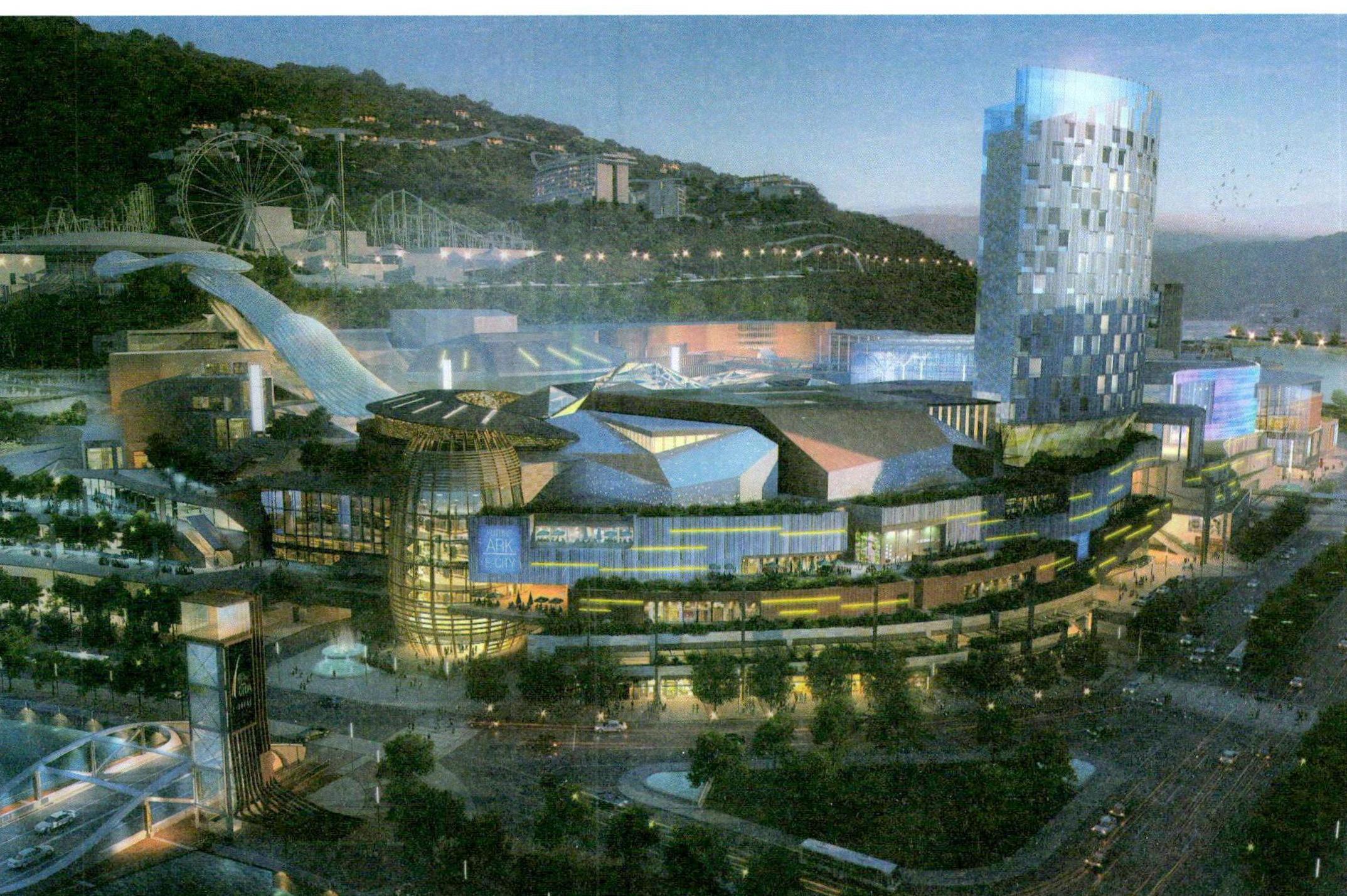
摘要:商業地產的租售比之高,在事實上遠遠超出了投資邏輯上的合理范疇,在投資活動的商業邏輯意義層面上出現了價格和價值的嚴重背離,完全失去了通常金融邏輯上的投資價值。
關鍵詞:投資回報;金融牌照;價格管制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1-9138-(2020)02-0060-62 收稿日期:2019-11-17
與住宅不同,商業地產是完全意義上的投資品,投資決策時首先是要考慮投資回報及退出難度與路徑的。關于商業地產投資的退出難度與技術路徑這里暫且不表,單就商業地產投資回報來講,其來源主要有兩點:基于運營所產生的租金及其衍生收入與資產買賣差價收入。就后者而言,一方面與宏觀行業走勢乃至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有關,另一方面還與物業經營管理水平帶來的租金收入多少和資產管理賦予的資產流動性有關,但是宏觀行業狀況與金融、城建政策是資產價值形成的基礎,經營管理和資產管理只是影響性因素。而買賣差價收入之外,最能體現商業地產投資回報的核心指標就是租售比了,這也是本文需要探討的問題。
大家知道,投資決策時無風險利率水平是最重要比對指標,也就是說無風險利率是投資的機會成本和決策選擇之錨,對于商業地產投資決策同樣如此。當前,集合信托在事實上存在著剛性兌付,所以在實踐中一般都將集合信托的收益水平默認為無風險利率。從安全性、流動性方面來比較,集合信托都是優于商業地產投資的,所以從金融活動的商業邏輯上來講,商業地產的投資回報率至少應高于集合信托。也就是說,從商業邏輯上來講,租售比作為商業地產投資回報的最核心的指標,所反映出來的收益率應是高于無風險利率的。
但邏輯歸邏輯,事實卻是如此的殘酷,我國當前商業地產租售比所反映出來的投資收益率遠遠低于無風險利率,通常情況下連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一半都達不到,更何談要高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無風險利率了?也就是說,商業地產的租售比之高,在事實上遠遠超出了投資邏輯上的合理范疇,在投資活動的商業邏輯意義層面上出現了價格和價值的嚴重背離,完全失去了通常金融邏輯上的投資價值。
但是凡是現實存在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么,我國商業地產當前超高的租售比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經濟快速增長的溢價。中國入世后的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且相對于成熟的經濟體而言這一勢頭在較長的時期內還有望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帶來的財富效應推動了資產價值的提升并形成了對未來的價值預期,也就是說產生了高速發展之下的資產溢價,這是我國商業地產的市場價值普遍較高這一現實狀況之所以出現的經濟社會條件的基本面。
第二,土地市場的一級壟斷。我國的土地市場中的一級市場是由政府完全壟斷的,出于增加土地財政收入規模的內在沖動,政府有控制土地人市節奏、人為制造土地市場短缺以推動地價上升的內在沖動,由此造成了地價不斷上升和難以真正實現市場話調節的預期。這種預期反應到房價之內或者疊加到房價之上,就自然而然推高了投資性物業,也就是商業地產的資產價格。
第三,金融牌照管制和利率管制拉低了無風險利率并推高了民間融資的市場化利率,進一步推高了包括商業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金融業在我國是市場開放度較差的行業,其中的國有經濟成分較高,政府與國有金融企業在利益上的兩位一體導致了以銀行、保險、信托、證券等為代表的金融行業較高的準人條件和價格管制,讓金融牌獲得者成為一種制度性租金的獲利者。他們一方面管制負債端的利率來壓低資金獲取成本以保證牌照租金和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以管制資產端利率來向央企和國企為主體的融資端輸送利益,也就無形中拉低了無風險利率和推高了民間融資的市場化利率,反過來也就從估值機理和成本兩個方面共同作用推高了包括商業地產在內的資產價格。
事實上,土地財政的內在沖動在推高土地價格的同時也形成了土地的過量供應,而現有城市建設法規的強制性配套規劃導致了商業地產建設的超前性和過量人市。但在兩者共同作用之下的商業地產的二級市場卻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其結果便是商業地產的價格在一二線城市的新區已一改之前遠遠高于住宅的狀況,而且租金水平在市場的過量供應之下普遍被拉低的同時,租金水平的區域和地段分化也日益嚴重。即便如此,從租售比角度而言,依然是遠遠高于可以對比的成熟經濟體的水平,導致以REITs為代表的商用物業資產證券化產品和工具在我國出現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或者在實質上演變為一種債性融資行為,而不能像這類金融工具發達的國家那樣一方面以之來推動行業發展,另一方面也為廣大中小投資者提供了一種風險相對較低而收益相對較高、較為穩定的投資機會,為投資機構提供了一種流動性和收益性相對較好的資產配置品種。
通過以上對我國目前商業地產過高租售比的形成原因進行的探討與分析,也就自然能夠得出如何才能化解過高的租售比、打開商業地產投資價值以及商用物業資產證券化的化解之道了:
第一,要逐步放棄土地財政,讓政府收入擺脫對于土地出讓金的過度依賴,進而放開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實現打破不同土地性質的認為劃分和割裂,讓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要素供求和價格完全實現市場調節,以此來化解土地價格被認為推高和超出市場均衡點的虛高現象。在暫時還不能作到這一點條件下,可以加快推進不同性質土地之間的平權和無條件人市,推動土地供需和價格的市場化調節機制,最大程度上去除土地作為生產要素被壟斷和管制所帶來的價格虛高現象。另外就是在規劃法規方面將商業地產配套比例的強制性要求改為指導性要求,讓市場的力量去調節商用物業的供需和利用市場機制來引導對商用物業的投資,自然會實現商業地產投資與商業地產租售比向合理水平的市場回歸。
第二,逐步放開金融牌照和價格管制,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回歸市場供需平衡之下的真實定價。也就是說,要逐步放開市場準人,以利率和匯率的逐步市場化來解決人為制造的牌照租金和對以央企和國企代表的部分利益團體的利益輸送,在推動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市場化定價的情況下實現利率向真實市場利率的回歸,以此來逐步消失利率在不同市場之間的區隔與分化造成的資產價格的失真,來促進商業地產租售比向真實水平的回歸。
就商業邏輯上而言,如果商業地產自身創造的以租金為核心的凈現金流不能覆蓋同期銀行貸款利息時,投資決策的唯一依據就是未來物業價格上漲的部分能夠填補經營性現金流的虧空并有所結余。但是目前商業地產市場的實際情況是,大多數商用物業的經營性現金流連同期銀行利息的一半都不到,除了一線城市和一些中心城市的核心區域以外,市場對于物業未來的升值速度也缺乏普遍的信心。目前商業地產存量的形成,多是以住宅為主業的開發商被動形成的沉淀資產,只是住宅開發行業務的配角和依靠開發業務的現金流來補充其運營成本,商業地產在事實上成為開發商資產負債表上的累贅。
在當今過高的租售比之下,商業地產無論從運營方面,還是從投融資方面都是困難重重。但是商業地產畢竟是城市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是金融和商貿服務業發展的基礎設施之一,在社會經濟結構向消費社會快速轉型和就業結構向服務業轉型的今天,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使得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一現實需要的角度,必須從土地制度、城市建設管理和金融體系方面進行反思和重構,同時也必須從政策體系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和逐步調整與引導,讓商業地產的投資和運營最終回歸市場邏輯。
作者簡介:柏文喜,眾和昆侖(北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