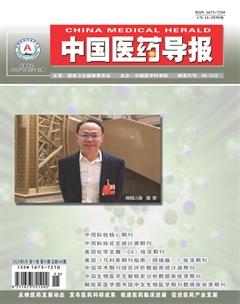國際規范內化理論視角下的世界衛生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發展歷程、挑戰與建議
阿咪娜 代 濤 鄭英 馬琳 程才



[摘要] 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是支持世衛組織實現其組織目標的合作者,同時也是中國參與全球衛生治理的一支重要隊伍。本文運用國際規范內化理論,從認知變化、制度變化和政策實踐3個維度梳理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初步發展階段、能力提升階段和快速提升階段的發展歷程,結合文獻梳理、現場調研、深度訪談和專家咨詢等方法分析當前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面臨的認知渠道不暢、國家層面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不力等問題與挑戰,并提出強化頂層設計和戰略布局規劃、整體推進在華合作中心發展,建立緊密的協調機制、暢通溝通交流渠道,積極調動主觀能動性、進一步提升在華合作中心的品牌效應和國際影響力等建議。
[關鍵詞] 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中心;國際規范內化;全球衛生;發展
[中圖分類號] D996.9?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1673-7210(2020)05(c)-0168-05
Development process, 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WHO cooperation center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normativ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A Mi′na1,2? ?DAI Tao2▲? ?ZHENG Ying2? ?MA Lin2? ?CHENG Cai2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730, China; 2.Institut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0,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in China is a partner in supporting WHO in achieving its 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o analyze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capacity improvement stage and rapid improvement stage of who cooperation centers in China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chang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olicy practice.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researc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who cooperation center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lack of cognitive channel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policy support at the country level. In addition, it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layout plann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centers in China as a whole, establish a clos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pe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ctively mobilize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brand effect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ooperation centers in China.
[Key word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ng Center Center; Inter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Globalhealth; Development
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世衛組織”)作為全球衛生治理的領導者,一直引導著全球衛生治理議題的走向和治理模式的創新[1]。為增強國家參與全球衛生治理能力,世衛組織利用衛生領域現有研究機構,通過提供技術支持、搭建合作平臺在世衛組織會員國任命世衛組織合作中心[2-3],協助開展傳染病防控、慢性非傳染病防控、公共衛生與全球衛生、衛生體系發展等領域的工作。本文基于“國際規范內化”理論對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分析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發展問題及挑戰,為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更好地參與全球衛生治理提供政策建議。
1 國際規范內化理論
隨著全球事務朝著專業化和制度化的方向發展,國際規范內化逐漸成為推進和實踐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4]。針對國際規范內化的內涵,國內外學者有不同的見解。美國學者Keohane[5]對國際規范做出了界定,認為國際規范是指主體與主體之間對相互關聯的行為構成的約束準則。Alderson[6]認為,國際規范內化是通過物質懲罰和類似于國家間伙伴壓力等綜合作用,使國際體系中的新規范讓國家接受的積極機制。本文中國際規范內化的內涵是指國家將國際上的價值觀、規范和行為方式轉化為自身穩定的反應模式,并且內在地認為這些國際制度具有吸引力[7]。
目前,國際規范內化理論通常在國際外交、教育和全球衛生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如《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國際衛生條例》等均為該理論在全球衛生領域的應用實踐。國內學者馬建英[8]、康曉[9]將國際規范內化表現的判斷指標分為認知變化、制度變化、政策實踐3個遞進維度。本文將借鑒這一思路并與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發展特點相結合,從認知變化、制度變化、政策實踐3個方面梳理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發展歷程,分析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本文的理論框架如圖1(世衛組織合作中心國際通用規范指世衛組織合作中心定義、指南等一系列文件)所示。
具體來說,在認知層面,主要體現在行政部門決策者及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負責人對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作用功能的認知變化和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領域數量變化。在制度層面,主要包括建立政府部門間的管理協調機制、增設專辦部門/人員。國際制度一旦在一國產生內化,除了在該國設立相應的配套制度之外,決策者還會采取與之相適應的國家政策,以促進國際合作,踐行國際規范[10]。在政策層面,主要通過行政部門政策文件的發布,與世衛組織簽訂一系列戰略協議來分析。
2 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發展歷程及內化過程
大多數學者將全球衛生發展歷程分為3個階段:傳染病防控階段(1948~1978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階段(1978~2003年)、全球公共安全頻遇危機階段(2003年至今)[11-13],本文也將從這3個階段,分別闡述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發展歷程及內化過程。
2.1 恢復和重建國內體系與秩序,為參與和融入國際規范奠定基礎
傳染病防控階段(1948~1978年)是世衛組織全球合作中心的初步發展階段,全球處于戰后社會經濟恢復期和衛生體系重塑期,各地特別是貧困地區流行病猖獗,包括瘧疾、鼠疫、霍亂、傷寒等[14]。隨著中國進一步參與國際制度,國際制度的規則和規范逐漸融入中國的認知和政治結構之中,規范認同開始成為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良性互動的基礎條件。
1948~1978年,世衛組織在全球任命了32家合作中心。該階段全球范圍內合作中心以傳染病防控和職業健康為主,合作中心的發展與當時全球衛生重點領域、關鍵問題緊密相關(見圖2)。由于此階段中國尚未與世衛組織建立正式關系,沒有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
在傳染病防控階段,原衛生部設立了國際合作司來組織指導衛生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對外宣傳、援外工作,開展與港澳臺地區的交流與合作。此階段,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醫療基礎薄弱,對參與全球衛生的認識不足,缺乏配套的制度安排和相應的政策實踐,因此,中國對世衛組織合作中心并沒有產生內化。
2.2 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初步建立并穩步增長,對國際規范的認知和實踐逐步提升
“人人享有衛生保健”階段(1978~2003年),世衛組織全球合作中心處于能力提升階段。世衛組織有能力倡導和幫助各國把基本衛生保健作為國家基本福利制度中的組成部分,把享有衛生保健推向全人類,開始了“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工作階段[15]。
1978~2003年間,世衛組織在全球任命了216家合作中心,該階段全球合作中心以傳染病防控為主,公共衛生與全球衛生領域的合作中心數量僅次于傳染病防控領域。此階段全球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發展與各國落實世衛組織倡導“人人享有衛生保健”有關聯[16]。該階段中國與世衛組織的互動關系從初步接觸轉向全面接觸及逐步加深理解加強合作時期,中國對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認知逐步提升。其中,任命在華合作中心28家,以傳統醫學合作中心為主,生殖與婦幼健康領域、傳染病防控領域和康復醫學等領域合作中心逐漸興起。見圖3。
在認知層面,隨著中國進一步參與國際制度,國際制度的規則和規范逐漸融入中國的認知和政治結構之中,規范認同開始成為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良性互動的基礎條件[17]。此階段世衛組織和原中國衛生部簽署了衛生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自此中國政府與世衛組織的合作納入正軌,一些醫藥衛生研究機構陸續被指定為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自第一批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任命,在國家衛生行政部門指導下開展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交流活動。
在制度層面,1978年至今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管理與協調遵循1983年發布的《衛生部關于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中心管理的辦法》(1983年11月21日(83)衛科教字第73號)。基于該管理辦法,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管理機制,這實際上規范了行政部門、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參與國際制度的政策協調。國際規范在國內的內化實施過程中,一般要求國內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或歸口單位[18],主要表現在相關的政府部門中設立對應的部門,增加并培訓處理與國際制度相關事務的專門人員,以處理與國際制度相關的各方面的事務。原衛生部國際合作司設立了國際組織處擬訂國際交流與合作工作規章制度并檢查執行情況且承辦聯合國機構、世衛組織等的聯絡和協調工作、管理并協調在華合作中心項目合作的實施和評估等。
在政策層面,國際組織倡議開展援外工作,中國遵循《衛生部關于援外醫療工作人員管理辦法(試行)》,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積極響應,輸送具有技術儲備專家參與援外醫療隊工作。
此階段,國內逐漸認可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專業性、權威性,對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認知逐漸提升。已形成相應的配套管理制度和管理機構,政策層面缺乏頂層政策規劃,配套政策不完善,內化力度不足,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處于學習和認同階段。
2.3 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發展與滯后并存、創新與固化并存,對國際規范的認知和實踐全面深化
全球公共安全頻遇危機階段(2003年至今),也是世衛組織全球合作中心的快速發展階段。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公共安全頻遇危機。埃博拉、禽流感、馬爾堡出血熱等新興病毒威脅著國際社會,特別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和地區[19]。
2003年至今,世衛組織在全球任命了587家合作中心。該階段全球合作中心仍以公共衛生與全球衛生、傳染病防控為主,衛生體系發展領域的合作中心數量逐漸增多,中國有38家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獲得任命,亦以傳染病防控和衛生體系發展為主,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與全球合作中心發展趨勢一致,體現努力滿足公民不斷增長的健康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對衛生事業發展的新要求,重視宏觀衛生體系規劃,與世衛組織優先發展戰略契合。
在認知層面,此階段中國對國際規范的理解和認知發生了深刻變化,進入接受國際社會的核心價值和規則、逐漸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一些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高層管理人員積極研習變革中的世衛組織政策,轉變合作中心職能,與世衛組織理念契合,為全球衛生治理做貢獻。
在制度層面,原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國際組織處對接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合作項目,把與各合作中心相關工作納入國際司重點工作,并建立了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協調辦公室來承擔溝通、服務、研究等職能。此外,為適應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國際衛生合作需求,部分地方衛生行政部門自上而下設立對應的外事部門,制訂了相關外事規定,提供涉外培訓。
在政策實踐層面,此階段世衛組織全球合作中心發展參照《世衛組織工作總規劃》相關要求,如《世衛組織第十三個工作總規劃》中明確提出要重視有影響力的全球公共產品,包括著力制訂和推廣實施規范指南和協議、數據收集分析和應用以及研究與創新[20]。該階段中國與世衛組織在雙方戰略性文件框架下簽訂了四輪次的《中國-世衛組織合作戰略》[21],推動世衛組織合作中心從對國內問題的關注擴展到對世衛組織全球目標的支持,提供標準、指南等衛生公共產品,為中國參與全球衛生治理做出貢獻。在《中國全球衛生戰略》“加強對中國全球衛生戰略技術支持”的一節中,明確提出:“要整合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成為一支中國參與和影響世衛組織地區和全球行動的有生力量”。
此階段,中國對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理解和認知發生了深刻變化,是影響中國與世衛組織合作的制度改革和策略制訂的基礎。配套制度的完善奠定了政策文件的出臺,一系列戰略政策文件可以看出中國衛生行政部門對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重視程度逐漸加深,進一步推動國家衛生發展戰略和世衛組織規劃相契合,進而塑造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發展的新理念和規范。
3 世界衛生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發展面臨的挑戰
3.1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認知渠道不暢,阻礙世衛組織與在華合作中心實現目標
世衛組織通常以召開學術會議、發布技術報告方式解讀組織目標或相關政策,相關信息覆蓋面較窄、范圍較小,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從世衛組織直接獲知當前全球衛生戰略重點、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相關政策的機會不多,不僅影響在華合作中心響應、支持世衛組織工作,也影響其結合相關戰略重點制訂發展規劃和行動策略,阻礙推進相關工作。部分在華合作中心對自身身份的認可不夠充分,任命后只停留在“掛名”上,未能利用自身特長與優勢,積極主動地開展衛生領域活動,以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身份在各國開展衛生相關合作較少。大部分在華合作中心專注于國內,合作中心職責在任命及續任前后未結合當前衛生領域發展重點、世衛組織戰略及國家戰略進行擴展、更新與轉變。
世衛組織對在華合作中心自上而下的認知提升,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自下而上的認知自信兩方面得不到匹配與平衡影響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由認知到行動轉變。各在華合作中心之間缺少信息分享與技術交流,在全球范圍內與相同專業領域機構或網絡之間的合作交流也不充分,尚未樹立合作中心的品牌與影響力。
3.2 多層面制度保障不完善,影響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整體性、系統性發展
當前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尚未形成暢通、高效的交流溝通機制,影響中心參與國際衛生合作交流和內部運行效率,體現在與世衛組織、區域辦事處等外部溝通方面,合作中心獲取國際衛生領域合作信息的渠道不暢通;與掛靠單位、上級衛生行政部門等內部溝通方面,亦沒有形成完善的上通下達的溝通協調機制。
在華合作中心對其掛靠單位的依賴性較強,人員也多以兼職為主,尚未形成穩定的可持續的經費投入機制和專職人員隊伍。從外部考核與激勵機制來看,世衛組織不為在華合作中心提供資金支持,且預算項目對在華合作中心也沒有傾斜,對在華合作中心的激勵主要體現在提升其機構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及自身能力建設等技術支持方面,激勵機制較弱。從內部考核與激勵機制來看,部分在華合作中心每年會對工作人員進行考核評價,但考核方式比較簡單,僅限于年度相關工作的總結,部分合作中心尚未開展任何形式的考核評價工作。內外部考核與激勵機制的缺乏都導致了在華合作中心管理松散、積極性缺乏等問題。
3.3 國家層面相關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相關保障措施仍有待加強
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發展缺少配套頂層設計和規劃的政策文件,《衛生部關于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中心管理的辦法》自1983年出臺以來,多年來一直未進行更新完善,適用于在華合作中心的發展政策較少,影響在華合作中心依規開展相關工作。在華合作中心開展國際合作時也面臨一些宏觀的政策障礙,如合作中心申請舉辦國際會議時審批時間較長、資金申請流程較為復雜、在華合作中心在技術和公共產品(中草藥、試劑盒)輸出時流程和審批管理嚴格等,影響國際合作進程。
政府層面雖逐漸認識到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在參與全球衛生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在中國參與全球衛生治理相關政策文件中倡導發揮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作用,尚未形成促進在華合作中心發展的政策體系和保障措施,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4 啟示與建議
4.1 強化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布局,整體推進在華合作中心發展
國家層面對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工作進行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布局,將在華合作中心發展與國家衛生事業發展規劃相結合,做好統籌發展規劃,轉變當前松散、零星化的發展狀態為統籌協調、齊頭并進的整體發展方式,具體包括:解讀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相關政策,明確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職責定位,了解其地域分布及數量變化及優勢特點等,鼓勵、扶持重點領域在華合作中心發展,建立具有科學性、標準化的激勵約束機制,及時更新、發布《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管理辦法》等。
4.2 建立緊密的協調機制,暢通溝通交流渠道
進一步明確國家衛健委、世衛組織西太區辦事處、世衛駐華代表處以及在華合作中心管理辦公室各自的職責與功能定位,建立更為緊密的溝通協調機制,在合作中心任命前、履任期間、開展活動等環節中發揮好各自的職能與作用,增強在華合作中心的規范意識和歸屬感。在各層級的管理機構間形成暢通、高效的溝通交流機制,盡可能減少因人員流動出現的斷檔現象,保證合作中心業務工作的正常開展。具體包括:以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征集、匯總在華合作中心動態;定期開展形式多樣、內容多元的培訓和交流活動;及時更新、通報負責在華合作中心相關事務人員的變更信息等。
4.3 積極調動在華合作中心主觀能動性,進一步形成品牌意識、發揮品牌效應
世衛組織或國家衛生行政部門以召開學術會議、發布技術報告、開展培訓等方式解讀組織目標或相關政策,將有助于在華合作中心了解當前全球衛生領域發展重點、世衛組織戰略及國家戰略;有助于在華合作中心理解其內涵及外延,及時更新與轉變合作中心職能,輻射區域、放眼全球。
鼓勵成立中國的世衛組織合作中心聯盟。通過定期召開在華合作中心主任會、技術領域研討會等促進在華合作中心交流常態化;加強在華合作中心與國際組織間交流,推動各領域在華合作中心建立或參與本領域全球網絡等,提升世衛組織合作中心品牌意識,發揮品牌效應。
[參考文獻]
[1]? 許晴.試析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作用的變化[D].北京:外交學院,2018:1-5.
[2]? 魯雅.利益相關者分析視角下世衛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管理策略研究[D].北京:北京協和醫學院,2016:3-8.
[3]? 劉久暢.試論世界衛生組織在華合作中心的意義和作用[J].中國衛生產業,2018,15(13):191-192.
[4]? 蘇長和.全球治理體系轉型中的國際制度[J].當代世界,2015(11):34-37.
[5]? Keohane,R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 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3-4.
[6]? Alderson KAI.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J]. Rev int Studies,2001,27(3).
[7]? 鐘龍彪.國際規范內化:涵義、機制及意義[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12(6):22-27.
[8]? 馬建英.國際氣候制度在中國的內化[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6):91-121,159.
[9]? 康曉.利益認知與國際規范的國內化——以中國對國際氣候合作規范的內化為例[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1):66-83,155.
[10]? 曹俊.國際制度的國內化[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2:5-8.
[11]? 晉繼勇.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的國際機制分析[D].上海:復旦大學,2009:8-13.
[12]? 徐彤武.埃博拉戰爭:危機、挑戰與啟示[J].國際政治研究,2015,36(2):33-60.
[13]? 張夢姣.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的中國參與[D].濟南:山東大學,2016:8-10.
[14]? 高明,唐麗霞,于樂榮.全球衛生治理的變化和挑戰及對中國的啟示[J].國際展望,2017,9(5):126-146,172-173.
[15]? 馬琳,鄭英,王璐.基于國際規范內化理論的我國與WHO的合作發展[J].南京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16(5):339-342.
[16]? 張朝陽,孫磊.全民健康覆蓋的內涵界定與測量框架[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4,7(1):19-22.
[17]? 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于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歷史解釋[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4):17-22.
[18]? 馬琳.不同時期我國國際衛生合作策略研究[D].北京:北京協和醫學院,2013:12-18.
[19]? 曾瑞聲.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機制的形成與演變:國家利益[D].廣州:暨南大學,2012:19-22.
[20]? 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2019-2023年第十三個工作總規劃》草案.2018.
[21]?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中國-世衛組織國家合作戰略(2016-2020)[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6, 9(3):68.
(收稿日期:2020-01-16? 本文編輯:封?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