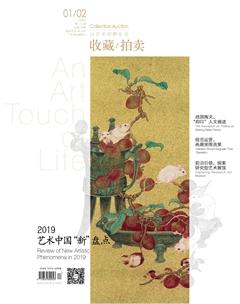宋代贛州鑄錢院鑄鏡往事
李德堂 姚純見



國祚綿延300年的宋代并重理想與現實,兼備大俗與大雅,有趣有料有態度,有些事情絕對超出常人想象。比如最不缺錢的鑄錢機構錢監(院)竟然也搞副業——鑄鏡創收,而且搞得還很有聲勢和傳承。近些年來陸續發現數枚宋代錢監(院)鑄造的銅鏡,如“咸平三年庚子東京鑄錢監鑄造”銘銅鏡;“升州錢監”、匠人蒯口”銘素面銅鏡;“豐國監造官(押)匠人林八鑄”銘雙鳳方形銅鏡以及三枚同銘贛州鑄錢院鑄造銅鏡,這些實物力證錢監鑄鏡貫穿兩宋,大江南北,皆有為之,絕非個例。
錢監(院)鑄鏡原是初心使命
銷錢鑄器,謀收攫利是錢監(院)鑄鏡的根本所在。錢監是國家鑄造銅錢的機構,銅錢本應為其法定的唯一產品。但由于錢荒始終伴隨宋代一朝,為緩解錢荒,朝廷采取禁銅政策,嚴格限制民間銅器生產,且必須在官府監督下生產流通,使得“銷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民多銷銅錢為器,利率五倍,乞禁約。”銷錢鑄器成為宋時普遍現象。這種現象在作為日常使用銅器之一的銅鏡上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致有的宋鏡直接鑄明“每兩一百文”“佳者每兩一百五十文”,明碼標價,爭相逐利。在這樣一個大環境、大機遇下,身處鑄錢重地,原料充足,工匠云集,技術雄厚的錢監(院),又怎能忘卻抵御住高額暴利的巨大誘惑?積極開辟鑄鏡副業,攫取豐厚利益成為其必然的選擇。
宋代贛州鑄錢院的身份證是什么?
“鑄造銅器尤甚”的贛州地處江西南部,古稱南康郡,隋改虔州,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改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合流之義”,自此贛州地名沿用至今,轄境相當今江西省贛州市、石城、興國以南地區。
據《宋史·食貨志》和《宋會要輯稿·食貨》載,宋政府主管采礦鑄錢的最高行政機構為“提點諸路坑冶鑄錢司”,管理地域為東南九路,總部就設在饒州,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增設虔州鑄錢司,大觀二年(1108年)設立虔州鑄造院,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改虔州為贛州,虔州鑄造院隨之更名贛州鑄錢院,從虔州鑄錢司設立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贛州鑄錢院停鑄撤并至饒州(鄱陽)歷經百年之久,可謂極盡風雨、幾經分合。需要給予亮明的是贛州鑄錢院至淳熙二年(1175年)停鑄,僅僅存在了二十二年。
又是司又是院的,兩者有無區別,不免有點小迷糊,有必要請出《宋史·食貨志》說說潔楚:宋代幣政管理機構大致采取三級管理模式:中央一級,始歸三司管理,元豐改制后,三司被撤,恢復了戶部、工部的地位,之后實權為宰相掌握;地方一級稱“鑄錢司”,鑄錢司具體管理各地“錢監”或“鑄錢院”,其勞作工匠主要是“役兵”,不涉及其家屬的安置等事宜;監、院既是管理機構又是生產單位,屬地方二級管理機構,錢監在京畿開設,以制造母錢和樣錢為主。鑄錢院則是錢監的一種補充或臨時設置,在各地設立,以鑄造大錢和夾錫錢為主,始于崇寧二年(1103年)。而大觀年間設立的虔州鑄錢院,則是蔡京當政時推出所謂“新修錢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募私鑄人丁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從某種意義上說,鑄錢院是蔡京推行當十銅錢和夾錫錢的產物,它的興衰,既與蔡京的政治生涯的變易相關,又與當十錢、夾錫錢的流通狀況及私鑄錢風行有密切的關聯,并受到了宋代幣制、錢監管理制度的限制。在客觀上一方面暫時滿足了朝廷因戰爭而引起的日益膨脹的財政需要,另一方面,也緩解了長期困擾朝廷的各地私鑄盜鑄問題。
40個鑄銘隱含重要史料信息
目前發現三枚同銘贛州鑄錢院鑄造銅鏡,一枚贛州館藏素面葵形銅鏡,銘文居鈕左,直徑26.3cm;一枚素面委角葵形銅鏡,銘文居鈕右,直徑18.5cm;一枚委角六出葵形,直徑18cm,三枚銅鏡盡管鏡形有別,但銘文內容、數量、書體一致、且均呈四列豎鑄格式,應為同一同時期、同一印模蓋戳鑄造。40個鑄銘(押)分為:“贛州鑄錢院鑄造到/匠人劉三劉小四王念七等/作頭陳七秤典朱謹劉章/保義郎差監鑄錢院劉元(押)”,既有“贛”字銘高出引銘“贛州鑄錢院鑄造到”官方身份標簽,又有“匠人劉三劉小四王念七等”三位鑄造者的大名,一位“作頭陳七”、兩位“秤典朱謹劉章”、一位“保義郎差監劉元”等鑄錢院管理人員銘記和花押居尾低收,形制規整、內容豐富、千年信息撲面而來。應是“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功致為上,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宋時官方鑄錢制度要求,旨在加強錢院精細分工管理,提高產品質量;打上花押則是亮明國營身份,以示官、民鑄鏡有別,簡單地說就是“物勒工名”。
宋代手工業生產的各種門類都稱某其“作”“作頭陳七”,意即鑄鏡作坊中鑄造銅鏡的“工頭”是陳七,“作頭”之稱一直沿用至明潔時期;“秤典朱謹劉章”,應是鑄鏡作坊中具體負責銅鏡規格重量的管理者。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此處鏡銘還告訴我們稱典編制為兩人(“朱瑾”和“劉章”),其目的就是雙人值守規則,確保銅鏡貨真價實,足見宋代鑄鏡制度的嚴謹科學性;“保義郎差監鑄錢院劉元”,應是贛州鑄錢院鑄鏡總負責人。“保義郎”是一種武職官階,舊稱右班殿直。南宋保義郎在有“品”之武職五十二階中,序列第五十,屬低等階武官。
鑄銘不僅使我們對宋代鑄錢院等官營手工作坊的組織架構及管理形式有了直觀了解,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宋代銅鏡鑄造史和官營鑄錢監鑄鏡的情況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贛州鑄錢院鑄鏡為何罕有面世?
雖說宋時錢監鑄鏡不是孤例,但出土面世實物卻真實地表明:錢監鑄鏡并不多,贛州鑄錢院鑄鏡數量更為罕見。為什么呢?2007年4月,原湖州博物館館長閔泉先生發表在《中國文物報》的《管窺宋代銅鏡業中的湖州鑄鑒局》(圖5)一文中對鑄鑒局(宋朝在湖州管理銅鏡鑄造的管理機構)設立的目的和職能作了較為客觀推論:“1.在錢荒銅禁時期,生產銅鏡牟取暴利;2.生產銅鏡專供皇室及達官貴人使用;3.監督管理當地制鏡業。”也間接解答了錢監(院)鑄鏡為什么罕見的原因。借鑒閔先生論述觀點,筆者以為贛州鑄錢院鑄鏡數量之所以罕見還應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
一是贛州錢院存世鑄鏡時間短,導致鑄鏡總量必少。宋代從虔州鑄造院到贛州鑄造院鑄造錢幣或兼鑄銅鏡的歷史,雖達近百年,但真正稱“贛州鑄錢院”的時間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其所鑄銅鏡時間僅有1153-1175年短短二十二年,正由于時間短,故能留傳至今的“贛州鑄錢院”署名鑄鏡只能是鳳毛麟角,有關贛州鑄錢院的銅鏡實物迄今為止公開所見僅三面也足以為證。
二是官方鑄鏡用材精足,導致價高量少。由于宋時持續錢荒銅禁,鑄錢鑄器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官方鑄錢監(院)更是嚴格執行“物勒工名”制度,在此背景下,作為官方鑄錢院的高利副業鑄鏡業必然是精煉銅材,嚴控產量和質量,高價牟利。
三是官方鑄鏡供給對象有限,直接導致出土面世量罕見。正是因為其官方身份和前兩方面因素,宋代官方鑄鏡必然成為皇室專供、達官貴人爭購的緊俏稀缺器物,尋常百姓幾無可能觸及,供給服務對象從其制造那一刻起就被牢牢鎖定在屈指可數的一定范圍中,現代又怎可能有較大的出土面世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