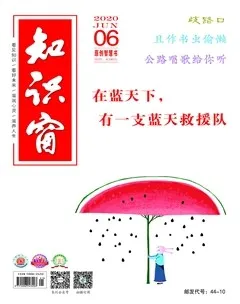遇見人間四月天
夏眠
小學自然課本的第一章節便是認識自然,雪融化成了水,匯入了江河湖海,又或升華入天空,之后凝聚化成水滴,落到了地上,結成了冰。配圖是雄偉的冰山,在冰山腳下是潺潺的流水,水邊是櫻色簇擁著的花,那是書本教給我關于春天最初的印象。
等長大些,和許多少女一樣,一朵花開便能讓我心動,一片落葉就能讓我感懷。所以,對于冰雪消融,我更是多了一份朝氣蓬勃的期待。
雪融化了之后是什么?
是春天呀!
這段對話被我用鋼筆工工整整地寫在書簽上。書簽上浮著櫻花圖案,散發著幽幽的櫻花香,我把它虔誠地夾在我最喜歡的日記本里。還未等我把日記本填滿,我又把書簽放到了一本在書店偶然遇見的書中。
長大后,我對于安好晴天的迷戀退卻了,對于櫻花的喜歡倒是與日俱增,無論是江蘇無錫的黿頭渚,還是美國的西雅圖,我都會熱切地期待櫻花開放的那幾天。櫻花開了,春天就近了,一切溫暖的、美好的、只存在于幻想的事,都會在櫻花下落的時間里慢慢發芽,慢慢生長。
我遇到了一個如櫻花般精致可愛的女孩子小鹿,她與我在一個寫作同好者群里相識。寫作,是一件孤獨且難以維持的事,若是遭遇了拒絕或者批評,更是容易放棄,小鹿卻一直堅持著。一開始我只是覺得她有趣得很,現在卻不知道該怎么形容她了。
若是用太陽形容她,顯得張揚;若是用春風形容她,又顯得單薄;若是用麋鹿形容她,又顯得敏感。想來想去,竟然還是櫻花最為妥帖,在寒意還未散盡的時候,她已然花開了,哪怕有風霜雪雨,她都散發著滿身的花香,告訴身邊的人,再堅持下,春天就到了。當春天真的來了,萬物復蘇,她就和大家一樣,從容而又輕松地渡過盎然的日子。
“你喜歡櫻花啊,來我這邊看啊,武漢大學的櫻花可好看了!”
“你來,我請你吃鴨脖啊!不辣的!很香!還有熱干面!”
說得久了,我對于武漢的印象漸漸立體起來,以小鹿為圓心,以武漢大學的櫻花為半徑,形成了一個圓,圓里有熱干面,有鴨脖,還有臭鱖魚。
“好的,好的,等考完試我就來。這次是資格考試,還不知道能不能通過呢!”
“可以的!你肯定可以的,我有預感!”
因為小鹿的篤定,我也陡然生出自己就是可以的勇氣,仿佛被文曲星眷顧一般順利通過了考試。就在我和小鹿熱切地商量旅行計劃時,凜冬悄然而至。
這是我經歷過的最寒冷、最漫長的冬天。
小鹿和我說武漢封城了,朋友生病了,湖北封省了,她回不去了,向來積極的她忽然變得消沉,這樣的落差讓我難以忍受卻又無從安慰。我在遙遠的地方,無論什么樣的言辭,都自帶遠離災難的慶幸,我只能機械地安慰她會好起來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所有的努力看起來都像是推山石的西西弗斯,每當見到曙光,就會被更糟糕的烏云吞噬掉。
窗外,杭州進入了陰雨的冬季,雨氣纏身。彼時的武漢也下著雨。人間的四月天好像凍結在了一月的冬雨里,再也不會來了。忽然,我身后的燈亮了。
夜晚,小鹿照常和我互道晚安,她習慣性地問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吧?”我信心滿滿地附和:“一定可以的!”
小鹿笑著說:“哈哈!你每次都這么說!”
“這次不一樣。”
“哪里不一樣?”
“因為我要來了。”
“!!!”
“因為我要來了,我要來馳援武漢了,等我。”
降落天河機場的那天,天下著雨,風一吹,冷得我直縮脖子。院長說了許多振奮人心的話,但是我只想趕緊躺著。
從此,我和小鹿仿佛又調換了角色。我開始變得壓抑而又絕望:那些溫暖而美好的事,那些激勵而沖動的熱情,所有那些本該存在于世間的,在頃刻之間,就消散得干干凈凈。“明明”二字成了最無力的語句起始,明明他還好好的,明明上午還和我說話,明明……我討厭這個詞,因為跟在它身后的只有背道而馳的現實的荒涼。
她成了那個安慰我的人,給我留言,給我鼓勵,無論多晚,她都會執拗地等我回到賓館,哪怕只能等到一句簡單的打卡,抑或完全沒有回答。就這樣,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忽然有一天小鹿告訴我:“武漢大學的櫻花開了!”
櫻花開了!春天就來了!
重癥的人數少了,重癥轉輕癥的人數多了,方艙醫院一家家關了,工作量也沒以前那么重了。
“我聽說武漢大學那邊接待了援鄂的醫療隊,你們去了嗎?那邊的櫻花開得很好呢!”
“不是我們醫療隊呢。”
“不知道什么時候才可以出門。”
“等我走了,你就可以回來了。”
直到我離開的那天,小鹿還在惋惜,沒能一起看看武漢大學的櫻花。
我們就好像水滴一樣,彼此吸引;我們又好像行星一樣,彼此守望。每當有人憔悴,就會有人為她開花;每當有人落入迷霧,就會有人為她領航;每當有人經歷嚴寒,就會有人為她取火。
離開武漢的那天,微風拂面,天朗氣清。
來年,我一定會回到這里,遇見武漢大學的櫻花,遇見武漢的人間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