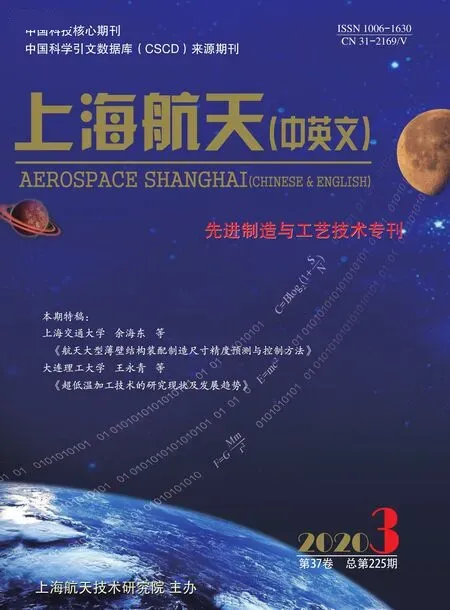熔融沉積成型連續碳纖維增強尼龍蜂窩芯材的壓縮特性
孫 靖,王旭琴,柳玉文,劉正武,趙 凱
(上海航天設備制造總廠有限公司,上海 200245)
0 引言
蜂窩結構芯材屬于結構型復合材料,具有輕質、高強等諸多優點,作為一種極具緩沖效果的結構,被廣泛應用于汽車以及航空航天領域[1]。蜂窩芯材具有極佳的能量吸收特性,在受到壓縮載荷時,蜂窩芯材可將載荷進一步轉向單元結構,單元結構通過變形傳遞將載荷繼續轉向屈曲單元[2]。屈曲單元可分為局部與整體屈曲單元,樣件的順應變形能力為局部屈曲單元的表現,而樣件的剛度則為整體屈曲單元的貢獻[3]。蜂窩結構緩沖原理在于它可將動能轉換成熱能、變形能或者是薄壁的破裂能等其他形式能量[4]。
當蜂窩結構受到壓縮載荷時,變形可大致分為3 個階段:彈性變形、平臺區域和緊實化區域。典型的壓縮過程力-位移曲線如圖1 所示。彈性區域主要是由材料本身決定的,隨后材料進入塑性變形階段,即平臺區域,在此過程中,載荷幾乎保持不變,平臺區域主要是由結構決定的,這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結構對能量的吸收能力。當所有的單元格被壓扁發生相互接觸時,即進入緊實化階段,這個階段載荷急劇增加,但位移變化有限[5]。

圖1 壓縮試驗力-位移曲線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rce-displacement curve of the compressive experiment
在能量吸收模式中,塑性材料的變形吸收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種,如金屬或高分子材料[6]。但是,金屬或高分子材料的蜂窩結構的精細制備為目前一大難題。傳統的蜂窩結構制備通常采用起皺和擴張的方法,這種方法限制因素較多,首先是不能制備特別細小的蜂窩結構。此外,采用傳統方法制備的蜂窩結構壁厚不可能完全均勻,且內部缺陷難以精確控制。因此,亟需尋求新的蜂窩芯材的制備方法,3D 打印技術的誕生為此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熔融沉積(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FDM)是一種應用較為成熟的非金屬3D 打印方法,其中,經加熱熔融的熱塑性絲材通過噴嘴擠出逐層累積形成零件,可實現直接由CAD 模型到零件的近凈成形[7-10]。FDM 可實現多種材料的直接成形,包括尼龍、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ABS)、聚乳酸(PLA)、聚醚醚酮樹脂(PEEK)等[11-13],其中不乏多種工業應用塑料成型。但是,聚合物的強度畢竟有限,無法直接與金屬匹敵。在此基礎上,實現連續碳纖維增強聚合物復合材料的成形,可明顯提升材料的服役性能。PEI 等[14]研究了碳纖維增強聚合物復合材料的3D 打印成形以及性能研究,發現長纖維增強聚合物復合材料的彈性模量和斷裂強度都得到明顯提升。GREGORY 等[15]研究發現纖維增強聚合物復合材料可使材料的彈性模量提升約20%~30%。孫振明等[16]研究發現連續碳纖維增強Mg 基復合材料抗彎曲強度可達到865 MPa。此外,連續纖維增強復合材料的FDM 成形為空間增材制造的實現提供了有效途徑。田小永等[17]開發了在線浸潤復合材料3D 成形系統,并為其在空間增材制造的應用方面做了較多的基礎研究。
綜上,大量研究基于蜂窩結構本身吸能特性或纖維增強復合材料的成形,本文將蜂窩結構與纖維增強兩種優勢相結合,研究了纖維增強蜂窩芯材的壓縮特性。采用FDM 方法成形連續碳纖維增強尼龍復合材料蜂窩結構,并對其壓縮過程的變形模式及壓縮性能進行表征分析,探索了連續碳纖維增強對蜂窩結構壓縮過程中變形過程及性能的影響,為連續碳纖維增強聚合物復合材料FDM 成形的空間增材制造提供理論依據。
1 試驗
1.1 原材料
蜂窩芯材采用MarkForged 公司開發的FDM設備(Mark Two)進行制備,原材料采用尼龍(Nylon-white),為MarkForged 公司開發的一種尼龍混合物,選用絲材規格為800 cm3。增強纖維采用連續碳纖維,規格為150 cm3。蜂窩結構單元格如圖2 所示,單元格長度l為3 mm,厚度t為0.5 mm。

圖2 FDM 成形蜂窩結構尺寸示意圖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unit cell size of the honeycomb cores prepared by FDM
1.2 FDM 成形
模型處理采用Eiger 軟件,將STL(STereo-Lithography)格式模型進行切片分層,規劃打印路徑,賦予打印參數后存儲為機器可讀格式。分層層厚為0.1 mm,填充率為50%,噴嘴加熱溫度為275 ℃,打印速率為35 mm/s。蜂窩結構為垂直于基板平面的方向進行成形。
蜂窩結構的外壁采用連續碳纖維增強,纖維鋪設方式采用回字形路徑,鋪設層數為2 層,模型處理截面及FDM 成形碳纖維增強尼龍外壁復合材料蜂窩結構如圖3 所示。材料輸送采用雙絲雙頭送給模式,形成的材料為連續碳纖維增強尼龍復合材料,本文中標記為CF/Nylon(Carbon Fiber Reinforced Nylon)。

圖3 CF/Nylon 蜂窩結構模型處理結果及成型圖Fig.3 Processing result and modeling diagram of the CF/Nylon honeycomb cores
1.3 靜態單軸壓縮試驗
靜態單軸壓縮試樣的尺寸為50 mm(X1)×50 mm(X2)×30 mm,由于結構的各項異性,對蜂窩結構的X1與X2方向進行準靜態壓縮試驗測試,如圖4 所示。試驗設備為Instron 5900,試樣放置在設備的固定壓縮平臺上,靜態壓縮速率為5 mm/min,最大壓縮量為50%。記錄壓縮試驗過程中的壓力與位移。

圖4 FDM 成形碳纖維增強蜂窩芯材壓縮方向示意圖Fig.4 Instruction of the compressive direction for the carbon fiber-reinforced honeycomb cores prepared by FDM
2 結果與討論
本文分別對FDM 成形的蜂窩結構CF/Nylon芯材進行了X1方向和X2方向的壓縮試驗,對壓縮過程中芯材結構的變形模式、力-位移曲線及結構對能量的吸收能力進行分析評估。
2.1 X1方向壓縮過程
FDM 成形CF/Nylon 蜂窩芯材沿著X1方向壓縮時的變形過程如圖5 所示。在壓縮試驗初始階段,試樣受到壓縮時表現為彈性變形,如圖5(a)所示。當壓縮量增大,達到d=10%時,首先試樣外壁發生明顯變形,其次局部六方單元發生輕微的變形與位移,如圖5(b)所示。仔細觀察發現,內部變形最初發生于蜂窩細壁的屈服、坍塌和變形,六邊形的蜂窩單元發生一定角度的旋轉,進而發生拉長變形和移位,六邊形單元演變形為帶有尖角的矩形,尖角的方向與試樣受力變形方向一致。六方單元發生向左或向右的旋轉,旋轉角度約為±45°。在壓縮變形過程中,由于載荷轉移,連續的六方單元變形形成折線形的變形帶,如圖5(c)所示。隨著壓縮量的進一步增加,變形條帶數量增多,方向基本與初始變形條帶呈平行狀態,如圖5(d)所示。當壓縮量進一步增加,±45°變形條帶在相互交叉時,形成互相交錯的“Z”形或“X”形條帶,如圖5(e)和圖5(f)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壓縮試樣的初始變形位置與外壁變形位置密切相關,起始位置比較隨機。
為更明確地表征蜂窩芯材X1方向壓縮變形模式,將壓縮變形過程的細節特征進行提取,如圖6所示。

圖5 FDM 成形CF/Nylon 蜂窩芯材X1方向壓縮變形過程Fig.5 Compressiv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FDM prepared CF/Nylon honeycomb cores in the X1-direction

圖6 CF/Nylon 蜂窩芯材X1方向壓縮變形過程示意圖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ressiv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CF/Nylon honeycomb cores in the X1-direction
具有外壁連續碳纖維增強的蜂窩芯材在壓縮變形過程中,首先是彈性變形階段,這個階段外壁的增強作用比較明顯,碳纖維的增強使得平臺載荷明顯提升。在塑性變形階段,外壁首先被壓潰,隨后為內部變形,主要是六方單元格的變形和重新排布,這個階段載荷基本維持不變,持續時間較長,即為力-位移曲線上的平臺區域,這段區域的面積決定了蜂窩芯材對能量的吸收能力。而六方單元格子之間交互作用變化越復雜,平臺區域持續越長,結構對能量的吸收作用也越突出[18]。
2.2 X2方向壓縮過程
CF/Nylon 蜂窩芯材X2方向壓縮變形過程如圖7 所示。與X1方向變形過程類似,在初始階段,材料處于彈性變形階段,當壓縮量達到d=10%時,試樣外壁出現明顯的彎曲變形,內部六方單元格發生輕微變形與移位,如圖7(b)所示。
隨著壓縮過程的進行,六方單元格薄壁發生屈服變形。經觀察發現,與X1方向變形不同的是,X2方向壓縮過程中,六方單元的變形與移位發生在水平方向。六方單元的上下夾角均被壓平,六邊形演變成被拉長的長方形。
隨著壓縮量的進一步增加,水平變形條帶數量增加,變形條帶之間呈現平行狀態。最終,CF/Nylon 蜂窩芯材平行條帶被完全壓潰,呈現互相平行的層片狀,如圖7(f)所示。與X1方向壓縮模式類似,外壁添加連續碳纖維可增加平臺階段載荷值,從而增加結構的能量吸收能力。

圖7 FDM 成形CF/Nylon 蜂窩芯材X2方向壓縮變形過程Fig.7 Compressiv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FDM prepared CF/Nylon honeycomb cores in the X2-direction
如圖8 所示,明確表征了CF/Nylon 蜂窩芯材沿著X2方向壓縮時的變形模式,與X1方向變形過程類似,在彈性階段,外壁增強作用比較明顯。與X1方向進行對比,X2方向結構上存在與壓縮方向平行的內壁結構,即六方單元的豎直內壁。

圖8 CF/Nylon 蜂窩芯材X2方向壓縮變形過程示意圖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mpressiv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CF/Nylon honeycomb cores in the X2-direction
在壓縮過程中,內部屈服開始即伴隨著豎直內壁的屈服與彎曲變形。如圖8 所示,壓縮變形過程中,蜂窩結構的變形為橫向逐層進行,因此,導致在平臺區域的變形過程中載荷將會發生規律性的波動。這是因為,橫向的六方單元的壓潰為連續過程,而在形成新的平行壓縮條帶時,需要更大的載荷,力值將會發生向上跳動,這將導致X2方向力-位移曲線平臺區域存在波浪形規律跳動。這將在壓縮性能小節詳細論述。
2.3 壓縮性能
FDM 成形CF/Nylon 蜂窩結構的壓縮力-位移曲線如圖9 所示。分別對比了純尼龍以及碳纖維增強尼龍復合材料不同方向的壓縮系性能。對于復合材料,X1與X2方向的最大載荷值差別不大,兩個方向的平臺載荷值也大致相同,X1方向稍高。仔細觀察發現,X1方向的力-位移曲線較平滑,而X2方向的曲線出現波浪形波動。這與試樣的變形過程密切相關,平臺區域主要涉及內部六方單元變形階段,如2.2 節所述,X2方向試樣變形過程中存在間歇性的六方單元豎直細壁壓潰現象,因此,平臺區域載荷值出現輕微波動。

圖9 CF/Nylon 及純尼龍蜂窩芯材壓縮力-位移曲線Fig.9 Compressive force-displacement curves of CF/Nylon and pure nylon honeycomb cores
純尼龍蜂窩結構的平臺區域載荷明顯低于CF/Nylon 復合材料,對比發現,連續纖維增強作用比較明顯,纖維增強作用使得彈性階段增長且平臺載荷值得到一定的提升,平臺載荷值提升約25%。后續將通過優化纖維填充路徑有望進一步提升蜂窩結構的綜合性能。
3 結束語
本文采用FDM 方法成形連續碳纖維增強尼龍蜂窩結構復合材料,并對其不同方向下壓縮過程的變形模式、壓縮性能進行了表征分析。兩個方向壓縮結果表明,X1方向的平臺區域力-位移曲線更加穩定光滑,更能適用于壓縮工況。連續纖維增強使得蜂窩結構在變形量達到20%后,內部單元結構發生變形移位,且平臺載荷值相較于純基體提升25%左右。對連續纖維增強聚合物復合材料的成形以及其空間也能夠用打下基礎。但本文僅對CF/Nylon蜂窩芯材的壓縮性能進行研究,對連續纖維的增強機理以及復合材料服役過程中增強纖維的變形移動等行為未進行深入研究。后續將對CF/Nylon 復合材料的制造過程控制及綜合性能進行全面探究,為空間增材制造應用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