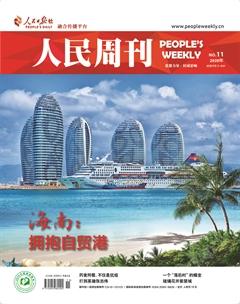被“遺忘”的勝利者
王磊
“明年最重要的大事就是衛國戰爭勝利75周年。”俄羅斯總統普京2019年12月13日如是說。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俄羅斯“2020年最重要大事”的具體安排,按慣例5月9日舉行的“衛國戰爭勝利日”大閱兵,被推遲至6月24日舉行。
同時,美歐一些政客別有用心的評論,成為紀念慶典場外的雜音。
“二戰始于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之時。”美國國防部在日前發布的題為《歐洲勝利日:慶祝與思考的時刻》的文件中稱。對于蘇聯為反法西斯主義所作出的貢獻,文件并未提及,白宮隨后發聲應和。美方此舉引發俄方不滿,一些俄羅斯網友用重新上色的蘇聯紅軍攻克柏林的照片回復白宮。
“我們不能原諒那些試圖篡改歷史的人。”普京說,一些國家試圖通過“篡改歷史”解決國內政治問題。
時間節點之爭
當地時間1945年5月8日午夜,納粹德國在柏林郊區卡爾斯霍斯特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此時,已是蘇聯5月9日凌晨,蘇聯和俄羅斯都將5月9日定為“衛國戰爭勝利日”。而美歐的二戰勝利紀念日則是5月8日。
事實上,雙方之間的隔膜,不只是紀念日的日期不同,在關于二戰歷史的記憶上,也存在很大分歧。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出自意大利學者貝奈戴托·克羅齊20世紀初期的著作《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被稱為“克羅齊命題”。其內涵為:人們總是從當前生活中的關切之處或所碰到的問題出發,去關注過去。過去是一片幽暗之地,當前生活中的關切就如同探照燈,決定了被照亮的是過去中的哪些部分。一旦從昔日的盟友變作今日的仇讎,當年并肩作戰的歷史也便有了截然不同的“記憶”和“解讀”。
每逢重要時間節點,關于歷史敘事的分歧可能就會更加顯化。2019年是西方眼中的二戰爆發(以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作為二戰爆發的標志)80周年,2020年是二戰勝利75周年,世界各地都密集舉行了相關紀念活動,但“視角”各不相同。
歷史敘事的美歐壓力
今年5月正值二戰勝利75周年,美歐一些主流輿論有意“遺忘”蘇聯在二戰中作出的巨大貢獻。白宮在社交媒體上發推說,美國和英國戰勝了納粹德國,美國精神永遠勝利。諸如此類的言論,引發俄羅斯方面強烈反應。
“盡管不是所有人都樂于見到我們取得的勝利,還有人試圖修改歷史的教訓,但俄羅斯不會允許任何人無視蘇聯在擊敗納粹中發揮的作用。”俄駐美大使安東諾夫5月9日說。
俄外交部5月10日發表聲明稱,在紀念二戰勝利75周年之際,美國試圖歪曲納粹垮臺以及俄羅斯在其中作出突出貢獻的歷史,俄羅斯對此表示非常憤怒。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俄美兩國總統此前發表的紀念易北河會師75周年的聯合聲明。俄羅斯和美國盡管存在分歧,依然可以在信任、相互尊重和考慮彼此利益的基礎上,共同應對日益增長的現代挑戰。
俄方希望與美國官員就這個問題進行嚴肅討論,敦促美方在當下俄美關系正處于“困難時期”的情況下,不要讓“有關1945年的記憶”成為兩國間的新問題。此外,俄羅斯還指責歐盟、波蘭和烏克蘭等淡化蘇聯在二戰中的作用。
美國無視俄羅斯在二戰中的作用,目的之一是以此拉攏以波蘭為代表的一些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長期以來在二戰歷史問題上與俄羅斯存在巨大分歧。特別是波蘭一直對蘇聯在二戰中的作用持否定態度,不承認蘇軍解放華沙。俄方則一直指責波蘭篡改歷史。這一分歧成為影響兩國關系發展的重要問題。
在二戰爆發80周年之際的2019年9月19日,歐洲議會通過有關《歐洲銘記歷史對歐洲未來的重要性》的決議,稱蘇聯與納粹德國1939年入侵波蘭,一起發動了二戰,呼吁在整個歐洲拆除蘇聯的戰爭紀念碑。
這份決議的要害在于,在歐洲層面將蘇聯與納粹德國并列,視其為二戰爆發的罪魁。但眾所周知,蘇聯是二戰和納粹德國發動戰爭的“受害者”,在二戰中失去了2700萬人口。
此后,普京多次反擊歐洲議會的上述決議,他在一次獨聯體峰會上指出:“歐洲的紀念碑是為蘇聯紅軍士兵而建的……這些人是為了把歐洲國家從納粹主義中解放出來而犧牲的。”
歷史記憶中的“安全困境”
正如美國戰略家基辛格所說,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不斷切割俄羅斯周邊傳統的“安全空間”,必然引發俄羅斯的反彈。在俄羅斯人眼里,保護自己國家安全必需的地理空間,是迫不得已的“反擊”和“自保”;而歐洲人和美國人總是習慣性表態稱,俄方對周邊鄰國的舉動是“強硬”“擴張”。
從根本上說,俄羅斯的“安全空間”及其當代認識,很大程度上由二戰所塑造。在俄羅斯人眼中,蘇聯在二戰中的歷史性貢獻不容抹殺,其巨大犧牲也不應被遺忘,捍衛二戰歷史中的蘇聯正面形象是正義之舉。但在美歐一些人眼里,俄羅斯為二戰歷史“正名”有別樣的政治含義。如2020年1月美國《大西洋月刊》指出,俄羅斯“貶低”波蘭,其目標是削弱波蘭地位,旨在破壞和動搖冷戰后的整個東歐政治安排,并修正冷戰給俄羅斯造成的地緣損害。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解讀二戰歷史的重點,則在于其想要的所謂“自由與奴役”的主題。美國自詡為自由的解放者、守護者,這符合其一貫主張的表面價值觀。對于二戰中犧牲極大、彼時還是盟友的蘇聯以及今天的俄羅斯,美國則避談、少談它們的相應貢獻,卻大談、多談蘇聯給東歐等國家帶來的所謂“奴役”。
今年5月7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的外長,就發表了一份這樣主題的聯合聲明,聲稱“雖然1945年5月在歐洲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它并沒有給整個歐洲帶來自由”,并反稱“操縱、涂抹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歐洲分裂的歷史事件,是令人遺憾的篡改歷史的行為”。
歷史與現實的吊詭之處
歷史不容篡改,也不應選擇性地“遺忘”。選擇歷史的某一點進而突出或者擴大成“面”,何嘗不是篡改歷史?美歐部分人可能忘記了,當年歐美各國是如何盼望著蘇聯出兵對抗納粹德國軍隊,如何希望蘇聯承擔更多的戰爭重擔。如今,他們對于蘇聯的戰爭貢獻卻閉口不談。
同樣,在東亞,美國出于與日本盟友的關系和現實政治需要,對于中國的二戰貢獻也有意“忽視”。他們中的很多人也似乎忘記了,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是如何感謝中國戰場拖住了龐大的日本軍隊。如今,他們對于中國的二戰貢獻卻惜字如金。
這恐怕是歷史與現實最吊詭之處。
解讀歷史與塑造歷史記憶,常常被用來滿足某些現實的政治需求。二戰在全世界范圍都占據著極其重要的歷史記憶部分。畢竟,是二戰結束開啟了全新的世界秩序,這種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直至今天,依然在影響著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
美國通過二戰確立了其在世界的霸權地位。解讀和定義二戰及二戰中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于美國既可以用作維護霸權地位合法性的歷史淵源,也可以用作打擊對手俄羅斯、團結歐洲盟友的一張牌。
從俄羅斯方面看,二戰相關結果依然關系到其在當今東歐地區很多安全主張的合理性,關系到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地位合法性的歷史來源。有分析人士指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常”席位,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各國在二戰中的的貢獻與犧牲。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歐、俄羅斯都不會放棄關于二戰歷史的話語權,這既關乎榮譽、道義、合法性與面子,更關乎現實地位、關系與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