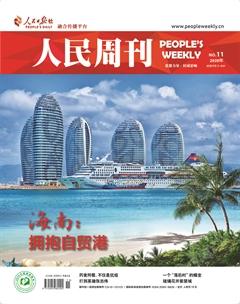鄭振鐸與10萬卷藏書
周鐵鈞
鄭振鐸,浙江溫州人,杰出的愛國主義者、作家、藏書家。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
他平生熱衷藏書,為傳承民族文化、保存珍典古籍作出非凡貢獻。40多年的不懈堅持、10萬卷藏書的坎坷經歷,堪稱中華藏書史上的雋永傳奇。
承傳好家風
1898年12月19日,鄭振鐸出生在浙江永嘉縣乘涼橋鄭家老宅。鄭氏家族是世代承傳的書香門第,清代就有高祖鄭元璧、叔祖父鄭允展等5位先人考中進士。
愛書喜讀的家風為鄭振鐸積淀下優秀的血脈傳承,他十幾歲念私塾時,就讀完了《三國演義》《岳飛傳》《水滸傳》等名著。40多年后他回憶說:“余素喜治流略之學,童稚時,不但通讀《漢書·文志》《古文觀止》等,尚手錄《隋書經籍志》《八史經籍志》等,時自省覽。”
1917年,鄭振鐸考入北平鐵道管理學校,課余最喜歡去瀏覽舊書市,眼望褐黃的書卷被風吹日蝕,深嘆自己無力拯救古人的珍貴典籍……他訂成一冊《求書日錄》,在扉頁寫道:“我要把保存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
從那天起,他發現善本、孤本、鈔本等珍籍,就把書名、作者、印刻年代、卷數等信息詳細記在《求書日錄》上,在北平讀書3年多,以史籍、詩文、戲劇、故事等分類,共記載古籍4800多種,為日后搜書、藏書積累了可靠依據。
手抄救孤本
1921年,鄭振鐸畢業回到上海,在商務印書館做譯文編輯。一次,他出差浙江鄞城(今寧波鄞州區),閑暇步入一家舊書屋,發現一套元代古籍《錄鬼簿》,這套書記錄了金、元兩代80余位知名雜劇、散曲藝人的生平和代表作。
他想買下,但店主要價過高,只得請求租閱,結果店主只允許他在店里看,不許拿走。恰好店主家樓上開客棧,他便租住樓上,雇來兩位謄寫快手,加上自己,3人圈在屋里兩天一夜,把《錄鬼簿》全部抄完。后來,這部原書佚失,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的《藍格寫本正續·錄鬼簿》,就是依照鄭振鐸抄本排印的。
1927年,鄭振鐸因投身反帝反專制斗爭,受到軍閥政府通緝迫害,不得不遠赴英法等國避難。到英國的第二天,早已抵達倫敦的舒慶春(老舍)、朱光潛等人為他接風,對他說:“這里的圖書館有許多從祖國掠奪來的古籍,你要去看一看,對藏書大有益處。”
當鄭振鐸走進大不列顛圖書館,果見難以計數的中國古籍。翻閱更為震驚,許多蹤跡難尋的孤本、善本,都默默躺在異國的書架上,他暗下決心:帶遭劫的中華民族智慧結晶“回家”!
但圖書館有嚴格規定:古籍只可閱讀,不許借走、抄錄。這難不倒鄭振鐸,他在閱覽室把古籍段落背熟,再到休息室默寫下來,后來覺得太耗力費時,便把白紙粘在大腿的褲子上,穿起大衣,坐在閱覽室偏僻角落,撩開大衣偷偷地抄。一個人太慢,就找老舍、朱光潛等人幫忙,在英國幾個月,抄得10多萬字珍貴孤本,還瀏覽了絕大部分中國古籍,并作了詳細記錄,回國后出版了《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等專著。
傾家購善本
1928年至1937年,鄭振鐸創作出版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等數十種專著,稿費所得換來了萬卷古籍。他購書、藏書不惜代價在文化界頗具名聲,當時的文史專家王伯祥說:“西諦買書之勇,世罕其匹,雖典質舉債,不恤也。”
1938年3月的一天,鄭振鐸在舊書店發現一套趙琦美手抄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趙琦美是明代“脈望館”藏書樓主人,萬歷年間,他竭力收集整理元、明兩代各類劇本,耗時3年多,手抄劇目242部,集成《甲編》《乙編》兩套共64冊《古今雜劇》,堪稱元、明戲劇大成,是彌足珍貴的善本。
他與店主楊壽祺討價還價,最終以1000元講妥。鄭振鐸拿出全部積蓄,變賣值錢家當,最后把呢子大衣、禮帽都送進了當鋪,才籌足款項。取書時他還托付楊壽祺幫忙打聽《乙編》的下落。
沒幾天,楊壽祺有消息傳來:《乙編》32冊在閘北“集寶齋”古董商孫伯淵手中。鄭振鐸急忙去找孫伯淵,誰知他也熱衷藏書,已尋找《甲編》多年,得知被鄭振鐸購得,竟提出兩個意想不到的條件:“一是我出5000元,買你的《甲編》;二是你出1萬元,買我的《乙編》。”孫伯淵想以漫天要價、給對方一筆賺頭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料鄭振鐸并未還價,一口應承出資1萬元購買《乙編》。
原來,鄭振鐸早有打算:賣掉自己的房宅,最少值兩萬元。但張羅出售不禁叫苦,當時上海局勢緊張,日本轟炸機常常掠過,防空警報不時響起,民眾惶惶,都無心購置房產。他只得四處托關系,把房屋抵押給銀行,拿到5000元貸款,急忙全部交了定金,并與孫伯淵簽下協議:余款一個月內付清。
此時的鄭振鐸,再也無力承擔巨額購書款,他請來好友張元濟(商務印書館總編)、程瑞霖(暨南大學校長)、張詠霓(光華大學校長)等人商議,終于湊足了5000元。
鄭振鐸購得全套善本,撰寫《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說:“得《古今雜劇》最為重要,它在中國文學寶庫、歷史文獻資料里是一個巨大收獲,這個收獲不下于‘內閣大庫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鈔本的發現。”
大隱隱于市
1941年12月,日軍攻陷上海,文化界許多愛國人士有的投奔陜北解放區,有的遠走重慶大后方,但人們卻不知鄭振鐸去了哪里,許多好友也不清楚他的下落。
1942年元旦剛過,上海居爾典路(今湖南路)一條里弄的二層小樓,搬來一位長衫禮帽、戴著圓眼鏡的新房客。不久,街坊得知他姓陳,是個書商。漸漸地,街坊發現,陳先生勤快熱情,每天晨練時都把弄口打掃干凈,鄰里有事總來幫忙,但他很少出門,只是躲在樓里看書、寫字。
上海淪陷前,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勸鄭振鐸去延安,那里是他多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數萬卷藏書如何帶走?幾經慎思,他還是下定決心留下來。他悄悄租好房子,在好友唐弢(后任《文匯報》副刊主編)的幫助下把藏書運來,除去家人,誰也不知他的居住地。
怕暴露行蹤,他不敢回家,家人也不敢來看他,濕冷嚴冬,獨自守書,仰望寒天朦月,他心中涌起陣陣傷感,慨嘆萬千,禁不住命筆疾書:“大地黑暗,圭月孤懸,蟄居斗室,一燈如豆。披卷吟賞,斗酒自勞,人間何世,斯世何地,均姑不聞問矣。”
在他心緒低落、思想灰頹時,上海地下黨組織通過唐弢轉告: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得知他冒險留在上海守護藏書,對他這種不顧個人安危保護文化遺存的精神十分欽佩,并帶來口信——一旦有危險,只要到指定地點,用暗號聯系,馬上有人安排他去蘇北解放區。中共黨組織和陳毅軍長的關懷,讓他備受感動,極大增強了藏書、護書的信念和決心。鄭振鐸在浦江灘頭陰霾籠罩、十里洋場血雨腥風的逆境中,忍辱負重、歷盡艱辛,護書、讀書、寫書,堅守了4年多。
鄭振鐸繁忙工作之余,把整理、閱讀藏書視為最大樂趣,他常常捧卷凝神,仿佛每套、每冊都是記憶的留存,都有難忘的故事。眼望一排排、一摞摞飽蘊歷史滄桑的珍籍古卷,他經常自語:“倘若我不在人世,這些書全是國家的。”
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團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不幸飛機失事罹難,享年60歲。他去世后,許多商家前來收購藏書,有的出價高達40萬元,但家人遵照他生前“這些書全是國家的”這一遺愿,把珍藏的94400多卷古籍全部捐給了國家,最好地實現了他生平的藏書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