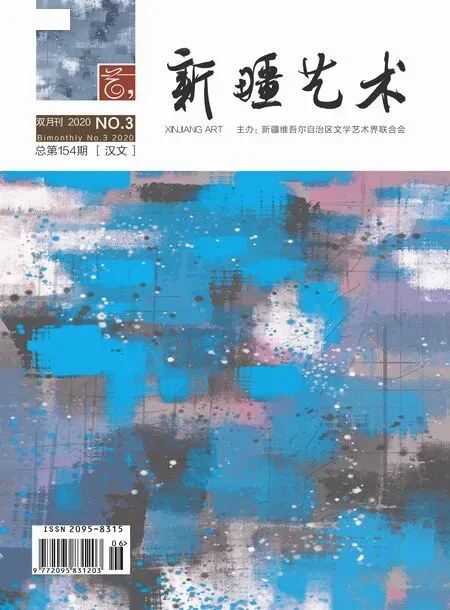試論李娟作品中的服飾敘事
□劉維笑

李娟
李娟自1998 年發(fā)表第一篇散文《山里的樹》開始至今,陸陸續(xù)續(xù)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從最開始的《九篇雪》到最近的《遙遠的向日葵地》,她的作品大致可被分為三個系列,即:阿勒泰系列、羊道系列以及向日葵地系列。其中,阿勒泰系列的散文作品包括《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著重敘述李娟一家人初到牧區(qū)的生活;羊道系列的散文作品包括《羊道三部曲》《冬牧場》,這個系列則將筆墨重點用來描繪哈薩克族牧民的游牧生活。而向日葵地系列的散文作品主要是《遙遠的向日葵地》,這些作品則是將關注點聚焦在母親在戈壁灘上開荒種向日葵的生活。
李娟的作品不但俘獲了不少讀者,也獲得了國內重大文學獎項評獎委員會的青睞。2011 年其作品《羊道》獲得了人民文學獎“非虛構類”大獎,2018 年她的《遙遠的向日葵地》又獲得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2019 年,《遙遠的向日葵地》榮獲自治區(qū)第六屆天山文藝榮譽獎。
獲獎是實至名歸,正如魯迅文學獎授獎詞所言:“她的散文有一種樂觀豁達的游牧精神。她的文字獨具性靈,透明而慧黠,邊疆生活在她的筆下充滿跳蕩的生機和詩意。”李娟的作品將北疆尤其是阿勒泰地區(qū)哈薩克族牧區(qū)以及農耕村落的民情風俗、自然風物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據(jù)筆者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關于李娟的研究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關于新疆阿勒泰這一地域風情文化的研究;第二,關于李娟族別以及地域文化身份的研究;第三,關于李娟散文創(chuàng)作方式手法的研究;第四,關于李娟散文文字語言風格的研究,此外,還有關于李娟個人成長以及對其作品進行生態(tài)批評的研究。
本文嘗試從敘事學角度分析李娟散文作品中的服飾,梳理她的代表性散文作品中有關服飾的敘事,并嘗試對這些服飾敘事的符號意義進行文化解讀。
一、李娟作品中服飾敘事概況
“衣食住行”乃人的最基本的四種需求。人們往往將“衣”排在第一位。這是因為相較于“食”、“住”、“行”,“衣”除了滿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還發(fā)展了人的審美需要。陳丕西在《服飾文化》中說,“避寒、遮羞、美化等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不斷地縈繞于原始人的腦際,潛藏在他們的心中,成為人類服飾發(fā)展的內在動力。”①可見,服飾對人而言是極其重要的。
關于“服飾”,《辭海》這樣解釋:“衣著裝飾”②。而《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將其定義為:“服裝及首飾。泛指各種人體妝飾,包括冠巾、發(fā)式、妝飾、衣服、褲裳、鞋履、飾物等。”③而今,服飾的含義與外延在不斷擴展,服飾不僅指服裝和首飾,還包括妝容、發(fā)型等。綜上所述,本文中的“服飾”概念范疇為四類:第一類是衣、裙、褲、帽等衣服類;第二類是耳環(huán)、戒指、項鏈、手鐲等佩戴的飾品;第三類是畫眉、涂唇、發(fā)型等人身體的裝飾;第四類是背包、傘具、扇子等具有一定裝飾性的實用物件。

李娟著作《遙遠的向日葵地》
而另一個概念“敘事”則是指源于俄國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兩種思潮、最早誕生于法國的一種研究學科即敘事學。“敘事學”最早由茨維坦·托多洛夫于1969 年正式提出。羅鋼的《敘事學導論》中將敘事學定義為研究敘事的本質、形式、功能的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包括故事、敘事話語、敘事行為等,它的基本范圍是敘事文學作品。
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說:“世界上敘事作品之多,不計其數(shù);種類浩繁,題材各異。對人類來說,似乎任何材料都適宜于敘事。在敘事遍布于神話、傳說、寓言、民間故事、小說……以這些幾乎無限的形式出現(xiàn)的敘事存于一切地方、一切社會。”④可見,敘事既可以是靜態(tài)的,也可以是動態(tài)的。
本文所指的服飾敘事,是指文學作品中關于人的服飾方面的描述。李娟的散文作品中關于人物的服飾描述有詳有略,服飾敘事在她的作品中承擔著不同的作用,或用來塑造人物形象,或用來表現(xiàn)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或用來表征新疆地域文化的象征意義等。
(一)一支耀眼的“大紅花”
《大紅花》這篇散文是李娟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為數(shù)不多的大篇幅進行服飾敘事的散文。她在散文中對“大紅花“衣著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
在這篇散文中,“大紅花”是一位五十多歲、頭發(fā)花白、身形高大的哈薩克族女性。不知為何大家都喊她“大紅花”這個有點莫名其妙的名字。文章著墨最多的是對她穿著的敘述,平日里“大紅花”衣著極為滑稽邋遢,“上面一件小了三碼的短背心,亮堂堂地露出肚臍眼,下面一條抹布似的長裙拖在腳背上。”⑤甚至,“大紅花”不按傳統(tǒng)套路出牌,不像其他哈薩克族婦女那樣穿襯裙,也不穿襪子,還套著一雙男式拖鞋……可以說這樣的“大紅花”是比較引人注目的,就連經常蹭飯的叔叔去一次也不敢再去“大紅花”家第二次了。但是,農忙時節(jié)放著高漲的工錢不賺,“大紅花”也要帶著一家老小去參加一百多公里外的阿肯彈唱會。而這時的“大紅花”又是另一番面貌了:“金絲絨的花裙子上綴了一層又一層亮锃锃沉甸甸的裝飾物。脖子上的珠串子粒粒都有鵪鶉蛋大。蕾絲邊的紫頭巾,銀晃晃的粗簪子。臉雪白、眉烏黑。還有靴子,擦得那個亮。”⑥
珍妮弗·克雷克在《時裝的面貌》中這樣描述時裝:“時裝常常被視為一種掩蓋身體或個人真相的面具,一種表面裝飾。我們可以將穿衣的方式看成是一種建構及表現(xiàn)肉體自我的積極過程或技術手段。”⑦“大紅花”確實將時裝當成了一種表現(xiàn)自我的手段。平日里干活不修邊幅的“大紅花”在去游玩休閑的時候可是極盡打扮裝飾自己的本事。通過衣著的裝飾,“大紅花”向世人展示了自己不同于平日勞動時的風采,一種獨屬于女性的、熱烈張揚的風采。
在這篇散文中,“大紅花”平日干活時不拘小節(jié)、衣著極不講究,但是閑暇節(jié)慶時候又極重視穿著,懂得美、在乎面子,懂得享受生活的性格特征通過李娟活靈活現(xiàn)的服飾描述成功地加以呈現(xiàn)。
(二)冬窩子里抗凍的“居麻”
在羊道系列作品中,《冬牧場》算是李娟的代表作,她自己也在序言中有此表述⑧。在這部散文集中,最惹人矚目的人物就是“居麻”,他有三個孩子,五十多歲,長得人高馬大,是個哈薩克族牧民,此人雖然是個喝了酒后會撒野的“酒鬼”,但他在不沾酒的大多數(shù)時候是個慈愛的父親,一個愛妻子的丈夫,更是一個風趣幽默不畏生活艱辛的哈薩克族大叔。他聰明自負、心氣高傲、勤勞能干、粗野不羈,但卻又善良溫和,在剛毅粗獷的外表下有一顆柔軟的心。
李娟對“居麻”的人物描述中,服飾敘事占了很大的比例,比如:“居麻除了一件很舊的皮大衣、兩件駝毛衣和一件羊皮坎肩,啥也沒有”⑨,穿上李娟為他縫制的羊皮褲后,“居麻”和鄰居的差距終于縮小了,心情大悅。即便是在冬窩子里放牛羊,即便是在天地蒼茫的黃沙和白雪上流浪,“居麻”這個五十多歲的哈薩克族大叔也會如同孩童一般鬧著要穿干凈的新衣服。搶奪干凈衣服不成的“居麻”只好穿上妻子翻找到的另一件干凈的舊夾克,他一邊穿這件舊夾克一邊不停嘮叨:“不給我好衣服穿,哼,我今天下午早早地就把羊趕回家來!……哎,穿成這樣這么臟怎么好意思在外面轉來轉去,被人看到了可怎么好!”⑩幾天后終于如愿穿上那件干凈的新衣服時,“居麻”高興壞了。當李娟問他穿這么好的衣服給誰看時,“居麻”用唱歌一般的調子說:“給綿羊看!給山羊看!”
如此,一個鮮活的哈薩克族牧民的形象便呈現(xiàn)在了讀者的眼前。他是如此的風趣,如此的富有生氣,他在冬窩子里穿著厚重的御寒衣物清晨歡快地趕著牲畜離去、夜晚歸來凍得幾乎不能言語的形象讓人難忘。
(三)向日葵地里赤裸的“我媽”
母親在李娟的散文中出現(xiàn)的頻率很高,尤其是在《遙遠的向日葵地》中更是圍繞著“我媽”在戈壁灘上開荒種葵花的艱辛不易展開。有趣的是,關于”我媽“的衣著,李娟描繪的比較少,但是卻飽含深意。
“我媽”平時在向日葵地里很少穿衣服。鋤地越干越累,越干越熱,于是一件件地脫下來,直至全脫完了。在葵花造就的叢林之中,她幾乎是“赤裸”的。她被太陽曬得黝黑,她與萬物似乎模糊了界限。千萬畝葵花迎著光的盛大表演中,只有“我媽”是觀眾,但同時她也是其中的一棵,她向光而生,她倔強又極富生氣,她在這荒野之中頂天立地地頑強地活著,“我媽是唯一的觀眾,不著寸縷,只踩著一雙雨靴。她雙腳悶濕,渾身發(fā)光。再也沒有人看到她了。她是最強大的一株植物,鐵锨是最貴重的權杖。她腳踩雨靴,無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榮、權勢鼎盛。”11
《遙遠的向日葵地》中有關“我媽”的這部分服飾敘事,可謂用意頗深,又極為成功。喬安妮·恩特維斯特爾在《時髦的身體——時尚、衣著和現(xiàn)代社會理論》中這樣界定身體與衣著:“人類的身體是衣著的身體。社會世界是著衣的身體的世界。衣著或飾物是將身體社會化并賦予其意義與身份的一種手段。”12在某種程度上衣著是自我與他人的界限,是個人與社群世界的界面,私人與公眾的交匯處。如此看來,身體不著寸縷的行為實則是一種頗具危險性的對社會規(guī)則的顛覆行為,也模糊了自我與外界的界限。“我媽”在貧瘠廣袤的大地上苦苦追尋生活,在萬畝葵花叢中尋找生活,她屢敗屢戰(zhàn),如戰(zhàn)士,如女神,如豐碑。她在葵花地里干活時的“不著寸縷”已然是對生活坎坷挫折的一種反抗。但從另一種角度來講,亦是與大地萬物的相融相生。這是她一往無前的奮勇,也是不顧一切的灑脫和豁達的表現(xiàn)。
(四)那些“不穿”衣服的人
李娟的作品中有關于人物服飾的敘述描寫,也有完全沒有服飾方面描述的“不穿衣服”的人,在筆者看來,這也是服飾敘事的構成部分。她的另一部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中,一篇關于一家哈薩克族鄰居的散文,涉及對大人以及孩子的描述,則完全沒有相關的服飾敘述。
這篇題名為《葉爾保拉提一家》的散文,講述的是這家鄰居孩子十分可愛,孩子有粉白的臉蛋,有蝴蝶展翅似的長睫毛,有靈動美麗的大眼睛……但這樣可愛的孩子偏偏沒有任何關于他穿著的描述。李娟看著這個五歲大的小男孩很想為他畫幅肖像畫,但幾經周折這個小男孩就是靜不下來,最終還是克服困難畫了出來。小男孩的媽媽則是一位體態(tài)豐腴的哈薩克族少婦,她力氣極大,干活利索。盡管人高馬大但是跳起“黑走馬”來魅力四射。在對這兩個人物的描述中,不管是要畫肖像畫的細節(jié)展現(xiàn)還是要哼著調子跳舞的場景描述,李娟都沒有關于他們的衣著服飾的描述。
這樣完全摒棄掉服飾敘事的“不穿衣服”的人物在李娟的作品還有很多。相較于有服飾相關描述的人物他們是另一種存在。珍妮弗·克蕾克《時裝的面貌》中談及到“服裝建構了個人習性”,而《葉爾保拉提一家》這篇文章中所有的人物都沒有關于服裝的描述,這樣讀者在某種程度上對人物的理解就沒有那么深刻。
二、服飾敘事在其作品中起到的作用
(一)服飾敘事的人物塑造功能
一般而言,小說等敘事作品需要通過人物的語言、服飾等的描述來塑造“典型人物”,而敘事散文中的服飾敘事則會使人物形象更加具體生動。羅蘭·巴特在《流行體系:符號學與服飾符碼》中將服裝分為三類:意象服裝、書寫服裝和真實的服裝。意象服裝是指人通過攝影或繪圖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的服裝。書寫服裝是指通過文字語言描繪出的服裝。真實的服裝是指現(xiàn)實生活中人穿的衣服。而書寫的服裝中語言描述能起到認知層面固化、傳遞知識信息和刻意強化的功能。可見服飾敘事可以加強人物形象的塑造,固化讀者對所描述人物的認識,使讀者接收到更多人物的相關信息,進而達到其突出某個人物或人物身上某個特性的目的。
干活時邋遢得讓人不忍直視的“大紅花”,在休閑時一身精致艷麗的打扮惹人注目。這位五十多歲的哈薩克族婦女的形象,通過李娟在散文中對其穿著打扮習慣的描述躍然紙上,顯得十分生動逼真。讀者通過李娟對“大紅花“的衣著描述了解到這位哈薩克族大媽生活習慣以及性格的不同側面。
無獨有偶,另一位在冬窩子冰天雪地里放羊的哈薩克族大叔,也是通過李娟對其服飾穿著的描述,在作品中樹立起自己的形象。這位在荒野中艱難求生的大叔幾乎將各種能夠御寒的衣物都穿在了身上,即便這樣,放了一天的羊回來的他還是凍得半天緩不過來。身材魁梧的他早已年過半百,但就算是在荒蕪蒼茫的地窩子里,就算方圓千里都遇不到一個人,他還是搶著要穿一件洗干凈的新衣服。哪怕是穿上只能給山羊看給綿羊看。這樣一位性格活潑、對生活滿是熱愛的人怎能讓人忘記呢?
同樣,“我媽”這樣一位從蜀中遷徙到新疆阿勒泰地區(qū)的女性,幾乎不著一縷地在葵花地勞作的形象更是讓讀者印象深刻。她剝離了一切外在的羈絆包括衣物,她赤身屹立于天地間,在李娟眼里,她是一位孤身駐足田野間辛勤勞作的、偉岸的女性形象。在貧瘠荒蕪的大地上勞作,她渾身自帶光芒,她跟周遭的自然萬物間幾乎沒有邊界,她如同向日而生的葵花,頑強豁達,她甚至成了大地之母的象征。
(二)服飾敘事側面表現(xiàn)生存環(huán)境的功能
與李娟的其他散文集相比,《冬牧場》中出現(xiàn)的人物幾乎都有衣著的描述。倒不是這人的穿著有多么美或者多么與眾不同,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穿”之于極寒自然環(huán)境中生存的群體而言顯得比“吃”、“住”、“行”更為重要,成了在冬窩子的黃沙與白雪之間生存下去的前提。
呵氣成霜,寒風呼號,在一望無際的寒冬荒原上,人對溫暖的向往成了一種本能的追求。如何凸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寒冷與惡劣?除了正面的環(huán)境描述之外,更好的寫作策略便是通過對環(huán)境中的人的服飾穿著描述來烘托體現(xiàn)。
相較于其他系列散文中的“我”的“零服飾敘事”的出場,《冬牧場》里的“我”的穿著描述幾乎成了該散文作品中的重頭戲。“我”出發(fā)的時候帶了多少件厚衣服,到了“冬牧場”后,“我”如何毫不顧及形象,里三層外三層地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裹身上,如何為了抵抗寒冷,晚上也不脫衣服就鉆進睡袋睡覺。不光是“我“,“冬牧場”里幾乎所有人物都被李娟這樣進行服飾敘事。
華梅在《中國服飾》中這樣界定服飾“服飾的面貌是社會歷史風貌最直觀最寫實的反映”13,事實上服飾不但是社會歷史風貌的反映,它更是自然生存環(huán)境最直觀的反映。阿勒泰地區(qū)冬窩子自然環(huán)境的荒涼與冷酷通過李娟筆下人物的穿著就可以直接地反映出來,“我”里三層外三層地穿衣服毫不顧忌美感,夜晚睡覺也不敢脫了厚外衣,“居麻”穿上皮毛棉褲腿幾乎打不了彎……這些人物的穿著比文字的直接描述更能說明生存環(huán)境之惡劣。
李娟以一個新疆本地人的身份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隨母親在荒野中開墾,跟隨哈薩克族牧民逐水草而遷徙,她主動拉開與棲身之所的審美距離,她在記游的同時加入了想象的元素。她讓《冬牧場》中的的嚴寒與荒涼都帶有了審美的屬性。
在極度寒冷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面前,人顯得如此渺小卑微又異常脆弱。可盡管如此,對抗嚴寒的人還是頑強地熬過了所有的冬天,熬過了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帶給人的嚴酷考驗。如此,那些穿著厚重衣服的人物無疑更加令讀者敬重。
(三)服飾敘事的象征意味
在李娟的散文代表作《冬牧場》中,“居麻“這個父親讓人印象深刻,但他的女兒“加瑪”同樣令人難忘,這使得關于她的服飾敘事多了些許象征的意味。
比如,散文中描述剛入冬窩子的“我”發(fā)現(xiàn)“加瑪”戴著夸張的、粗制濫造的紅水鉆耳環(huán)和假的金戒指,一時間無法理解在荒野中這種“愛美”的表現(xiàn)。在蒼茫的荒野中,吃穿都能難以保證的惡劣環(huán)境中,比起吃喝“加瑪”卻更在乎她的紅水鉆耳環(huán)和假的戒指。即便是要拿著編織袋去背雪回來化水做飯,或者是去撿牛糞,加瑪在從事這樣繁重的體力勞動時還是要佩戴著她的首飾。
不僅如此,“加瑪”只要是有機會見到別的人,回定居點或者去別的牧民家串門前,她都要花很多時間收拾自己,用極難獲得的水,仔細洗干凈自己的頭,還要往頭發(fā)上抹桂花頭油。最后,再換下自己干活時穿的臟衣服,換上漂亮的衣裙和鞋子。哪怕忍受寒冷也要穿上最好看,最體面的衣服、鞋子。
羅蘭·巴特在《流行體系——符號學與服飾符碼》中指出了服飾敘事的修辭功能,即服裝詩學。“一件衣服的描述(即,服飾符碼的能指)即是修辭含蓄意指之所在。這種修辭的特殊性來源于被描述物體的物質屬性,也就是衣服。或許可以說,它是由物質和語言結合在一起決定的。這種情形我們賦之以一個術語:詩學。”14這種由服飾敘事營造的詩意之美即為一種服飾帶來的象征意義。
不管是“加瑪”的紅水鉆耳環(huán)還是假的金戒指,抑或是她出門前梳頭用的桂花頭油,都成了這位哈薩克族女孩性格的一種象征,成了她青春愛美,熱愛生活的一種表征。這種在大地上趕著牛羊逐水草而居的開闊豁達的民族性格與對尊嚴體面的追求,通過“居麻”對新衣服的渴望、“加瑪”執(zhí)意佩戴首飾體現(xiàn)出來,而他們的服飾裝束抽象成為一種詩意的美感。
(四)服飾敘事的留白意韻
當“服飾敘事”不在場時,它在李娟的散文中扮演的則是另外的角色,提供一幅“留白的意韻”,并給讀者更多想象的空間。
珍妮弗·克雷克在《時裝的面貌》中闡釋穿著與人的習性之間的關系時這樣表述:“我們通過裝扮身體將自己呈現(xiàn)給社會環(huán)境,通過時裝顯示我們的行為準則。我們的服裝習性產生了一種‘面貌’,這種面貌積極地建構了個性。”可見服裝對于展示人物習性有重要的作用。反之,如果文學作品完全省略掉對人物的服飾描述,在某種程度上人物的性格或者形象則是空白的狀態(tài)。
在李娟的散文作品中對“我”的服飾描述,既有具體穿著細節(jié)的描寫,也有完全一筆帶過的服飾描寫,甚至有完全不提及服飾的情況。完全不提及服飾的時候,“我”的形象則是留白的狀態(tài),盡管對其有不少動作或者情態(tài)的描摹,甚至有情緒語言的描述,但沒有衣著服飾的具象描寫,這個“我”的形象仍然是留白的狀態(tài),是極簡的線條勾勒出的一部分的“我”,具體的形象需要讀者自己去補充想象。
除了我之外還有“我媽”、“姥姥”以及諸多其他出現(xiàn)在李娟作品中的人物。比如《阿勒泰的角落》中《看著我拉面的男人》這篇散文中關于那個“男人”的描述完全沒有服飾敘事的痕跡。
散文中描寫道,在一個偏僻的小村落,“我”在家手忙腳亂得拉面,狼狽不堪時偏偏八百年不一遇地來了個陌生的“男人”毫不客氣地觀摩。關于這位男人的描繪是這樣的:“這人也就三十來歲的樣子,又高又瘦……也具備牧民的某些特征:面孔黑紅,雙手骨骼粗大,舉止和目光都十分安靜、坦然。”15這樣一位男子坐在那里像是看表演一般看“我”滑稽地拉面。在這段描述中,讀者對這位男子的服飾裝扮一無所知,對這位男士的描述如同一幅簡筆肖像畫,只是勾勒局部,身體衣物的敘事細節(jié)全無,大片留白,反而為這位人物的出場留出余味未了的意韻。
三、服飾敘事的意義以及局限
總的來看,李娟的散文中關于服飾敘事的描述并不算多,但是這些已有的服飾敘事完成了其相應的功能。服飾敘事在李娟的作品中為渲染哈薩克游牧文化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性格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通過這些服飾敘事,哈薩克族的熱情好客、樂觀豁達、不拘小節(jié)以及追求榮譽的價值觀被生動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
不但如此,散文中,這些有關人物衣著打扮的描述也從側面襯托出新疆這個西部邊陲地區(qū)獨特的地域風情。冬季的寒冷,地域的廣闊,人煙罕至的空曠與孤寂……等等,如同神來妙筆,李娟在散文中通過服飾敘事,巧妙地展現(xiàn)出這片土地的風土人情。
喬安妮·恩特維斯特爾在《時髦的身體——時尚、衣著和現(xiàn)代社會理論》中認為衣著為身體的自我劃定基本框架,衣著是身份的一種視覺隱喻,衣著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文化積淀而成的纏繞著身份認同的那種矛盾心理。衣著可以說是他人解讀自己或自己解讀他人的一種符號。從這個角度來看,李娟筆下那些服飾描寫充分的人物在社會身份認同以及對自我界定上更加清晰。
同樣,正是因為身份的自我界定和他人界定在某種程度上由衣著裝束來幫助完成,李娟筆下的“大紅花”“居麻”以及“加瑪”等人物才如此地重視自己的穿著,即便是再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中也要爭取自己的“體面”。他們穿洗干凈的衣服或是梳整齊的頭發(fā)來張揚自我,來求得肯定與認可。
從人物刻畫的角度而言,李娟散文中有關那些“不穿衣服”的人物描寫,除了留給讀者以想象的空間、獨具特殊的意韻之外,也存在模糊不清的弊病。相比于那些有具體服飾敘事的人物描寫,零度服飾敘事的人物形象顯然不能令人記憶深刻,人物的“習性”以及社會身份等難以更充分地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