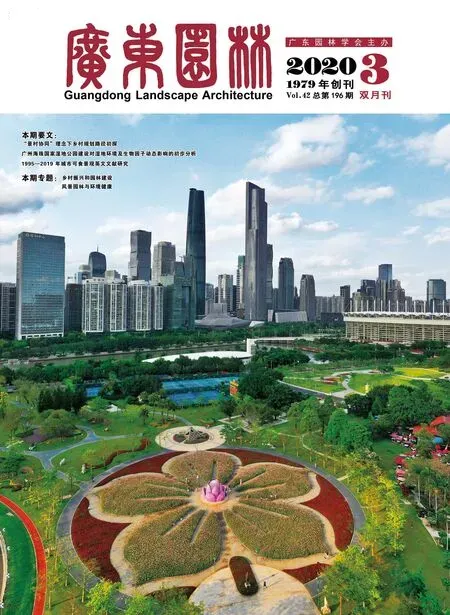基于“言象意”思想的上海方塔園詩意空間營造研究*
鄧濤 侯則紅 陳展川
“言象意”起源于《易經》,成形于《易傳》,其相關問題的探討,最先是從哲學層面開始的,是思辨語言如何在思維中運用及其能否充分表達思維的問題[1]。古人試圖用“象”來協調“言”與“意”之間的矛盾關系。《易經》中的卦形來自于對客觀事物的模擬,欲指某種物理、事件或哲理,即用圖象來呈現意蘊。但《易經》中的“象”雖然來源于客觀世界,且具有承載“意”的作用,但卻沒有加入主觀抽象的思想與感情,所以其并不是詩歌藝術中的意象,但卻為詩歌藝術意象的萌發提供了理論基礎。孔子在《易傳·系辭上》中有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語言符號無法完全地表達出曲折深遠的“意”,而具體的“象”卻可以把內涵與精神性的東西以極其有韻致的方式表現出來。《易傳》對《易經》中意象內蘊的說明,為中國傳統詩學意象論的生成奠定了基礎。在“言象意”系統引入文論中之后,人們仍然以“象”為中介來考察“言”“意”之間的關系,但“言達意”的局限性并沒有被認為是文論中的弊端。南朝文論家劉勰認為,如果沒有語言,構思中的意象就不能被思維所把握,即“神與物游”的“物”必須通過語言的形式才能表達出來[2]。所以一個文學作品的產生需經過“意”“象”“言”3個階段,即醞釀文學作品、具體構思、形諸物質載體的語言[2]。而在園林詩意空間的營造中,同樣需遵循立意、取象與盡意的“意”“象”“言”3個階段,即創作者構思的含蓄、深遠與抽象的“意”,需通過主客觀融合而形成的園林意象來承載,并最終以山石、水體、植物與建筑等具體的“言”來呈現。其中意象作為由“言”達“意”的中介,是園林實體景象向造園立意轉化的過渡環節。
1 園林詩意空間的營造方法
1.1 立意
“意在筆先”的命題來源于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中“意在筆前,然后作字”的論述,表示在動筆書寫之前要凝神靜思字形的大小、平直與振動等,使其經脈相連,從而才能完成一幅好的作品。之后,“意在筆先”的命題滲透進繪畫與園林等其他藝術領域中。張家驥與孟兆禎先生認為園林意境的創作,要做到胸有成竹,意在筆先[3]。立意是造園的方向和目標,是意境創造極為重要的環節。立意不僅是依據功能需要、藝術要求、環境條件等形成的設計思想,也是構思設計意境的過程。傳統園林是心靈化的園林,在儒家倫理道德“天人合一”觀、道家非倫理道德“天人合一”觀及佛家“心源”“體悟”等理論影響下,其立意表現出了園主人的世界觀、人生觀、藝術修養與人格涵養。
1.2 取象
山水、植物、建筑等造園要素作為傳統園林“言象意”系統中的“言”,其在直接表達造園立意的時候具有極大的局限性。而“象”是飽含審美主體意識與內在情感的主客觀融合的意象,即造園家在審美感知過程中,借助聯想與想象,將情感和思想等主觀因素注入到具體的“言”中所塑造成的主體意識中的虛象。如揚州個園的四季假山,造園家通過聯想與想象,將自己對于自然四季特征的感悟與理解,融入色澤、質地與形態不同的石材與花木等具體造園物象之中,從而營造出體現不同季節特性的四季山景審美意象。意象是主客觀的融合,所以其受主體生活態度、審美情感、人生經歷與文化歷史等種種方面的影響。
1.3 盡意
“盡意”分為2個部分,首先是創作者立意的物象化,其次是欣賞者物象的精神化(圖1)。園林創作者與觀賞者之間“意”的交流需以審美意象為中介,以具體的園林空間與景象為物質載體[3]。在造園過程中,需將要表達的較為抽象與復雜的主題思想或意境氛圍轉化為意象,并最終通過山石、建筑與水體等造園要素來呈現。因為欣賞者只能通過具體的、與立意美學特性相符合的、審美感受強烈的空間景象來與創作者產生共鳴,所以將意象轉化為具體實景是造園中非常重要的步驟,是從意境中追求畫境的過程,主要使用的手法是聯想與想象。古人為解決園林之“言”對于“盡意”的局限,常常采取景物擬人化、景象圖案與符號化,由于園林語言表達存在局限,故常借助文學語言,采用題詠作為一種點題方式來引導“意”的表達[4]。獅子林的臥云室位于假山中央的頂端,群峰環繞,寓意遠離凡塵的佛家須彌山“靈界”,而假山象征佛家須彌山,臥云室前的小橋寓意“俗界”與“靈界”的界限,并用“臥云”二字引導人們的聯想與想象,整體營造出禪宗隱逸的意境[5]。如若不是“臥云”二字的引導,欣賞者很難將高約10 m、面積僅1 153 m2的假山與須彌山聯系起來。
2 方塔園案例分析
方塔園是上海園林局委托馮紀忠先生設計的1座以宋代方塔古建筑為主體的歷史文物遺址公園,位于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上海市松江縣。在遺跡方面,方塔園內具有北宋九層古塔建筑、元代石板橋、明代磚雕照壁,以及因市政工程遷入的明代楠木廳與清代天妃宮大殿等歷史文物。在自然要素方面,原有竹林2片、古樹8棵及1條貫穿東西且具有丁字形河汊的小河。對于方塔園的設計,馮紀忠先生不僅思考了如何展示遺跡與歷史文化,同時思考了如何使傳統文化合理的存在于現代生活之中的問題[6]。
2.1 立意
宋代文化承前啟后,既傳承了唐代文化的精華,又是元、明、清代文化深化與分化的起點。在寬松自由的政治氛圍中,宋代文化取得巨大的成就,其文化精神普遍趨于追求個性的表達。宋代文化注重個人內心情感的表達,趨向平淡素雅、淡泊寧靜。在“理學”思想的影響下,宋人崇尚天然真實與樸素的自然之美,進而反對雕琢偽劣[7]。宋塔尺度大,年代久遠,造型優美,且蘊含著宋代的樸素韻味,是整個園區最有價值的存在,亦是最重要的景觀,對園內空間具有重要的限定作用(圖2);且宋代的文化精神是現代社會仍然需要的,其能與如今的人們產生共鳴[8]。所以馮紀忠先生將宋塔確定為全園的主體,總體上營造出宋代樸素、典雅、寧靜與明潔的意境氛圍。在傳承與發展上,馮紀忠先生提出“以古為新”,即使整個園區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滿足歷史文化園林的功用需求,具有時代精神,同時又具有宋代文化的意境。“古”并非完全在于形式上的模仿,而在于宋代的精神,即意境、韻味上的拿捏。其認為整個園區是為了展示宋代的文物,突出宋代的韻味,那么從整體布局、空間組織及每個細節都要體現出宋代文化的韻味,呈現出一種東方文人的詩意境界[8]。

圖1 盡意流程分析

圖2 宋塔及塔院院墻

圖3 大草坪
2.2 取象與盡意
馮紀忠先生認為意境的營造需要理性分析與感性激發2條線的并行,具體的“形”與“象”組成的意境是環境、結構與構造等理性因素與感性審美并行的粘合劑[9]。意象的積累或組合生成意境,意象是主客觀融合的產物,而不是設計師自己想出來的,意境也不是最后才突然出現的,而是醞釀出來的。方塔園的山水意象提取于松江地區河湖水網交織與局部山巒起伏的地形條件[6]。山水骨架不僅起著呈現地域地形特征的作用,還將全園劃分為北面的天妃宮、南面的大草坪(圖3)、西面的楠木廳與東南面的何陋軒等幾個不同特色的功能空間,同時擴寬的大水面能很好地倒映方塔,從而增加空間的層次感,形成虛實結合的空間。通過馮紀忠先生的布置,宋塔這件珍貴的“展品”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了其風韻。主體建筑宋塔所處位置地勢低于周邊環境,不利于營造高聳、巍峨、肅穆與素樸的空間氛圍。在方塔園廣場的設計中,為了突出主體建筑與營造意境,其在宋塔的南面與東面設置院墻,用以規避視線觸及塔基從而帶來的低陷感,并營造了塔院的圍合之感(圖2)。北入口的甬道與東入口的塹道高低起落,同樣起著模糊觀賞者對于塔基所產生的地形低陷感(圖4~5)。為了不分散觀賞者的注意力,使其能融入場所空間,并與宋塔產生情感上的交流,馮紀忠先生采用“冗繁削盡留清瘦”的減法原則,使院墻呈現出簡潔的形式,庭院內不植一木,且避免其他建筑物的出現,從而確保宋塔的主體地位,營造樸素、肅穆、靜謐與明潔的意境[6]。遠處土丘之上種植形態蒼古的常綠樹木,作為宋塔的屏障,起著屏蔽影響意境表達的物象與烘托主體的作用,從而獲得典雅與寧靜的意境氛圍。
何陋軒屋頂的意象提取于松江當地正日益減少的傳統民居四坡頂彎屋脊形式,馮紀忠先生用現代建筑設計手法演繹出了當地民居的建筑形式。整個建筑由竹子與稻草組成,以竹子演繹現代鋼架結構作為建筑的承重結構,以稻草覆頂,既體現現代感,又具有回歸自然的感覺。“建構”是一個包含技術、結構、工藝與材料等諸多方面的綜合體,是一種“求意”的建造方式[10]。在接受《A+D》雜志提問時,馮紀忠先生認為“建構”不僅是詮釋木、石材等如何結合的問題,同時也是有關材料、人為因素的問題,即將人的情感融入細部處理之中,從而使“建構”凸顯出來[10]。何陋軒的設計理念就充分體現出了“建構”的“求意”思想,其使用黑色的構件連接竹結構,給人造成竹桿斷開的視覺錯覺,就像竹竿漂浮在空中,從而產生飛動的感覺。另外,何陋軒自由布置的弧形墻體,起著粉墻弄影的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光影也不斷變化(圖6)。幽靜的環境與飛動的建筑,營造出了一種動靜相融的空間(圖7),呈現出了馮紀忠先生精密的理性思維與豐富、感性的詩性思維。何陋軒不僅與園內景物相聯系,同時也延續了松江民居的歷史文脈,并且體現了時代特征。
3 方塔園對現代詩意空間營造的啟示
3.1 自然與生態精神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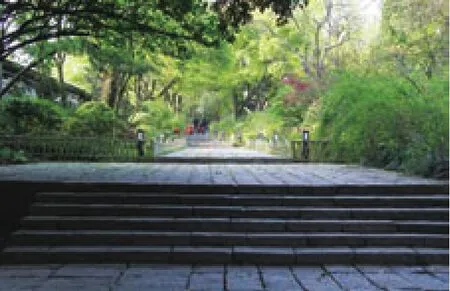
圖4 甬道

圖5 塹道
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與哲學觀的影響下,自然成為中國傳統和現代人心里的一種原始意象,人們對于自然有著特殊而統一的情感。由于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生活節奏的逐漸加快,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更加需要走進自然來調節心理壓力、陶冶情操以尋求精神的解脫。方塔園因地制宜,尊重場地現狀,營造了一個天然真實與樸素自然的園林空間。將原有水系局部拓寬以倒影宋塔,采用以土帶石的形式在原有土丘的基礎上進行堆疊,形成土山,進而形成園區的山水骨架。全園土丘自東向南形成脈絡,水系南面之山隨勢降坡,并緩坡入水,形成的大面積草坪不僅增加了自然山水的效果,使園區環境更加自然,同時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休憩與活動的親水休閑空間。除了山水骨架,現在清幽的竹林景區也是在原有竹林的基礎上規劃建設的。保留下來的古樹名木,作為園區的景觀樹,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價值。
生態問題的提出,來源于人與自然環境矛盾的沖突。具有生態意識,可以發揮園林空間的生態服務功能,進而改善生態環境。由山、水、植物等構成的自然生態環境作為園林“言象意”系統中的“言”,是園林詩意空間中的“意”能得以呈現的物質基礎。所以園林詩意空間的營造需注重自然與生態精神的追求。中國傳統園林順應自然、融于自然等造園法則無不體現出古人的生態意識。而方塔園作為一個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現代詩意空間,既體現出了順應自然與融于自然的審美意識,也展現出了生態意識。園區的山水骨架具有涵養水源、調節局部微氣候及凈化空氣的的作用,拓寬的水域、大面積的草坪及綠化具有調節區域洪澇災害的作用。
3.2 傳統文化的提取
隨著實踐的檢驗,照抄照搬、符號變化與文化隱喻等手法越來越受到詬病,被證明為淺層次的、表面的模仿。沒有承載主觀抽象思想與情感的物象不能成為意象,所以對于傳統文化元素的提取,不能僅表達物質方面的內容,需主客觀融合,才能創造出由“言”達“意”的意象中介,進而承擔起由實體景象向造園立意轉化的過渡作用。馮紀忠先生的方塔園展示了現代空間意境的魅力,證明了意境不僅是傳統園林的最高審美追求,其也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并能體現出民族特征。先生說過,傳統并非完全顯現在形式上,而是意境上的一些味道,味道匹配,就有意境了[9]。意象是組成意境的基本元件。方塔園整體宋代韻味的呈現,就是由一個個具有宋代文化韻味的意象所組成。意象不是設計師主觀想出來的,而是設計師主觀的精神情感與客觀具體物象融合的結果。方塔園注重從傳統、歷史、地方與民間等方面尋找靈感,并將其提煉用于新的設計之中。其意象提取于場地內的人文環境與區域內的民居建筑形式,具有豐富的審美特性與歷史厚度。現代園林意象的提取應有合適的來源,而不是憑空捏造,應提取于場地內或相關地區的自然環境與文脈、地域歷史文化、歷史典故與文學創作等方面。
3.3 現代資源的運用
傳統園林是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一定歷史條件下逐漸形成與發展起來的,而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也理應形成符合現代審美與需求的現代園林。現代園林的詩意空間營造應以傳統園林為基礎,并從現代的角度系統闡述傳統的概念,使其符合現代的審美,照抄照搬顯然不符合時代精神。詩意的棲居,并不是號召人們像古人一樣生活在傳統園林中,而是生活在具有詩意的現代園林之中。馮紀忠先生用現代的手法、材質與結構營造了方塔園這樣一個現代的詩意空間:采用了現代簡潔、疏朗與明快的布局,園路以直線或弧線為主,舍棄了傳統園林刻意追求的曲折多變,并增加了來源于西方的大草坪和塔前廣場;新建的建筑在體現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表現出很強的時代特征,通過現代建筑材料或工業化構造技術完美呈現了現代建筑的空間品質,如何陋軒使用的竹為傳統材料,但建構的是嚴格的理性結構。用現代結構重新詮釋傳統材料之美,是現代資源應用的優點之一。現代詩意空間是使用現代材質、手法與技術等現代資源,營造出傳統與現代結合、東方與西方結合、符合現代審美、服務大眾的空間。現代資源的使用,最終都需通過園林“言象意”系統中的“言”來體現,并呈現出園林詩意空間的現代性與時代特征。
3.4 詩性思維的參與

圖6 何陋軒弧形墻體

圖7 何陋軒
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是一種高度凝練的語言藝術,其并不像畫作一樣給人以直觀的視覺感受,而是運用詩性思維,將語言轉換成的意象組合起來形成意境,才能供人們品味與賞析。詩性思維是一種將主觀精神過渡到客觀事物,從而創造一個心物融合的主體境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創造性的、感性的、形象性的與非邏輯性的思維方式[11]。古代詩性思維是一種空間思維,其跳躍性、多維性與含蓄性等特征給人營造了一種空間感。意象與意境所創作的意蘊深遠、回味無窮的審美空間,則是其空間性的體現。陳植鍔先生將古代詩歌意象組合歸納為并置、脫節、疊加、相交與融合5種方式[12]。馮紀忠先生曾說對偶是我國普遍突出的文化現象,是諸如隱喻、聯想、夸張、背反等意象運作的一種技法,詩里面的對偶亦稱對仗[13]。如王維《青溪》中“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里”,表現出了意象的對偶運作。詩性思維在園林詩意空間營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其影響著園林“言象意”系統中“象”的生成及組合方式,進而影響著“意”的表達。在方塔園中,馮紀忠先生多次使用對偶的手法來運作意象,如全園空間序列的曠與奧的對偶,北門甬道兩側使用曲折與筆直、剛與柔的對偶,自然入水草坡與人工駁岸的對偶,方塔空間與竹林空間形成的塔顯竹隱與竹顯心隱的對偶[13~14]。意象經過安排組合與浸潤之后,遂成就方塔園的詩意篇章。詩性思維是一種想象力極為發達的創造性思維,其以主觀感受與體驗來認識與把握世界。中國現代園林受西方現代園林的影響,嚴重偏向于理性,然理性卻無法把握人獨特而內在的生命體驗,從而無法給予人精神上的慰籍[15]。 所以需重視詩性思維的運用,將現代園林引入一個詩意化、審美化,同時注重理性化的美好境地。
4 小結
“言象意”思想起源于哲學領域,進而被引入文論與園林等藝術門類之中,從思辨語言如何在思維中的運用及其能否充分表達思維的問題,引申到對藝術創作方法的探討。故而從“言象意”思想切入分析園林藝術,能為現代園林詩意空間營造方法的研究提供一個可行的方向。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的極大豐富,人們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斷攀升,現代景觀在解決社會與環境問題的同時,還需滿足人們精神的需求。中國現代園林需要一個傳統與現代、中方與西方、理性與感性融合的詩意空間,其不僅能突顯出中國的韻味,也能涉及西方理性主義所不能顧及的人獨特而內在的生命體驗,給現代人提供精神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