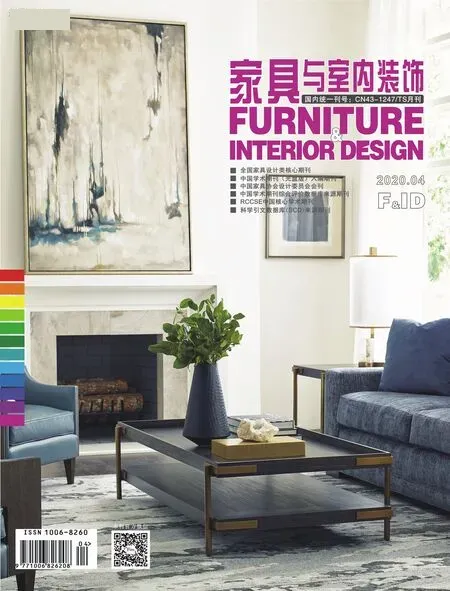福建安溪藍(lán)染在茶空間產(chǎn)品中的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與應(yīng)用研究
■卜 俊,唐 剛,張錦锳 Bu Jun & Tang Gang & Zhang Jinying
(廈門(mén)大學(xué)嘉庚學(xué)院,福建漳州 363105)
福建安溪印藍(lán),又稱(chēng)為“福建青”,是以天然草木為染料,通過(guò)傳統(tǒng)的印染工藝制成的印染品。安溪藍(lán)染在歷史上負(fù)有盛名,2005年安溪藍(lán)印花布被列為福建省首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然而在工業(yè)化的浪潮下,此項(xiàng)傳統(tǒng)藍(lán)染技藝正在逐漸消失,如何將它與地方產(chǎn)業(yè)結(jié)合,并通過(guò)設(shè)計(jì)再造的方式使其融入現(xiàn)代生活當(dāng)中已經(jīng)成為一項(xiàng)亟待解決的問(wèn)題。
1 福建安溪藍(lán)染概述
1.1 福建安溪藍(lán)染發(fā)展?fàn)顩r
據(jù)有關(guān)史料記載,福建藍(lán)染源于宋元時(shí)期,福建省面海背山,耕地較少,人們?cè)诜N植農(nóng)作物的基礎(chǔ)上,也小規(guī)模買(mǎi)賣(mài)各種商品。《三山志》曾記載福州有除糧食以外的各種商品交易,如鹽、鐵、紫草、藍(lán)靛等。《仙溪志》記載“貨殖之利則搗蔗為糖,漬藍(lán)為靛,紅花可以朱、茈草可以紫。”表明在宋元時(shí)期,伴隨著棉紡織業(yè)在福建地區(qū)的盛行,藍(lán)染已經(jīng)開(kāi)始存在于勞動(dòng)人民的生活之中,但是由于元朝時(shí)期苛捐雜稅嚴(yán)重,導(dǎo)致民間棉布剩存無(wú)幾,藍(lán)染技藝因此沒(méi)有得到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
明清時(shí)期,生產(chǎn)力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民眾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棉紡織品開(kāi)始進(jìn)入尋常百姓家,需求增多促進(jìn)了棉紡織業(yè)的迅速發(fā)展。泉州沿海成為當(dāng)時(shí)主要的產(chǎn)棉地區(qū),《安海志》卷十一記載“棉布為類(lèi)極多,晉江之南鄉(xiāng)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長(zhǎng)四丈二尺為一匹,時(shí)布五百縷,上布八百縷,細(xì)密堅(jiān)致,如青花、斜紋布,直徑斜緯、織文方斗”,其中青花布即為藍(lán)印花布。此時(shí)安溪藍(lán)染發(fā)展最為興盛。安溪縣種棉業(yè)“近時(shí)山坡平曠多有種之者”、婦女“冬棉夏葛、以為女工”、“藍(lán)靛:藍(lán)草,即《詩(shī)》所謂采藍(lán)。有大藍(lán)、小藍(lán),俗名菁。以藍(lán)草淹水?dāng)?shù)日,去稿,投灰以收其色,用以染練”[1],目前安溪保留有專(zhuān)門(mén)種植藍(lán)草得名的藍(lán)田鄉(xiāng)、漂洗藍(lán)染布而得名的河流藍(lán)溪以及舊染局遺跡“清玉泉井”等,諸多史料和遺跡表明福建安溪藍(lán)染在明清時(shí)期達(dá)到了鼎盛時(shí)期,并且以閩南安溪最為出名。
繁盛后的安溪藍(lán)染在近代跌入發(fā)展窘境。清末時(shí)期,受到西方工業(yè)化生產(chǎn)的沖擊、合成化工染料引進(jìn)替代,以及經(jīng)濟(jì)蕭條市場(chǎng)萎縮等影響,福建安溪藍(lán)染近乎絕跡。直至1995年,時(shí)任安溪縣文管辦副主任的黃炯然先生對(duì)安溪縣的藍(lán)染工藝進(jìn)行了挖掘和整理復(fù)原,成為該項(xiàng)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代表傳承人。除黃炯然先生對(duì)福建安溪藍(lán)染進(jìn)行研究之外,集美大學(xué)楊光敏[2]和余明涇[3]分別從工藝的生態(tài)變遷、藝術(shù)特色和表現(xiàn)價(jià)值對(duì)安溪藍(lán)印花布進(jìn)行了探究。伴隨著傳承人黃炯然先生的去世,福建安溪藍(lán)染,再度陷入瀕臨絕跡的危險(xiǎn)。由此看出福建安溪藍(lán)染技藝的傳承和保護(hù)面臨著很大的挑戰(zhàn),引導(dǎo)傳統(tǒng)藍(lán)染工藝走上可持續(xù)發(fā)展道路迫在眉睫。
1.2 福建安溪藍(lán)染面臨滅絕原因
福建安溪藍(lán)染面臨絕跡的原因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其一,是板式相對(duì)固定。藍(lán)印花布的刻板工藝的復(fù)雜性影響了其普及程度,刻板制作工序比較繁瑣,學(xué)習(xí)難度大,需要耗費(fèi)大量時(shí)間精力,成板幾乎很難改變,板式的相對(duì)固定決定其難以規(guī)模化推廣。其二,是圖案缺少創(chuàng)新。安溪的藍(lán)印花布圖案主要都是一些民間工藝流傳下來(lái)的圖案,如松鶴延年、鳳朝牡丹、鯉魚(yú)跳龍門(mén)、喜上眉梢等,過(guò)于傳統(tǒng)和保守,不能滿足時(shí)代潮流與現(xiàn)代消費(fèi)者的審美需求。其三,是缺乏載體創(chuàng)新。藍(lán)印花布主要應(yīng)用在衣服、被單、床墊等物品上,應(yīng)用的載體相對(duì)較少,加上圖案缺少創(chuàng)新,很難激起人們的消費(fèi)欲望,這也導(dǎo)致其傳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綜上所述,福建安溪藍(lán)染想要進(jìn)行更好地傳承和發(fā)揚(yáng),首先要在制作工藝和圖案設(shè)計(jì)上進(jìn)行創(chuàng)新;其次結(jié)合本地的特色文化尋找不同的消費(fèi)載體;最后能夠結(jié)合本地特色文化形成創(chuàng)意性產(chǎn)品,從而產(chǎn)生經(jīng)濟(jì)價(jià)值。
2 福建安溪藍(lán)染在茶文化空間中的創(chuàng)新思路
宋人周絳《茶苑總錄》稱(chēng):“天下之茶,福建為最”[4],閩茶的發(fā)展,不僅推動(dòng)了瓷業(yè)的發(fā)展,同時(shí)也形成了歷史悠久、文明璀璨的茶文化。茶文化最初是在茶產(chǎn)業(yè)中作為附屬物融入到茶產(chǎn)品,提升茶產(chǎn)品的附加值,滿足消費(fèi)者對(duì)文化消費(fèi)需求的同時(shí)也給經(jīng)營(yíng)者帶來(lái)可觀的經(jīng)濟(jì)效益[5]。在茶文化中,茶席空間是一個(gè)最為精致、濃縮了茶文化精華的氛圍空間,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 使得茶文化和茶室空間越來(lái)越受到關(guān)注[6-7]。中國(guó)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和、靜、怡、真”,茶席作為人們品茶的重要活動(dòng)空間,可以通過(guò)主題空間來(lái)營(yíng)造自然為尚,意在和諧,簡(jiǎn)樸尚用,忠于本真的茶道氛圍,以此呈現(xiàn)出優(yōu)雅、恬靜、簡(jiǎn)素的意境之美[8-9]。
福建安溪藍(lán)染以純天然藍(lán)靛作為染料,采用純棉織物純手工制作,通過(guò)純色、漸變、藍(lán)白相間的表現(xiàn)形式呈現(xiàn)出清新、樸素的特點(diǎn),其作為中華民族的正色之一,與古時(shí)青花瓷圖案有異曲同工之妙[10],獨(dú)有的中國(guó)藍(lán)表現(xiàn)出靜謐、恬雅的色彩意象,營(yíng)造出的幽微空間意境與茶席空間意境主旨不謀而合。利用福建安溪藍(lán)染與茶文化中的茶席相關(guān)因素結(jié)合進(jìn)行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可以從意境的營(yíng)造出發(fā),根據(jù)茶席不同的組成元素,將福建安溪藍(lán)染技藝應(yīng)用于茶席的設(shè)計(jì)之中,不僅能夠使面臨絕跡的福建傳統(tǒng)藍(lán)染文化傳承再現(xiàn),得到創(chuàng)新性的發(fā)展,同時(shí)也能夠?yàn)楦=ǖ貐^(qū)的茶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與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做出積極的貢獻(xiàn)。

■圖1 福建安溪縣西坪鎮(zhèn)

■圖2“一葉亦品”設(shè)計(jì)實(shí)物圖一

■圖3“一葉亦品”設(shè)計(jì)實(shí)物圖二

■圖4“一葉亦品”整體效果圖
3 福建安溪藍(lán)染在茶文化空間中的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實(shí)踐
3.1 基于藍(lán)染的茶空間產(chǎn)品設(shè)計(jì)構(gòu)思
茶席空間產(chǎn)品設(shè)計(jì)需要考慮多種不同因素,以茶為靈魂,以茶具為主題,向外進(jìn)行擴(kuò)散性延展,其基本要素包括茶、茶具、茶葉罐包、茶杯包、茶墊、桌旗、掛畫(huà)、以及相關(guān)工藝品[11]。可通過(guò)對(duì)地域自然如山巒、梯田、茶葉等元素進(jìn)行提取,結(jié)合吊染、蠟染等一系列藍(lán)染工藝,賦予茶席空間中不同的產(chǎn)品要素以新的載體形式和文化意境。在茶空間的設(shè)計(jì)中,品茶的意境和氛圍作為茶空間的靈魂,處于核心位置。茶具作為茶空間的產(chǎn)品主體,有使用功能和視覺(jué)審美的作用。為了能夠迎合茶空間的意境創(chuàng)造,根據(jù)周邊產(chǎn)品的材質(zhì)特性,在進(jìn)行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時(shí)可以選取棉麻,絲綢等織物進(jìn)行創(chuàng)作,不僅符合藍(lán)染的特性,而且對(duì)茶空間的基本要素也能很好地匹配。
安溪是中國(guó)茶葉之都,自然條件得天獨(dú)厚,群山環(huán)抱、峰巒綿延、云霧繚繞,非常適合茶葉的生長(zhǎng)(圖1)。重疊的山巒與茶葉的綠色在薄霧的籠罩下所呈現(xiàn)的自然景觀能夠營(yíng)造出與茶道契合的意境,這和作為福建獨(dú)具特色的青茶與藍(lán)染“福建青”形成了對(duì)應(yīng)。
3.2 基于福建安溪藍(lán)染的產(chǎn)品創(chuàng)新應(yīng)用實(shí)例
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實(shí)踐“一葉亦品”主要采用安溪茶山輪廓元素,采用藍(lán)染工藝對(duì)茶文化中的茶席空間進(jìn)行設(shè)計(jì)和制作。選取偏薄和厚的棉麻織物、藍(lán)靛泥以及在染色的過(guò)程中所用到的工具為使用材料。偏薄的棉麻織物用來(lái)做掛畫(huà),可以營(yíng)造出通透的氛圍效果,厚的棉麻織物可以用來(lái)做茶葉包等物品,體現(xiàn)出清新拙樸的意境。為了保證后期藍(lán)染的上色效果,在染色前需要對(duì)面料進(jìn)行預(yù)處理。一方面是為了除掉織物表面的漿質(zhì)和雜質(zhì),使面料干凈整潔,另一方面可以使織物更加柔軟,增加其滲透性,便于染色[12]。整體以安溪茶山輪廓為元素進(jìn)行創(chuàng)作,以吊染為主,做出層巒疊嶂的輪廓,以蠟染為輔助元素進(jìn)行點(diǎn)綴,將布染好之后進(jìn)行晾干、熨平等處理,再根據(jù)需要設(shè)計(jì)的產(chǎn)品進(jìn)行手工的縫制,完成一系列茶席空間產(chǎn)品的設(shè)計(jì)與制作。
從左到右(圖2)分別為茶杯墊,桌旗、茶葉罐包、茶具包實(shí)物圖,茶杯墊采用不同角度重疊的山巒,采用3~4種不同純度的藍(lán)色進(jìn)行漸變,營(yíng)造出山巒遠(yuǎn)近層次感,桌旗用漸變營(yíng)造出天空靜謐的感覺(jué);茶葉罐包圖案結(jié)合不同角度的山巒重疊輪廓,采用不同純度的藍(lán)色進(jìn)行漸變,營(yíng)造出山巒遠(yuǎn)近層次感,隨意排列在一起也猶如一個(gè)整體山脈。茶葉罐包大小不一,便于整理收納。束口抽繩設(shè)計(jì)不僅開(kāi)合方便,也適用于日常攜帶;茶具包內(nèi)層夾棉設(shè)計(jì)在使用過(guò)程中能有效保護(hù)茶具。作品設(shè)計(jì)整體為冷藍(lán)色,茶杯袋束口繩處的紅珠子增添一絲暖意。
圖3所示為屏風(fēng)、包袱皮、手包實(shí)物圖。屏風(fēng)為雙層設(shè)計(jì),前層是重疊的山巒,后層則是白藍(lán)漸變。前層染布時(shí)是整體一起染,后期再裁成三塊,這樣便于圖案的連貫性。前層后層高低錯(cuò)落,使屏風(fēng)不呆板。面料采用薄紗布,透光性良好,使屏風(fēng)上的山巒具有虛實(shí)遠(yuǎn)近感;包袱皮適用于茶具、茶葉的包裹與攜帶。融入刺繡和麻繩元素,運(yùn)用簡(jiǎn)單線條及補(bǔ)丁描繪出一處重疊山巒的景象;該日月背包不僅可用于攜帶茶具、茶葉等,也適用于日常外出使用,圖案元素取自于大自然,如同茶葉取之于日月精華[13]。以上實(shí)物產(chǎn)品僅僅圍繞著福建地域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從中提取設(shè)計(jì)元素進(jìn)行設(shè)計(jì)再造,將傳統(tǒng)藍(lán)染與茶文化相結(jié)合,衍生出多種多樣的茶文化空間產(chǎn)品(圖4)。
4 結(jié)語(yǔ)
將福建優(yōu)秀的茶文化與瀕臨滅絕的傳統(tǒng)藍(lán)染文化進(jìn)行嘗試性的結(jié)合,進(jìn)行了一系列茶空間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應(yīng)用。實(shí)踐證明,傳統(tǒng)藍(lán)染技藝能夠很好地融合到現(xiàn)代茶文化產(chǎn)品中,并且能夠營(yíng)造出與茶道相契合的空間氛圍。藍(lán)染與茶文化的融合與設(shè)計(jì)再造,不僅能夠使福建安溪藍(lán)染這項(xiàng)傳統(tǒng)技藝得到傳承和創(chuàng)新應(yīng)用,同時(shí)也能夠弘揚(yáng)福建優(yōu)秀的茶文化,彰顯地域特色,為福建地域經(jīng)濟(jì)及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做出積極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