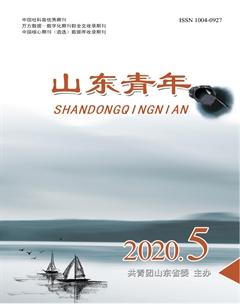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所獲供述排除規則
姚煊
摘要:
2017年新的《嚴格排非規定》將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確定為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此規定內涵和外延不清,以至于實踐中難以運用。筆者通過現有法律和指導案例對此規定發表個人見解。
關鍵詞:排非規則;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超期羈押
2017年6月,最高法等五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嚴格排非規定》)。《嚴格排非規定》第四條規定了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所獲供述應當排除。
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法院排除非法證據已然十分謹慎的背景下,若不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進行明確解釋或者規定,將使得法院難以援引該條款排除非法供述;也難以達到威懾偵查機關,杜絕非法拘禁,完善司法監督的立法目的。由此,筆者結合現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嘗試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所獲供述這一條款的內涵和適用條件發表意見。
在《監察法》頒布后,監察機關也有權訊問犯罪嫌疑人,但監察機關行使的是調查權,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無疑無法適用該條規定。因此,如果監察機關工作人員非法拘禁犯罪嫌疑人則其供述也無法排除。筆者認為,為了切實完善對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保護,應當將監察機關也納入非法取證的主體范圍。
何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對行為的界定是該規定得以切實實施最重要的前提。對于具有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偵查機關而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主要表現在:第一,是沒有法定理由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二,是未經法定程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三,是對公民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超過法定期限。
1.沒有法定理由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我國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對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分為到案階段、刑拘階段和逮捕階段。到案措施可以大致分為“由人到案”和“由案到人”兩種。所謂由人到案,是指偵查機關在尚未立案的情況下先行將有犯罪嫌疑的人帶至公安機關,再決定是否立案。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留置盤問。這一情形得以成立不存在法定理由的可能性非常小,《警察法》第九條規定,對于有犯罪嫌疑的人員,警察有權盤問犯罪嫌疑人;有嫌疑的還可以將其帶回公安機關留置盤問,留置的最長期限可達48小時。可見,無論是留置盤問還是扣留,只要公安主觀判斷某公民存在嫌疑即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難以認定是否真實存在法定理由。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由案到人的措施共有傳喚、拘傳、逮捕三種,傳喚或口頭傳喚為任意性到案措施,拘傳和逮捕為強制性到案措施。現實中,即使是由案到人的措施也難以直接確定是否存在可以適用的客觀情形。以口頭傳喚為例,《刑事訴訟法》規定,對在現場發現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口頭傳喚。何為“現場發現”,在實務中存在較大爭議,口頭傳喚作為傳喚的一種形式,理應屬于由案到人的措施,即應當在立案的前提下使用。若將“現場發現”做現行犯解釋,則與傳喚的性質存在矛盾,并且如果是現行犯,公安機關更可能采用留置盤問這一無證到案措施①。可見,雖然不具備法定的客觀情形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可以構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但由于客觀情形本身規定主觀性強,在實務中被告人及其幾乎不可能以此為由要求排除非法取得的供述。
2.未經法定程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未經法定程序的主要表現形式為無證拘禁,這是由我國司法實踐現狀決定的。司法實踐中的非法拘禁行為,大都是因為拘傳證、拘留證、逮捕證申請程序復雜、簽發效率低下,部分偵查人員出于盡快收集證據、查獲犯罪等目的,在未獲取許可之前拘禁犯罪嫌疑人②。此處存在的問題在于,偵查機機關一般的程序違法屬于證據收集程序的瑕疵,存在補正和合理解釋的空間,并不會被作為非法證據排除。筆者認為,既然新的排非規定已經將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作為了構成非法言詞證據的情形之一,就應當本著保護犯罪嫌疑人人權的原則,將無證拘禁作為非法證據排除的一種情形,所獲的證據不應再作為瑕疵證據而是非法證據,應當嚴格排除。
3.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超過法定期限
超過法定的羈留期限是否屬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在理論和實務中均存在爭議,按照《嚴格排非規定》出臺前的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超期羈押”應當屬于偵查人員的行為違法,所獲的供述非但不屬于非法言詞證據,甚至可能不被認為是瑕疵證據。刑法學者張明楷教授認為偵查機關工作人員故意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應當視為非法拘禁行為③。《刑事審判參考》(第108集)第1165號案例,黃金東、陳玉軍受賄案中,法院認為偵查機關傳喚犯罪嫌疑人超過了傳喚的最長期限24小時,所獲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筆者認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應當包括羈留犯罪嫌疑人超期,法律規定傳喚、拘留的期限就是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過度的侵害,而超期顯然違法了法律對于期限的規定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即使偵查機關先前系合法羈押犯罪嫌疑人,若存在羈留的超期,則超期的期間訊問所獲的供述應當被認定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所獲供述予以排除。
此外,超期行為的不法性不應當因為犯罪嫌疑人的“自愿”而改變。以傳喚為例,傳喚或口頭傳喚作為任意性到案措施,本身不具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效力,如果公民應傳喚主動到案,也應當構成主動投案。但關于犯罪嫌疑人在經傳喚到案后超過24小時卻“自愿停留”,偵查機關是否可以對其進行訊問,筆者持反對意見。傳喚雖然并非強制措施,但對于有犯罪嫌疑的人而言,偵查機關傳喚其到案后并不會放任其自由行動,在實質上已經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本質表現。
首先,即使是如傳喚此類的任意性到案措施,也應當嚴格遵從《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期限。再者,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偵查權的監督和限制,犯罪嫌疑人無法影響偵查機關的非法取證行為本身的性質。因此,即使犯罪嫌疑人自愿停留在偵查機關,偵查機關如果不對其采取拘留等其他強制措施,則無權繼續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也無權訊問犯罪嫌疑人,如有訊問,所獲供述也應當被排除。
[注釋]
①馬靜華:《偵查到案制度比較研究》,《中國法學》2009年第五期.
②鄭旭、徐文靜:《論非法拘禁供述排除規則的適用》,《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8年第三期.
③張明楷:《刑法學(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883頁.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