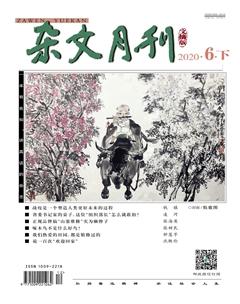高衙內何以變壞?
夏俊山

《水滸傳》中,高衙內是人人痛恨的浪蕩子。他毀了林沖原本幸福的家庭,毀了林沖的大好前程,逼得林沖雪夜殺人,落草梁山。施耐庵沒有寫高衙內的結局。《蕩寇志》中,高衙內被林沖放血、剜眼、割耳之后烹了。央視老版《水滸傳》中,高衙內被一群潑皮無賴給閹了,新版《水滸傳》中,高衙內被魯智深騙至菜園子燒死了。
高衙內的結局,大概是作者為了讓讀者或觀眾解氣、解恨,才這樣安排的。不過,筆者覺得,沒有誰是天生的壞蛋,高衙內跟林沖一樣,也是受害者,只不過施害方不同罷了。
害林沖的主要是高俅父子、富安、陸謙,《水滸傳》寫得很清楚,讀者沒有多少疑問。害了高衙內的又是誰呢?
筆者覺得,一是家教不當,害了高衙內。《墨子·所染》中說:“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 孩子出生后,最初就像一張白紙,你填什么顏色,它就會呈現什么顏色。父母無疑是最早給孩子填色的責任人。高衙內的老爸原是街頭小混混的高俅,他是怎樣培育養子高衙內的呢?
翻遍《水滸傳》中,找不到高俅訓斥高衙內的一言半語,能找到的只是他對高衙內的遷就與滿足。“高太尉愛惜他。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水滸傳》第七回)高衙內“倚勢豪強”實際上就是仗著老爸的權勢,才敢于胡作非為。“養不教,父之過”。高衙內的諸多惡行,其根子是高俅的縱容。“嚴是愛,松是害,不管不教要變壞”。溺子如殺子,高衙內的父親如果是有道德的好官、有良知的嚴父,發現孩子行為不端,及時給予疏導、教育、訓斥,由此關注其精神成長,時時嚴加管教,孩子可能從此向善,怎么會一步步墮落,成為人渣呢?
《觸龍說趙太后》 中有句名言:“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換言之,父母愛孩子,就要為孩子的一輩子考慮。明白這一道理,父母就不能一味滿足孩子的物質要求,以為讓孩子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就是“愛孩子”,而是更關注孩子道德、人格等,教育孩子要做一個不畏艱難、勇于進取,有道德、有理想、有奉獻、有責任感的好人。高俅是怎樣培育高衙內的呢?
《水滸傳》第七回寫道。林沖“搶到五岳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拿著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桿邊。胡梯上一個年小的后生,獨自背立著,把林沖的娘子攔著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俗話說“閑則生非”,高衙內整天無所事事,打鳥捕蟬,又正是青春期,見到林娘子貌美如花,產生沖動,上前騷擾,想入非非,并不意外。問題是,絕大多數人因為道德、法律等諸多約束,見到美麗的異性,至多也就止于遐想,不會有什么荒唐之舉。高衙內敢于攔住林娘子,一是有勢可仗,二是老爸高俅大概從未對他進行過青春期教育、道德理想教育、遵紀守法教育,正是家教的缺失,高衙內才有此流氓之舉。
說高俅害了高衙內,《水滸傳》第七回還有個重要情節:陸虞候和富安設計陷害林沖,老都管去見高俅,“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竟然“教喚二人來商議”。陸虞候和富安到來后,“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個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抬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彩道:‘好計!你兩個明日便與我行。 ”明明知道高衙內行為不當、陸虞候和富安是在犯罪,高俅不但不制止,還竭力支持,甚至以“抬舉”利誘、以“喝彩”贊揚,鼓勵實施陷害林沖。這樣的禽獸父親,怎能不害了自己的孩子?
二是受交友不慎,害了高衙內。孔子曾把友人分為損友和益友,他在《論語·季氏》中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奸佞,損矣。”高衙內交的是什么樣的友人呢?是“拿著彈弓、吹筒、粘竿”的一批閑人、混混。有個叫富安的,綽號“千頭鳥”,更是詭計多端。林沖娘子被高衙內調戲,林沖趕來喝止。《水滸傳》寫道:“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沖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這說明,高衙內對林沖還是有所顧忌的。高衙內回到府中,整日悶悶不樂。此時,如果有益友給予勸導,讓他放棄非分之想,也就沒有了后來的故事。可惜,高衙內身邊沒有益友,只有富安之類的損友。
富安看穿了高衙內的心思,這個內心歹毒之人知道,高太尉寵愛高衙內,高衙內高興了,自己就有機會升官發財。為討好高衙內,他丟開道德倫理,獻出一條詭計:派遣和林沖要好的心腹陸謙出面,請林沖到樊樓吃酒,他再去把林沖妻子騙出來,讓高衙內趁機下手。
第一條詭計落空后,富安竟然又生詭計。把高俅也拉進來,一起設陷阱坑害林沖,讓林沖手持利刃誤入白虎堂,犯了殿帥府禁令。《曾國藩家書》中寫道:“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筆者的家鄉也有俗語:“跟好人學好人,跟著老虎學咬人,跟著巫婆跳假神。”一個人有益友相伴,如同與高人為伍、與智者同行,可以在無形中化解困境、扭轉逆境。如果交了損友,則可能帶來厄運甚至是災禍。圍繞在高衙內身邊的是富安這樣的小人,他能不受害嗎?
三是體制缺陷,害了高衙內。高俅是可恨的,溺愛護短害了養子;富安等小人是可惡的,自作孽還要拉上高衙內。但高衙內成為人渣,除了高俅、富安等人的因素,還與封建王朝的體制缺陷有一點的關系。
封建專制體制下,官員升遷,并不需要草民投票,皇上喜歡就行。高俅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皇上愛踢毬,高俅是踢毬高手,氣味相投,高俅就成功地升遷為太尉。手上有了大權,誰還敢跟他過不去?仗著“我爸是高俅”,高衙內才色膽包天,敢于青天白日,淫人妻女。假如有人不服,跟高衙內過不去,高衙內一句“有本事你告去”,就能讓不少人知難而退。
大宋王朝雖有法律,但是誰都明白,法治是假,人治是真。高俅干的壞事再多,草民是監督不了的。官員之間,魚幫魚、蝦護蝦,烏龜找王八。告高衙內的狀,門都沒有。更骯臟的是,專制體制,等級分明。上下之間,有一種明顯的人身依附關系。富安、陸謙為何討好高衙內?無非是為了攀附。“念準經、跟準人,升官發財才有門”。林沖武藝高強,能重用富安、陸謙,給他們前途和好處嗎?不能,但是,高俅能。所以,富安、陸謙為個人的前途與利益考慮,自然會棄林沖攀附高俅。攀附之術,可以是效忠效力、可以是行賄示好。設計陷害林沖就是為高衙內效力,攀附高俅。如果是法治社會,民主體制,個人的發展不需要攀附權貴,而是靠自己的努力、群眾的支持,富安、陸謙就不會挖空心思幫助高衙內作惡,而高衙內一旦作惡,也會遭到群眾舉報,輕則送進“少管所”,重則關進大牢,依法判刑。高俅想包庇?那就讓他下臺!
幼年時的高衙內,跟其他孩子一樣,都是人見人愛的寶寶,后來變成人渣,顯然與他受的家庭教育、他生活的環境、他成長的社會有關。什么樹開什么花,什么藤結什么瓜。高衙內其實也是一名受害者,受高俅之害、受損友之害、受社會體制之害,只考慮把高衙內閹了、殺了,才解恨,不去思考是誰害了高衙內,這是不應該的。
陳福民薦自《江海晚報》2020年4月22日 戴敦邦/圖
- 雜文月刊(選刊版)的其它文章
- 酵母
- 勸杯
- “門檻”形同虛設
- 茶客留言
- 趙姨娘為什么總是氣急敗壞?
- 狹隘的愛情正在遍地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