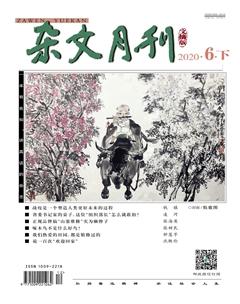說一百次“歡迎回家”
沈軼倫
住在上海的小區就是這樣,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有時候門對門住了十幾年,也不知道對方是干嘛的,頂多有點臉熟,電梯里遇到,大家點點頭。到了疫情期間,你看我像病毒,我看你像病毒,彼此戴著口罩,更顯得客客氣氣。
到了二月初的時候,小區安靜得不能再安靜。唯一的聲響,是樓道里偶然傳來小孩子打球發出的聲音,咚——咚——咚,隔了很久,又咚了一下,襯托得整個小區更寂寥。沒有人敢出門。幾片落葉追逐著落葉,在冷冷的街面上打滾。只有到了夜晚,一扇扇窗戶亮起來,才讓人察覺,小區不僅不是空城,事實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滿。
這滿里面有重量,每一天都讓人覺得更沉甸甸些,也更神經緊繃些。有一天,新聞說外地流調顯示,一個住戶因為在樓梯遇到另一個確診住戶,所以也被感染。此后,家長們連放孩子們去樓道打球也不允許了。小區更安靜了。線上的業主微信群也沉寂下來。這個時候,歡醫生在朋友圈發文字說,即日要隨仁濟醫院的援鄂醫療隊出發。
我知道他,是知道他與我們同住一個小區。有時早上看見他一個人跑步,有時下班看到他帶著孩子打球,有時他在微信朋友圈曬出做飯的照片,有一次我們交換了春節的土產——我們送給他旅游帶回的柿餅,他送給我們自家制作的崇明糕。僅此而已。
但在肅殺的沉寂里,在家家戶戶因為恐懼關緊門窗的時候,意識到這個身邊的人,作為大夫,他要去前線了。這感受是不一樣的。
在微信朋友圈,歡大夫陸陸續續更新了進展:2月19日,到武漢了,當地工作人員歡迎喊著加油的口號;進雷神山了,連做了16個小時的工作;進ICU了,有一次護送一個病人轉病區,防護服被勾破了;他在異鄉,想念孩子在他出發那天流淚的樣子……
我買了一大包吃的放在他家樓道門口。我知道他的孩子不缺食物,但這是我能表達的一點敬意。走出樓道,抬頭看小區里一幢幢樓,窗戶里人影走動,是一一幅幅令人習以為常的生活的場景。但究竟是誰,確保了這日常生活的安全,是誰讓這一間間屋子成為家,是誰使得平常的東西有了非凡的意義?
上海的情況漸漸緩和。小區里開始重新出現人們匆匆出門買菜的身影。復工后我出門上班,拍下了小區街角外一紅葉李上的花骨朵。“生命帶來希望”,我發在朋友圈。歡醫生給我留言,然后給我看他那邊的照片,在他這一批援鄂醫生駐地的湖泊邊,武漢的柳枝綠了。病人們的情況在好轉。
武漢櫻花開放的時候,上海的小區里,也是一片花海。花影下,小區閑置許久的快遞收放區又重新熱鬧起來。大家在那里翻找自己的快遞,彼此停下來,猶豫地隔著一點距離。似乎用目光確認了,我們經歷了同樣的感受。樓道里,重新出現咚咚咚孩子打球的聲音。以往這聲音叫人煩躁,現在卻珍貴得幾乎叫人落淚。
4月6日,有人在業主微信群發消息,是一張照片。在快遞收放區,有一只紙箱,上面寫著“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黨委慰問援鄂醫療隊員及家屬物資”。拍照的人說“原來我們小區也有白衣天使,真好”。歡醫生回復說:“謝謝各位鄰居關心,我已經隨上海市第八批援鄂醫療隊返滬,目前正在青浦隔離。”
沉寂許久的業主微信群,忽然像一夜開放的櫻花一樣,上百條消息涌進來:“歡迎平安回家,歡醫生。”“辛苦你了,好好休養。”“門前的垂絲海棠正在盛開,等你回來跑步。”“我們小區也有最美逆行者,身邊的英雄,連我也感到自豪了。”
一條又一條,持續了整個下午,在這個群里不斷出現,每一條消息帶來手機的提示聲,是一聲一聲道謝:“歡迎平安回家”“歡迎平安回家。”
小區里還是看不到人們扎堆。大家還是把門戶緊閉。從朋友圈,我大概知道歡醫生隔離結束回家了,也大概知道他重新擁抱了孩子,知道他準備回醫院上班了。但我沒有見到他。雖然我們住在一個小區。
住在上海的小區就是這樣,大家關起門來,各自過著各自的小日子。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更何況還沒有到徹底摘口罩的時候,所以見面連點頭微笑也免了。但這口罩下面是溫暖的臉頰,臉頰下面是人的胸口,胸口里有跳動的心,心跳和心跳的頻率,叫我們確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夜里,我回家,走過歡醫生家的窗下,看到燈光暖暖亮著。這亮光和小區里所有窗戶后的亮光匯聚在一起。在口罩后面,我也念出這句被鄰居們重復了一百次的話:“歡迎回家。”
徐峰薦自《新民晚報》2020年5月12日
- 雜文月刊(選刊版)的其它文章
- 酵母
- 勸杯
- “門檻”形同虛設
- 茶客留言
- 趙姨娘為什么總是氣急敗壞?
- 狹隘的愛情正在遍地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