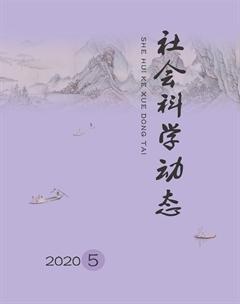王夫之史論的思想家底色
記得30多年前做碩士學位論文時,我選了王夫之文藝美學思想為題,標題取得頗為“文藝”——《古典美學的落霞》;當時導師說這是一塊“硬骨頭”。當“啃”過之后,方知起初完全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可說是無知又膽大。此后這么多年,除了略加修改把學位論文一分為三發表,再沒敢輕易去碰王夫之。最近有個特殊機緣,拜讀了王先志先生著《船山通鑒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以下大多時候采用簡稱“王著”,下文凡引用此書直接標頁碼),有一種故友相逢格外親的感覺,同時依舊心存敬畏。這里不揣簡陋,略談一點膚淺的讀后心得。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夕堂,又自號船山,湖廣衡陽(今湖南衡陽)人,他與顧炎武、黃宗羲并稱為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代表性著作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張子正蒙注》、《讀通鑒論》、《宋論》、《薑齋詩話》等書。19世紀40年代初,他的主要著作以《船山遺書》之名刊行,大約20年后曾國藩設官書局,重新整理刊印了新版的《船山遺書》,而前些年湖南的岳麓書社則進一步整理校勘,推出了規模宏大、搜羅完備的《船山全書》。收入其中的《讀通鑒論》,正是王夫之晚年的嘔心瀝血之作,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影響極為深遠。
在《船山通鑒論》的“緒論”中,作者分四節展開論述,提綱挈領,要言不煩。特別對于王夫之為什么、又是怎樣撰寫這部大書的,王著寫道:
他的主要生涯是一位隱居者,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甚至學術文化中心,但是他心憂天下,? ? 感慨著時代的大變化。大明的滅亡才使王夫之由一介書生成為亡國遺民,這個隱居者一生都將自己視為大明子民,自定墓志銘身份就是“有明遺臣行人”。明亡這個殘酷的現實不僅粉碎了一介書生的夢想,也喚醒了這個書生的心智,這才有直到生命的最后歲月也要探討歷史的成敗得失的心愿,這才有《讀通鑒論》這部偉大的曠世遺著。(第4頁)
《讀通鑒論》,其實就是王夫之讀了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后寫的讀書札記,對于原著中涉及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以及相關評價進行再討論、再評說。王著注意到,中華書局版“標點例言”有一段話:“船山史論兩種,成于最晚之歲。蓋讀史有感,隨事觸發。初無意于文,故每篇皆不立題目;而于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均有論列。又自以身丁末運,明幟已易,禹甸為墟,故國之痛。字里行間,尤三致意焉。”王夫之用了差不多60萬字的篇幅,對于300多萬字的《資治通鑒》做了點評式的評論。對于《讀通鑒論》的主要特點,王著從文體形式(札記),立論范圍(不限于《資治通鑒》所論),評論視野與歷史闡釋,觀點創新以及評論、史論、政論的“三位一體”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很好的概括,認同前人對其進行的總的評價——網羅宏富,體大思精。
王著從第二章開始,直到第十五章,主要是分專題(或問題)就王夫之《讀通鑒論》涉及到的若干話題進行資料的勾稽和歷史的闡釋,具體綱目為:德論、天下財富論、民本論、政治論、君主論、宰相論、將領論、三國人物論、歷史比較論、批判論、史學論、睿智論。這里,作者沒有過多講求形式邏輯的規則,而是針對具體問題或話題,有感而發,述評結合。該書結構用一句說散文特點的話來講,叫“形散而神聚”,這個所謂“神”,就是王夫之的歷史觀,背后是其思想家底色。王著最后這樣寫道:
王夫之與司馬光這些不同見解的是非曲直可暫且不論,無妨看作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對于歷史的不同解讀,應作前代人與后代對歷史的當下理解。重在為當世之治資鑒是司馬光纂史的目的,意欲替后世求鑒故充滿洞見是王夫之的著書理念;司馬光是作史編纂,王夫之是評說歷史,兩者的出發點不同。故而解釋具有多樣性不足深究,恐怕也無高下之分。故王夫之更多哲學的深刻,司馬光則更多史學的持平。王夫之與司馬光有諸多不同,有一點似乎有相通性,即司馬光是歷史學家里最懂得政治的,又是政治家里最懂得歷史的;王夫之則是哲學家里最懂得歷史的,又是歷史學(家)里最懂得哲學的。兩個人的隔時空對話的精彩,或許正在這里。王夫之有句“六經責我開生面”,他的評史論史是“開生面”的。(第458頁)
用思想之光燭照幽暗歷史,正是王夫之史著的特點和亮點。我認為,王先志先生確實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因此著力挖掘王夫之《讀通鑒論》的現實關懷和思想價值。王著讓我們想到西方理論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認識。
克羅齊講,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在他看來,我們只能以今天的心靈去思想過去。深受克羅齊影響的英國歷史學家科林伍德更是強調“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那意思是說:人們必須歷史地去思想,也就是必須思想古人做某一件事時是怎么想的。由此而推導出的系論便是:可能成其為歷史知識的對象的,就只是思想,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這里也許可以用一個流行的比喻說法,即:思想是靈魂,抽掉了思想,歷史或史學就將剩下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① 盡管西方和中國史學界都有人在肯定科林伍德這一觀點的基礎上,提出過一些批評,但值得重視的是其基本觀點——“人的心靈是由思想構成的”,歷史事件則是人們思想所表現的行動——對我們研究歷史、研究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甚而對于我們理解王夫之《讀通鑒論》,以及王先志《船山通鑒論》不無啟示。
王夫之到底稱為哲學家好,還是思想家更恰當?我個人覺得后者或許更符合他個人,也更符合中國古代歷史實際。葛兆光教授曾說:“相比起來,‘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 或intellectual history)在描述中國歷史上的各種學問時更顯得從容和適當,因為‘思想這個詞語比‘哲學富有包孕性質。”② 王著論述王夫之及其《讀通鑒論》,雖使用了哲學家、哲學史等詞匯,但在里面主體部分的14章中,實際更多內容是與更具包容性的“思想”相關涉。事實上,無論是陳述歷史,還是解釋歷史,都離不開一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在王著看來,“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都有著當時一代的解讀和印記,但其主導精神具有永恒的價值,其所構建正確歷史的努力會永留史冊”(第18頁)。
王先志《船山通鑒論》的另一重要特點或價值在于其現實關照。作者寫作此書,不是僅僅為了鉆故紙堆的癖好,也不是要發思古之幽情。王著總體風格近于“述而不作”,依據不同專題,分門別類匯輯資料,排列組合,作者自己的觀點則點到即止,有點“春秋筆法”的味道。即便如此,其間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指向依舊清晰可見。例如第四章《民本論》,其中的第四小節為“輕徭薄賦就是民生”,作者有這樣的結論:“在王夫之那里‘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興亡。統治者必須心里有人民,江山社稷才會綿久。”在列舉了唐玄宗及安史之亂等史實后,作者寫道:“上至唐玄宗在安史之亂的逃難途中還想到‘勿使掠奪百姓,所以才能轉危為安;下至地方郡守興利除弊才能贏得民心。”“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到人民的擁護,得民心,王夫之有幾句管總的話:‘以得民心為本務。”(第69頁)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聰明的人特別是執政者一定會認真學習歷史,深刻反思歷史,以免重蹈歷史覆轍。在第五章《法論》中,作者抓住王夫之“法的作用在‘定民志”這一觀點展開,在盤點了王夫之相關論述后概括說:“王夫之這些論述指出法本于仁,治者依憑的是知人安民。這里的法,不但指法律法治,也包括政治措施在內,其含義廣泛,但不論何義,其基點是一致的,就是法必須考慮民的因素。真正的法律精神是以民生福祉為指歸的。”(第77頁)王著在此章中探討王夫之對法與情關系的認識,尤其給人啟發,富有現實參考價值。作者寫道:
中國向來是人情社會,王夫之這段論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法與情理如何兼顧的問題。他既指出了法與情的兩不相容的對立性,這應該是法律的本質。他也分析了法不顧情之失在于假借名義而摧折五倫,又分析了以情骫法,則亂法殃民。所以在法與情兩者之間的把握上就是執法者的素質要求。王夫之為解決情法難以兼顧開出的一劑藥方是任官的回避,即不到原籍任官以避免“致法與情兩掣”(卷二十,唐高宗一〇)。王夫之在法與情理的考慮上還是重點考慮到了老百姓的心理感受。這實際上在現代社會也長期是一個很難處理的癥結問題。王夫之的思考也富有當代啟示意義。(第78—79頁)
由這番議論,我們想到前幾年網上網下輿情洶洶的山東“辱母案”的審理和宣判。確實,在我們邁向依法治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道路上,如何更好地制定法律、如何有效地嚴格執法,依舊有許多現實的困境。對于歷史上的青天大老爺包拯、海瑞,以往總是好評如潮,王夫之也有不同看法。王著專門提及到這一點,可說不無道理。在王夫之看來,包拯和海瑞的“悁疾”是不足取的。其核心觀點是“執法者不可過于嚴苛”。“王夫之法律思想的核心是法本于仁,不僅是法律本身,尤其是執法之人都要本于仁。”(第82頁)此外,王夫之主張“法貴簡”,“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他強調“法簡”,同時主張“政簡”,堅持“法制之不能泥于古”,“治之不可恃于法”等等,其原則精神都是一致的。這些不僅對于我們的法治與法制有啟發,也對當下如何“簡政放權”,政府如何由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無遠不至回歸本位——建設服務型政府,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王著對于王夫之史論中的若干精粹,若干思想火花,都一一縷述,適當發揮,頗能啟人思智。在第六章《政治論》中,作者特別強調了統治者開通“言路”、帝王勇于納諫之重要,因為“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卷十四,安帝二);“人君之待諫以正,猶人之待食以生也。絕食則死,拒諫則亡,固已。”(卷二十五,憲宗六)王夫之這里確實有點“上綱上線”了,把言路是否通暢、皇上是否納諫提高到了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我想他應該是有充分歷史事實、正反經驗教訓做依據的。講到皇帝“求諫有道”,王著有一段話論述很到位,也完全可以作為現實的參照:
……唐憲宗標榜以至濫用直諫之名設科取士,鼓勵了一些人投機取巧,激成朋黨;而且實際提出了一個很重要且帶普遍性的問題,納諫有道,求諫有道,如若失道,就會助長下位者的諍諫失道,“言直而心曲”是會造成很壞結果的。(第96頁)
這就讓我們聯想到當今加強紀檢監察,注意來信來訪。但如若引導不當,可能誣告成風,奸邪橫行,結果或許是小人告君子、壞人整好人成為風氣。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
此外,書中論相權與皇權之關系,講到“宰相無權,則天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也”;論中國與四夷之關系,強調“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論中央與地方之關系,王夫之不太主張用“專使”(欽差大臣)辦事的制度,而主張加重地方守令的責任,等等,都很發人深省,值得咀嚼回味。
當代著名史學家戴逸曾說:“對現實知道得更多,對歷史會理解得更深。”王夫之深山隱居,“論史評史,并非與世隔絕,而是緊緊扣住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來理解歷史的,他和時代不脫節。這又與他的史學通識大有關聯。”(第363頁)王先志撰寫這部《船山通鑒論》,同樣也是不僅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而且注意環顧當下、觀照眾生的。毛澤東曾經有個說法:“西方有個黑格爾,東方有個王船山。”誠如王著所言,“從毛澤東的這句評語,人們可以讀出這樣的信息。王船山是以思想來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人。而這些思想是通過王船山的一系列著述來承載的”。王君先志這部《船山通鑒論》探幽發微,鉤玄提要,既豐富了我們歷史的滋養,更賦予了我們思想的啟迪。
注釋:
①[英]R·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譯序。
②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作者簡介:范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主編,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