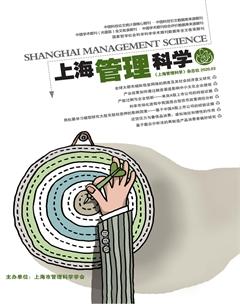責任型領導如何產生:領導盡責性、組織環境的共同影響
趙紅丹 俞心悅



摘 要:通過對浙江、上海、江蘇等沿海城市企業253名員工及其直接上司的配對樣本,研究了領導的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同時基于特質激活理論,探討了社會責任導向的人力資源管理(social responsibl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RHRM)實踐和組織倫理氣氛(organizational ethic climate)在領導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的影響中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表明,領導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形成有正向影響,SRHRM正向調節領導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組織倫理氣氛的關懷導向氛圍正向調節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
關鍵詞:盡責性;責任型領導;SRHRM;組織倫理氣氛
Abstract:Based on the paired samples of 253 employees and their direct superiors in coastal cities of Zhejiang, Shanghai and Jiangsu,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conscientiousness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it acti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RHRM)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al ethic clim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cientiousnes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SRHRM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conscientiousness 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 organizational ethic climate is positively regulating the influence of conscientiousness on responsible leadership.
Key words:conscientiousnes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ethic climate
1 問題提出與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組織內頻發的各種違規甚至違法的行為(如大眾“排放門”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了消費者的普遍關注。在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開始關注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背后的領導風格。
實際上,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科技的日新月異,企業之間出現了共生共存的局面,社會也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業領導者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如多樣化挑戰、利益相關者挑戰、倫理挑戰等。這就要求企業領導者不僅要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還要求企業承擔各種社會責任。由此,Pless和Maak(2005)在第六十五屆管理學會年會上首次提出的責任型領導概念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認同。他們認為責任型領導是一種基于價值觀和道德的規范性現象,是一個將領導和社會責任這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理論融合在一起的綜合性概念。這一新型領導風格超越傳統的“領導—下屬”二元關系,將不同利益相關者(員工、顧客、供應商、公眾等)通過領導的建立與協調作用緊密聯系起來。領導者強調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并把維持與利益相關者的高質量關系視為自己的責任。在這種領導風格的影響下,員工將領導視為學習榜樣,態度與認知直接或間接地受其影響。Voegtlin(2011)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責任型領導會帶來較高的員工工作滿意度。Maak(2007)發現,責任型領導在與利益相關者分享交流的過程中,會與他們建立相互協作的關系,不斷積累企業的社會資本,進而直接或間接地提高組織效益。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組織層面,責任型領導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注意力集中到對責任型領導的研究上。
在我國,關于責任型領導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盡管已經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但現有關于責任型領導的研究,主要關注了責任型領導對下屬、對企業社會資本等的影響,如郭億馨等(201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責任型領導對下屬組織公民行為有雙刃劍效應,宋繼文等(2009)通過對怡海公司領導者的風格及行為的實證研究,發現責任型領導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社會資本的形成與發展,而對責任型領導的成因研究較少。閱讀其他關于領導風格成因的文獻發現,領導者的人格特質是影響其領導風格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邱茜,2016),Stahl和De Luque(2014)也提出同理心是責任型領導的一個重要預測變量。Tepper(2007)發現大五人格等人格特質對破壞型領導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孟慧(2003)也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外向性和責任意識能夠有效地預測變革型領導及其部分子維度,神經質和經驗開放性均與變革型領導顯著正相關。由此我們推斷人格特質對責任型領導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在人格特質的研究結果中,大五人格特質模型是運用廣泛、具有有效結構并得到研究者們認可的一種方式,是穩定的、可跨文化推廣的。大五模型包含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宜人性和盡責性五種人格因素。盡責性,又被稱作嚴謹性、責任心,它是個體對于目標在組織、堅持和動機方面的表現。作為一種細心、認真、嚴謹的人格特質,它預示著個體更加勤奮、可靠、高效、有組織性、有責任心。正是由于盡責性具有這些積極品質,使得高盡責性的個體更容易實現目標和取得成就,也更容易考慮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不難發現,盡責性表現出來的特征與責任型領導需要具備的品質一拍即合。關于盡責性與領導力的關系,Barrick等人(2001)對其進行了研究分析,很容易就發現盡責性是影響領導效能的重要因素。盡責性強的領導能夠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目標的完成上,并能在與利益相關者的社交中主動打開局面,促進與利益相關者建立和諧共贏的關系。
用以研究個體認知行為的特質激活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受個體的特質和環境因素的交互影響。當環境提供了有利于某種個體特質“激活”的相關線索時,該種特質就被“激活”,出現對應行為。當組織形成關懷導向的組織倫理氣氛時,強調利他主義,領導將實現員工利益最大化視為努力方向,具有高度盡責性的領導將更主動地為員工著想,加強與員工的聯系,在環境的刺激下,盡責性特質充分被“激活”,成為責任型領導。社會責任導向的人力資源管理(social responsibl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SRHRM)是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實踐與社會責任的相互融合,企業注重與內(員工)外(股東、環境等)部利益相關者的聯系。這種人力資源管理實踐要求領導加強與各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高度盡責性的領導在這樣一種環境下,通過更加全面細致的考慮,有組織有目的地用符合倫理的方式與利益相關者建立平等互助的關系,以實現目標,成為責任型領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將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研究領導的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并基于特質激活理論,引入SRHRM和組織倫理氣氛的調節作用,探討其作用機理,期望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貢獻:首先,從領導的盡責性特質出發,探討其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機制,豐富責任型領導的前因變量理論研究,為以后的研究提供經驗。其次,本文基于特質激活理論解釋SRHRM和組織倫理氣氛的調節作用,進一步豐富了責任型領導的研究理論。最后,本研究結論為組織選拔培養責任型領導提供了借鑒,有助于加強組織對責任型領導這一概念的理解,幫助企業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2.1 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
在人格特質的廣泛研究中,大五模型是被廣泛運用且被學術界普遍接受的一個模型,它包含盡責性、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宜人性五種人格因素。本文研究中提到的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是一種較為穩定的特質,又被稱作嚴謹性、責任心。Roberts等人(2009)將責任心定義為遵循社會規定的沖動控制傾向的個體差異,目標導向,有計劃,能夠延遲滿足,遵循規范和規則,它是個體對于目標在組織、堅持和動機方面的表現。盡職盡責是一個廣泛的特征領域,包含多個低階方面。目前,至少五個方面可以被認為是盡責性的組成部分:勤奮、有序、沖動控制、可靠性和慣例性。盡責性程度高的人做事有條理,堅持不懈,并有著很高的效率。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更傾向于設定較高的目標,會以積極的方式應對工作中遇到的困難與挫折,從而負責任地完成任務,努力達到既定目標。
Maak和Pless(2009)將責任型領導(responsible leadership)定義為領導者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種基于價值觀和原則驅動的關系,他們通過共同的意義和目標感將他們提升到實現可持續價值創造和負責任變革的動機和承諾的更高水平”。區別于傳統的“領導—下屬”二元領導,責任型領導關注的是組織內外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通過與各個利益相關者建立友好關系,采用積極協商和友好對話的方式,權衡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需求,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實現商業的可持續發展。責任型領導不僅追求利潤最大化,還通過與各方利益相關者積極合作,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這些都對領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領導者以一種更負責、更嚴謹的態度,有條不紊堅持不懈地開展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盡責性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成為責任型領導。另外,研究表明人格特質對于人的動機、行為、認知、社會行為以及組織公民行為都有復雜的影響,因此領導行為也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我國學者時陽(2017)證實了這一觀點,并指出個人特質是影響責任型領導的一個重要因素。具備盡責性的個體更具備責任感,在工作中更加勤奮、負責任,做事更高效、更可靠,也更容易實現目標和取得成就。Dugan JP(2006)研究發現,對于責任型領導來說,個性特征的影響表現在道德層面的責任心上。這些都充分證明盡責性可能是責任型領導產生的誘因之一。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正相關。
2.2 組織倫理氣氛的調節作用
組織倫理氣氛(organizational ethic climate)由學者Victor在1987年提出,是指員工對組織倫理程序與政策所共同持有的一種穩定的認知與行為意向,是組織內部成員對于什么是符合倫理的行為, 以及如何解決倫理困境或問題的共同體驗和認知, 是組織倫理環境特征的集中體現,具有穩定性。領導權變理論指出領導者所處的情境不同,其表現出來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組織倫理氣氛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責任型領導的行為。具體而言,責任型領導強調權衡組織內外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加強利益相關者的聯系,對利益相關者負責,對社會負責,進而與利益相關者發展出符合倫理規范的關系。如果組織內部形成了以仁愛和關懷為導向的倫理氣氛,那么領導在進行與倫理問題有關的行為決策時就會認為 “關注他人利益 ”是組織內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模式。于是,他們的行為決策就不僅僅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實現,還會考慮那些受自己行為影響的利益相關者,并試圖追求自我、團體以及組織整體利益的平衡。為了實現組織目標,領導們在決策時將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積極與利益相關者進行互動,以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這與責任型領導所要求的理念一致。據此可以推測,如果企業內部形成了關懷導向的倫理氛圍,有利于責任型領導的產生。特質激活理論是目前學術界用于研究個體認知行為的頗具影響力的理論工具之一,認為個體行為是個體特質和情境因素互動共變的結果,個體特質能否有效作用于個體行為取決于情境能否提供“激活”個體體質的相關線索。據此推理,盡責性作為領導的一種個體特質,在關懷型組織倫理氣氛強的特定情境中會被“激活”,進而會對責任型領導產生顯著效應。具體而言,具有盡責性的領導能認真負責地朝著目標努力,組織營造的對員工仁愛負責的倫理氛圍會更好地激發領導的盡責性,促使其產生一系列對組織負責任的行為,迫使領導為了實現組織目標,主動考慮利益相關者的需求,進而成為責任型領導。Stahl和De Luque(2014)在研究中指出組織文化等情境因素在上述過程中起調節作用。當組織具有較高的倫理氣氛和完善的獎懲機制時,不論領導者的個人特質如何,都會展現出較高的責任行為來遵守規則,滿足這些情境因素所傳達的期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關懷型組織倫理氣氛正向調節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之間的關系。關懷型組織倫理氣氛越強,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越大。
2.3 SRHRM的調節作用
Gond等人(2011)從HR的職能貢獻、實踐貢獻和關系貢獻三個層面分析了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可以極大地幫助塑造組織環境,以發揮責任型作用。其中,HR的職能貢獻主要是確定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和人力資源部門之間關系的配置,以及它們如何形成企業社會責任的組織和定義邊界。研究表明,當CSR部門作為HR部門的一部分時,有助于責任型領導工作的開展。此外,HR的實踐貢獻(如營造公平的組織環境、關心員工的需要與利益、關注生態環境等)和HR的關系貢獻(如鼓勵員工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均對責任型領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學者Pless(2011)等人也提出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實踐的針對責任型領導的培養計劃有助于責任型領導的形成與發展。SRHRM是企業在追求可持續發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堅持商業倫理道德三者的交融中采用的一種更負責任和更可持續的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是一種通過人力資源管理實踐鼓勵員工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從而實現組織系統內企業社會責任制度化與可持續發展的管理實踐。SRHRM超出企業需要基本滿足的經濟義務和法律義務,還另外充分考慮了對其雇員以及社會利益相關者履行道德、自由方面的責任,大大提高了員工在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中的地位,通過影響企業的倫理道德文化,讓企業感知和承擔社會責任,促使企業形成一種與組織內外部不同利益相關者達成互信、合作和穩定的互惠關系網的氛圍。同理,遵循特質激活理論,不同水平的SRHRM為不同領導的盡責性提供的關聯線索是不同的。當處于高水平的SRHRM時,員工對組織外部CSR行為的支持積極地被影響,領導作為組織員工,更加重視企業倫理和可持續性問題,會提高對利益相關者的重視程度,感知并且承擔社會責任,盡責性個體特質被“激活”,進而促進責任型領導的產生。
H3:SRHRM正向調節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之間的關系,組織中SRHRM越強,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影響越顯著。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和研究程序
為了盡可能增強數據的可說服性,本文采用配對問卷的方式進行數據的收集,即事先在問卷上設置配對題,采取配對的方式對調查問卷(領導版和員工版)進行配對,并根據問卷的配對情況對回收問卷進行配對整理。其中:員工版問卷包含組織倫理氣氛、SRHRM、責任型領導這三個變量,由員工填寫;領導版問卷包含組織倫理氣氛、SRHRM、盡責性這三個變量,由領導填寫。同時,領導和員工按照1∶1的互評比例發放調查問卷。
本研究主要以浙江、江蘇、上海、福建等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員工作為調查對象。這些地區的企業發展相對較快,員工接觸的管理理念相對較新。在企業的協助之下,研究員隨機抽取人員進行調研,最終共得到253套有效問卷。
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被試的人員男性約占64.03%,女性約占35.97%,學歷以本科為主(56.91%),平均年齡為36歲,職位以中層管理者為主,約占41.10%,在當前工作單位工作的平均工作年限為8.78年,與下級平均相處時間為2.29年。
3.2 測量工具
調查問卷包括盡責性、責任型領導、SRHRM、組織倫理氣氛等變量。為保證在中國情景下這些量表測量的有效性,本文采取標準的翻譯-回譯程序將收集到的成熟的量表翻譯為中文版,并結合中國情景對量表進行適當調整。問卷以李克特5點量表測量,即主要是1~5點評價標準,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1)盡責性的變量測量。盡責性作為主要解釋變量,是大五人格特質模型中的一個變量。因此,本文采用大五人格簡式量表中有關盡責性的分量表,測量被試在多大程度上是盡責的,共有12個條目。例如:“我將自己的物品保持得干凈整潔。”采用李克特五點評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盡責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份問卷的信度系數為0.866。
(2)責任型領導的變量測量。責任型領導的測量使用文鵬等人(2016)所開發的量表,共有5個條目。例如:“我的上級會表明其意識到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本研究中,該份問卷的信度系數為0.834。
(3)組織倫理氣氛的變量測量。組織倫理氣氛量表使用頻率最高的是Cullen和Victor(l988)的組織倫理氣氛問卷(ethical climate questionnaire, ECQ),學者劉文斌(2009)參照ECQ問卷自行編制了關懷、自利和規則3維度組織倫理氣氛問卷。本文根據研究需要,采用其編制的問卷中的關懷導向相關題項,共有6個條目。例如:“在我們公司,員工普遍把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看得很重要。”本研究中,該份問卷的信度系數為0.809。
(4)SRHRM的變量測量。SRHRM的測量使用Shen等人(2016)所開發的量表,通過翻譯-回譯法結合中國情景,對量表進行適當調節,共有6個條目,例如“公司在招聘和選拔過程中會考慮員工對于環保、慈善等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本研究中,該份問卷的信度系數為0.911。
(5)控制變量。我們進一步控制了上級的性別(1=男性,0=女性)、年齡、工作年限、學歷(1=高中(中專)及以下,2=大專,3=本科,4=碩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職位(1=基層管理者,2=中層管理者,3=高層管理者,4=其他人員)、與您的下級相處時間等變量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4 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區分效度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正式的樣本調查中,借助AMOS24.0軟件,本研究進行了一系列驗證性因子分析來檢驗研究變量的區分效度,并采用IFI(增量擬合指數)、TLI(非規范擬合指數)、CFI(比較擬合指數)、RMSEA(近似誤差均方值)等擬合指標判斷模型優劣,具體結果見表1。由表1可知,相較于1因子、2因子和3因子模型,4因子模型的擬合效果最好(IFI=0.913,CFI=0.912,TLI=0.901,RMSEA=0.060),這表明本研究的4個變量相互獨立,且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4.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是各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由表2可知,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r=0.258,p<0.001)、SRHRM(r=0.279,p<0.001)、組織倫理氣氛(r=0.258,p<0.001)顯著相關,責任型領導與SRHRM(r=0.176,p<0.01)、組織倫理氣氛(r=-0.214,p<0.001)顯著相關。這些結果為本文進一步論證假設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4.3 假設檢驗
4.3.1 主效應檢驗
假設1提出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正相關。應用層次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進行模型檢驗,結果見表3。第一步,加入性別、年齡、工作年限、學歷、工作崗位和與下級相處時間等控制變量對因變量進行回歸(模型M1);第二步,加入自變量盡責性對因變量回歸(模型M2)。由回歸結果可知,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顯著正相關(β=0.320,P<0.001,模型M2),假設1得到驗證。
4.3.2 調節效應檢驗
假設3提出,SRHRM調節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之間的關系,本文通過層次回歸分析對調節效應進行驗證。為減少回歸方程中變量間的多重貢獻性,本文在分析之前對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并將中心化后的自變量(盡責性)與調節變量(SRHRM)構建交互項。我們再次對主效應進行了檢驗。從表4中的模型3和模型4可知,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顯著正相關(β=0.269,P<0.001,模型M4),假設1得到驗證。對于調節效應的檢驗,首先檢驗調節變量是否顯著調節盡責性對于責任型領導的直接效應。從表4中的模型5可知,當盡責性、SRHRM、盡責性與SRHRM的交互項同時進入以責任型領導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時,盡責性與SRHRM的交互項與責任型領導顯著相關(β= 0.095,P<0.05,M5),說明SRHRM顯著調節了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直接效應。為了更清晰地判斷調節效果,本文根據SRHRM的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值,將樣本分為高低兩組繪制調節圖(如圖1),可見當SRHRM水平較高時,盡責性對于責任型領導形成影響較強,當SRHRM水平較低時,盡責性對于責任型領導形成影響大大較弱,進一步驗證了SRHRM顯著調節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之間的關系。
假設4提出,組織倫理氣氛調節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之間的關系,本文通過層次回歸分析對調節效應進行驗證。為減少回歸方程中變量間的多重貢獻性,本文在分析之前對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并將中心化后的自變量(盡責性)與調節變量(組織倫理氣氛)構建交互項。對于調節效應的檢驗,首先檢驗調節變量是否顯著調節盡責性對于責任型領導的直接效應。從表4中的模型6可知,當盡責性、組織倫理氣氛、盡責性與組織倫理氣氛的交互項同時進入以責任型領導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時,盡責性與組織倫理氣氛的交互項與責任型領導顯著相關(β= 0.120,P < 0.05,M6),說明組織倫理氣氛顯著調節了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直接效應。為了更清晰地判斷調節效果,本文根據組織倫理氣氛的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值,將樣本分為高低兩組繪制調節圖(如圖2),可見當組織倫理氣氛水平較高時,盡責性對于責任型領導形成影響較強,當組織倫理氣氛水平較低時,盡責性對于責任型領導形成影響較弱,進一步驗證了組織倫理氣氛顯著調節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之間的關系。
5 結論與討論
當前國內對于責任型領導的研究多集中于后果研究,對前因的探索相對較少。本文針對責任型領導的成因,以特質激活理論為基礎,深入探究了SRHRM和關懷型組織倫理氣氛對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間關系的調節效應。
5.1 理論貢獻
首先,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檢驗了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的正向影響,深化了學術界對于責任型領導成因的探索,為過往有關研究提供了相關經驗。以往的研究探索了人格特質對領導的影響,如邱茜(201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領導者的人格特質是破壞型領導的前驅因素,在大五人格中神經質對破壞型領導有正向影響,外向性和宜人性對破壞型領導有負向影響。本文沿著這一思路,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檢驗了大五人格中的盡責性對責任型領導有正向影響。發現盡責性越高的領導,在工作中更認真負責,為了實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組織任務,在決策時能考慮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積極合作,與其建立一種合作關系。本研究也進一步驗證了De Hoogh(2008)的觀點,證實了責任心越強的領導者表現出更多的責任行為。而Stahl和De Luque(2014)也提出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行為密切相關。本文的結論與前人研究有相通之處,有助于解釋責任型領導的成因,也為后人研究責任型領導提供了參考。
其次,本文基于特質激活理論,分別驗證了關懷型組織倫理氣氛和SRHRM兩個變量對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關系的調節作用。個體行為是個體特質和情境因素互動共同影響的結果,而個體特質是基于情境因素呈現的。如果情境中存在特質關聯線索,那么個體特質會被“激活”。組織中若形成高水平的關懷型組織倫理氣氛,領導需要及時考慮員工利益,關心員工,履行對員工的責任,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建立強大的關系網絡,從而鞏固企業的社會資本,進而提高組織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領導的盡責性特質被激活,可促進責任型領導的形成。根據Nishii等人(2008)的闡述,SRHRM能改善員工對外部CSR實踐的態度和行為。Shen和Zhang(2017)實證研究發現:SRHRM會積極影響員工對組織外部CSR行為的支持。組織中SRHRM水平較高,領導會積極支持外部CSR實踐行為,考慮雇員和社會中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群體的道德和責任,幫助組織履行其經濟和法律義務。在這種情境下,領導的盡責性同樣被激活,促進責任型領導的形成。這一研究結論既有助于解釋組織倫理氣氛和SRHRM對盡責性發揮影響責任型領導的約束條件(即激活不同盡責性所需的組織倫理氛圍和SRHRM水平是不同的),也為后人研究責任型領導的成因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
5.2 管理啟示
本研究的管理啟示如下:首先,領導者的盡責性是責任型領導的前驅因素,正向影響責任型領導的形成,這說明領導者的人格特質對于責任型領導是有一定預測作用的。因此,組織在進行領導者選拔的時候可以把盡責性作為一個參考標準,盡責性維度得分較高的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其次,不同情境因素能不同程度地激發領導的盡責性特質。高水平的關懷型組織倫理氣氛有助于激發領導的盡責性特質,促進責任型領導的形成。因此,對于內部員工,組織不僅應履行法律規定的責任,還應仔細考慮員工工作環境、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責任。組織可以通過對領導者進行培訓,鼓勵領導與下屬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在決策時將員工的利益考慮在內,激發領導的盡責性。此外,組織中高水平的SRHRM正向調節盡責性與責任型領導之間的關系,因此,組織應該積極采取社會責任導向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方式,提供充分的企業社會責任培訓,宣傳企業社會責任,以幫助員工更好地參與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促進企業社會責任成為組織的核心價值。鼓勵員工尤其是領導者重視與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組織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還應在環境保護、社會公益等方面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可以在招聘和選拔過程中考慮員工對于環保、慈善等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并在對領導進行績效考核、薪酬獎勵、職位晉升時綜合考慮領導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
5.3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在樣本的地域分布上,本研究的問卷集中于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未面向全國不同地區發放問卷,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結果的有效程度和推廣范圍。未來可嘗試多地區收集數據,以保證數據的可靠性。其次,本文是一項橫截面研究,在同一時間進行數據收集,難以反映出盡責性、組織倫理氣氛、社會責任導向人力資源管理對于責任型領導的動態影響過程。后續研究有必要采用縱向研究設計,對員工進行追蹤調查,使得變量間的關系更加具有說服力。最后,本文認為未來的研究還可以在以下方面進一步深化:一是考慮自利型組織倫理氣氛、規則型組織倫理氣氛的調節作用機制;二是探索盡責性是否通過某個中介變量影響責任型領導;三是探索領導者的其他人格特質如宜人性、開放性等是否一樣可以預測責任型領導。
參考文獻:
[1] PLESS N M. Understanding responsible leadership:role identity and motivational driv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4(4):437-456.
[2] MAAK T.Responsible leadership,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4(4):329-343.
[3] PLESS N M, MAAK T. Rel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leading responsibly in a connected world[C]//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Briarcliff Manor, NY 10510:Academy of Management, 2005:I1-I6.
[4] VOEGTLIN C. Development of a scale measuring discursive responsible leade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8(1):57-73.
[5] 郭億馨,蘇勇.責任型領導對下屬組織公民行為的雙刃劍效應[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8,39(5):90-102.
[6] 宋繼文. 責任型領導與企業社會資本建立——怡海公司的案例研究[C]//中國企業管理案例論壇. 2008.
[7] 邱茜.人格特質對破壞性領導的影響研究——基于工作滿意度和組織認同的中介作用[J].東岳論叢,2016(3):179-185.
[8] STAHL G K, DE SULLY L M. Antecedents of responsible leader behavior:a research synthesi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4, 28(3):235-254.
[9] TEPPER, B. J.Abusive supervision in work organizations:review synthesis,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33):261-289.
[10] 孟慧. 特質目標定向與變革型領導[J]. 心理科學, 2005, 28(2):444-446.
[11] BARRICK M R, MOUNT M K, JUDGE T A. The FFM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job performance:meta-analysis of meta-analys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2001, 9(1/2):9-30.
[12] ROBERTS B W, JACKSON J J, FAYARD J V, et al. Conscientiousness.[J]. 2009.
[13] ROBERTS B W, CHERNYSHENKO O S, STARK S, et al. The structure of conscientiousnes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seven major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s[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5, 58(1):103-139.
[14] ROBERTS B W, BOGG T, WALTON K E, et al. A lex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lower-order structure of conscientiousnes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4, 38(2):164-178.
[15] MAAK T, PLESS N M. Business leaders as citizens of the world:advancing humanism on a global scal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 88(3):537-550.
[16] 時陽,李天則,陳曉.責任型領導:概念,測量,前因與后果[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7(1):6-15.
[17] DUGAN J P. Involvement and leadership: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6, 47(3):335-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