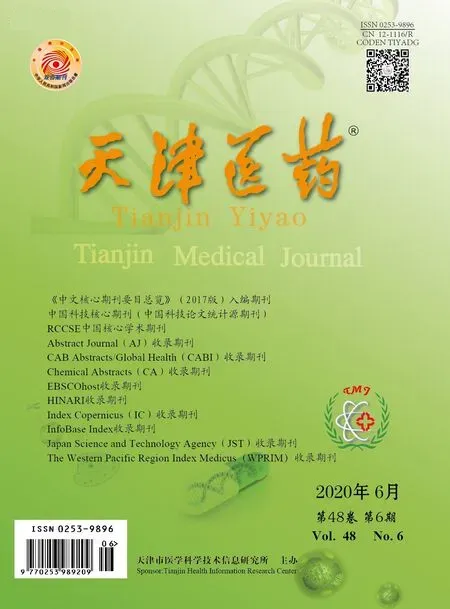河南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排除病例和確診病例分析
潘靜靜,范威,王文華,聶軼飛,尤愛國,王博昊,葉瑩,黃學勇,郭萬申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主要表現為發熱、干咳、乏力等,重癥患者可伴發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呼吸衰竭、休克等并發癥,目前無特效的治療藥物或疫苗[1-4]。該病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出現,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目前,COVID-19 病例的排除和確診均依據實驗室核酸檢測結果,病例排除率很高,但存在假陰性情況。本研究通過比較河南省確診和排除病例的流行病學和臨床特征,以期為臨床診療和防控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信息系統中河南省 2020 年 1 月 21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報告的COVID-19病例傳染病報告卡和個案調查表。納入所有被診斷為疑似但排除的病例和確診病例。排除標準:數據清理后,項目缺失或有異常值、邏輯錯誤的病例排除在分析之外。由于缺失值數量在不同分析項目之間不同,因此分析時樣本量不同。
1.2 指標收集 主要關注COVID-19 疑似排除病例和確診病例的基本人口學特征(性別、年齡等)、臨床嚴重程度、既往史、臨床癥狀(發熱、干咳、乏力、咳痰、胸悶、呼吸困難等)、血常規檢查、胸部X 線檢查、胸部CT 檢查、關鍵時間間隔和流行病學暴露史等。
1.3 病例定義與臨床分類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5],疑似病例:有流行病學史中的任何1 條,且符合臨床表現中任意2 條。無明確流行病學史的,符合臨床表現中的3 條。臨床表現包括:(1)發熱或者呼吸道癥狀。(2)具有病毒性肺炎影像學特征。(3)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具備以下病原學證據之一,即通過實時熒光定量逆轉錄聚合酶鏈反應(qRT-PCR)檢測疑似病例的血液或呼吸道標本中新型冠狀病毒核酸陽性,或通過基因測序與已知的冠狀病毒高度同源。排除病例:疑似病例連續2次核酸檢測陰性(間隔24 h)即排除。根據診療方案將臨床嚴重程度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以最嚴重的狀態為準。本研究將癥狀分為輕癥(輕型和普通型肺炎)和重癥(重型肺炎和危重型肺炎)進行比較分析。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Excel 2010 和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定量資料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2獨立樣本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用χ2檢驗進行比較。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基本特征 共收集5 635 例,其中確診病例1 267例(22.5%),疑似排除病例4 368例(77.5%);男3 078 例(54.6%),女2 557 例(45.4%),中位年齡37歲,排除病例和確診病例中性別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確診病例年齡大于排除病例(45歲vs.34歲,Z=14.857,P<0.01)。見表1。
2.2 流行病學史 在發病前14 d 內,1 449 例(34.4%)有武漢及周邊地區或其他有病例報告地區旅居史,為輸入病例。2 174 例(52.1%)有醫療機構就診史,1 568 例(37.6%)有與武漢及周邊地區或其他有病例報告社區旅居人員接觸史。除了醫療機構就診史外,確診病例中有武漢及周邊地區旅居史、與確診病例或無癥狀感染者接觸史、與來自武漢及周邊地區人群接觸史、涉及聚集性疫情、住所周圍有農貿市場和去過農貿市場等暴露史比例均高于排除病例,而暴露史不明確的比例低于排除病例(P<0.01)。見表1。
2.3 臨床特征 輕癥病例4 159例(94.9%),重癥病例225 例(5.1%),確診病例和排除病例中重癥比例分別為11.6% 和2.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49.938,P<0.01)。確診病例中合并慢性基礎性疾病、發熱、干咳、乏力、胸悶、腹瀉、白細胞正常或減少、淋巴細胞減少、胸部CT 異常比例高于排除病例(P<0.01);確診病例白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均低于排除病例,而淋巴細胞比例高于排除病例(P<0.01)。確診病例發病到報告、報告到確診、發病到確診的時間間隔短于排除病例,而發病到首診、發病到入院、發病到隔離的時間間隔長于排除病例(P<0.01)。見表2~4。

Tab.1 Comparison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epidemiological history between excluded and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 Henan province表1 河南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排除與確診病例基本特征和流行病學史比較
3 討論
河南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疑似病例的排除率近78%,早期排除率較低,隨著疫情發展,排除率逐漸增大。可能由于早期病例大多是從武漢及周邊地區返鄉人員,流行病學史比較明確,診斷標準比較嚴格,因此疑似病例被確診的可能性大。后期大多為本地病例,為了盡可能發現更多病例,診斷標準放寬,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范圍擴大,因此更多的人會被診斷為疑似病例,確診率會降低。
早期診斷對于疾病治療和防控意義重大。疑似病例的確診和排除主要依靠核酸檢測結果,但由于采樣方法、采樣種類和檢測試劑等原因,該方法存在一定假陰性率,有些地區已經發現多次檢測陰性后再次檢測陽性,或者出院時陰性而出院后復測陽性的情況,可能與核酸檢測的假陰性有關。這給臨床診療和疫情防控均帶來了挑戰,排除的病例可能會成為潛在的傳染源,也給臨床診療造成一定的困擾。
本研究發現,確診病例中位年齡大于排除病例,確診病例中重癥病例所占比例(11.6%)明顯高于排除病例(2.6%),確診病例中有慢性基礎性疾病、發熱、干咳、乏力、胸悶、腹瀉、白細胞正常或減少、淋巴細胞減少、胸部CT 異常比例均高于排除病例,白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和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均低于排除病例。病毒感染人體后,抗病毒反應會限制病毒復制,并進一步激活特異性的體液或細胞反應,細胞因子釋放增加,誘發細胞因子風暴,導致全身的炎癥反應,外周血白細胞和其細胞分類是評估炎癥的有效指標[6-7]。有報道顯示,外周血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是機體免疫反應的重要指標,被廣泛應用于診斷和預測與炎癥反應密切相關的疾病中[8-10]。

Tab.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xcluded and confirmed COVID-19 cases表2 COVID-19排除與確診病例臨床特征比較

Tab.3 Comparison of laboratory results between excluded and confirmed COVID-19 cases表3 COVID-19排除與確診病例實驗室檢查結果比較

Tab.4 Comparison of onset time between excluded and confirmed COVID-19 cases表4 COVID-19排除與確診病例發病時間比較 M(P25,P75)
確診病例發病到報告、報告到確診、發病到確診的時間間隔短于排除病例的相關時間間隔,主要是因為疑似病例需經過2次核酸檢測陰性(間隔24 h)才能排除。而發病到首診、發病到入院、發病到隔離的時間間隔長于排除病例,可能是因為過早就診,咽拭子等標本中病毒量有限,不能被實驗室檢測發現。
比較確診病例和排除病例的流行病學史發現,確診病例中發病14 d前有武漢及疫情地區旅居史的比例大于排除病例。此外,與確診病例接觸史、與來自武漢等疫情地區居民接觸史、與來自武漢等疫情地區發熱和呼吸道癥狀人員接觸史、涉及聚集性疫情、住所周圍有農貿市場和去過農貿市場的比例均高于排除病例。確診病例中暴露史不明確的比例低于排除病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排除病例還是確診病例,發病14 d 前醫療機構就診史比例均高于50%,提示在疾病流行期,還是有很多人員到醫療機構就醫,可能增加院內感染的風險。
綜上,在對COVID-19病例進行診斷時,除了考慮病原檢測結果外,還要綜合考慮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尤其是接觸過高危人群、涉及聚集性疫情且具有發熱、干咳、胸悶、腹瀉等臨床表現、血常規白細胞計數減少、胸部CT 異常的疑似病例,在核酸檢測陰性的情況下,應繼續規范采樣檢測,可考慮將口咽拭子改為鼻咽拭子或其他樣本,提高檢測陽性率。同時做好隔離,防止疫情傳播。另外,需加強健康教育,提醒公眾疫情期間盡量避免到醫療機構,做好患者的預檢分診和隔離救治,輕癥病例和重癥病例分別采取不同的就診和救治方式,防止醫院內感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