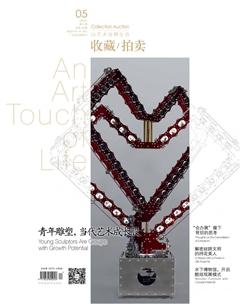缺席的女性聲音
張小雪
全球疫情暴發(fā)期間,美國(guó)女性主義藝術(shù)家海倫·艾龍(Helene Aylon)因新冠肺炎離世,我們突然想到了缺席的女性聲音。
《現(xiàn)代藝術(shù)150年》的作者,評(píng)論家維爾貢培茲在講述現(xiàn)代藝術(shù)發(fā)展過(guò)程中,提出了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我們沉浸于一波又波宣言的浪潮中,他們邀請(qǐng)所有人前去參加無(wú)所顧忌的藝術(shù)盛宴。然而,在所有這一切建立新烏托邦、搗毀舊統(tǒng)治的喧囂中,有一個(gè)聲音缺席很久了……”這個(gè)缺席的聲音,就是女性藝術(shù)家的聲音。
早在1971年,女性主義藝術(shù)史家琳達(dá)諾克林(Unda Nochlin)的文章《為什么沒(méi)有偉大的女性藝術(shù)家》就在藝術(shù)評(píng)論界引起轟動(dòng)。琳達(dá)·諾克林指出,“在視覺(jué)藝術(shù)中,婦女作為被男性凝視的物體非常普遍,女性的身體經(jīng)常是作為性的聯(lián)想而出現(xiàn)。在藝術(shù)界的運(yùn)作中女性同樣處于被忽視的地位”。
從印象派畫(huà)家貝爾特·莫里索到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畫(huà)家弗里達(dá)·卡羅,得到認(rèn)可的女藝術(shù)家不在少數(shù)。但是從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一路看來(lái),整個(gè)藝術(shù)史的敘事,重大的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和藝術(shù)大師還是以男性為主,女性只是男性藝術(shù)家們的妻子、情人或繆斯。瑪麗卡薩特更多地作為印象派大師埃德加·德加的情人被當(dāng)時(shí)的人們所熟知,她女性畫(huà)家的身份幾乎被忽略。在藝術(shù)教育領(lǐng)域,1850年前女性被禁止參與人體寫(xiě)生課程。1897年法國(guó)女星才被允許跟男性一樣進(jìn)入國(guó)家高等美術(shù)學(xué)院。究其根本,女性在藝術(shù)領(lǐng)域中的“被消失”與女性的社會(huì)地位變化分不開(kāi)。藝術(shù)具有雙面性,它有既定的行業(yè)機(jī)制,被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束縛著,同時(shí)又具有對(duì)規(guī)則的反叛性。
法國(guó)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xiě)道,“一個(gè)人之為女人,與其說(shuō)是天生的,不如說(shuō)是被塑造的”。“女性”是在社會(huì)進(jìn)程中逐漸顯示出的“社會(huì)性別”。1920年8月26日,賦予婦女和男性相同選舉權(quán)的美國(guó)憲法第十九修正案才被通過(guò),直到1928年英國(guó)婦女才有了平等的選舉權(quán)。
在藝術(shù)史上,第一個(gè)只有女性藝術(shù)家參與的展覽在1942年的紐約,由“現(xiàn)代藝術(shù)之父”馬塞爾·杜尚協(xié)助古根海姆博物館館長(zhǎng)佩吉·古根海姆女士策劃。評(píng)論家Henry McBride毫不隱瞞對(duì)女性的偏見(jiàn):“女人確實(shí)比男人更有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天賦。畢竟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所需要的是70%歇斯底里,20%文學(xué)修養(yǎng),5%畫(huà)工,5%忽悠觀眾。醫(yī)學(xué)數(shù)據(jù)顯示女人更容易神經(jīng)過(guò)敏。”
然而,這場(chǎng)展覽中層出了后來(lái)被認(rèn)為是超現(xiàn)實(shí)主義代表作之一的瑞士藝術(shù)家梅雷特·奧本海姆的《皮毛餐具》。日常的餐具上長(zhǎng)滿了長(zhǎng)毛的顛覆造型直指人心底對(duì)于未知和失控的恐懼不安。同時(shí)也諷刺了資產(chǎn)階級(jí)把大量時(shí)間浪費(fèi)在咖啡廳閑聊和處于虛榮虐待美麗動(dòng)物。協(xié)助策劃這場(chǎng)展覽的杜尚,也曾以名為“蘿絲·瑟拉為”的法國(guó)貴婦形象出鏡。
近年來(lái),各大美術(shù)館中女性藝術(shù)家展覽比例和藝術(shù)市場(chǎng)中女性藝術(shù)家作品的價(jià)格不斷提高。即便如此,在世藝術(shù)家作品最高價(jià)格紀(jì)錄中,女藝術(shù)家珍妮。薩維爾的《支撐》大約為男藝術(shù)家大衛(wèi)·霍克尼《藝術(shù)家肖像(泳池與兩個(gè)人像)》的十分之一。兩性在藝術(shù)領(lǐng)域中仍然存在著巨大的發(fā)展機(jī)遇和收益的差異。僵化的現(xiàn)實(shí)由來(lái)已久,改變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