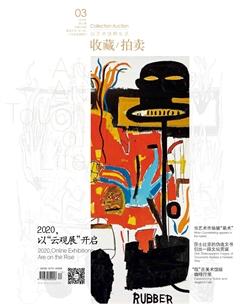金粟工藝,小金珠的玲瓏魔法
劉星辰



在中西方歷史中,黃金文化源遠流長,它被看作是太陽的化身。黃金不僅是硬通貨幣,還是名貴奢侈品的重要原料之一,黃金的使用與社會等級和宗教信仰緊密相連。在先秦時期,人們將金、銀、銅都稱為金,分別是黃金、白金和赤金,即“金三品”。但《漢書·食貨志》中有明確記載,“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黃金最為珍貴。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黃金制品為新石器時期文物,如1976年在甘肅玉門市清泉鄉境內的火燒溝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金耳環。而歷經數千年的發展,黃金制作裝飾工藝日趨成熟,精益求精,本文討論的金粟工藝就是黃金制品的重要裝飾工藝之一,它以精巧的設計和先進的技術,在傳統與現代金飾中都占據著重要地位和影響力。
黃金化學性穩定,只可溶于王水和水銀,并且具有極強的延展性和可鍛性。基于黃金特有的化學性和物理性,衍化出了專門的黃金加工工藝,稱之為細金工藝。細金工藝種類繁多,如掐絲、鑲嵌、錘揲等,金粟工藝也是其中之一。
金粟工藝,又細分為金珠、金炸珠。金筐寶鈿工藝等。通俗來說,就是將黃金制成直徑極微小的球形顆粒,然后將它們以一定的形式排列、焊接在金器的表面或邊緣,也可作為主體或局部的紋飾。這種工藝比起錘揲、鏨刻等其他細金工藝更為復雜,視覺立體感更強。在光束的照射下猶如繁星點點,反射出璀璨光芒,格外精美。
金粟成珠之法
就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我國金粟工藝出現的時間在戰國中期。金粟工藝制品主要有“服飾首飾”“貨幣”“飲食用具”“兵器飾件”“宗教法器”和“模型器具”六大類,分布地區也十分廣泛,北方、中原、南方地區均有出土發現,常見于新疆、內蒙古、陜西、河南、江蘇、廣東、廣西等省份。
制造金粟的傳統方法有吸珠法、撥珠法、研磨法和吹珠法四種。吸珠法的工藝現在已不得而知。撥珠法是將正在溶融的金液,往種球面物體上撥,利用沖擊力,使團聚的金液分散開來,形成細小的顆粒。研磨法是用金絲裁剪成大小一致的小金粒,放在兩塊質地堅硬、表面平整的小木板之間,轉動上層木板進行研磨。吹珠法又叫熔珠法、炸珠法,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把細金絲剪成大小一致的小金粒放在細沙盤上或碳末盤上,用吹管對準油燈蓋的火焰有節奏地吹鼓,使火焰被吹向砂盤上的小金粒,讓其燒紅達到焰融的程度,冷卻后便形成了小金珠;另一種是將黃金溶液滴入溫水中,使之凝結成大小不等的金珠。
現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1975年出土于新疆焉奢博格達泌古城的漢代八龍紋嵌寶金帶扣就是研磨法制成的金粟飾品。此帶扣重48克,采用了錘揲。掐絲。鑲嵌。炸珠等多種復雜工藝制作而成,其款式與現代的腰帶帶扣幾乎一致。其上裝飾有一條大龍和七條小龍,龍姿翻騰跳躍。靈動飄逸。龍眼上鑲嵌著紅寶石,龍身還裝點著幾顆綠松石,龍身花紋和水波紋用金絲焊接而成,其間滿綴小金珠。金粟顆粒目測直徑在Q3-Q6毫米之間,這些細如金沙的珠子就是先將金絲斷成等長的小段,然后溶融聚結成粒,再在兩塊平板間碾研加工而成。與其類似的,還有湖南省博物館藏,湖南安鄉劉弘墓出土的漢晉金框粟珠嵌松石帶飾。
金粟鑲嵌,渾然一體
金粟工藝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其制作,將微小的金珠按一定的規律排列在金器表面,如何固定和連接也是很困難的事情。金粟裝飾與制品主體之間可焊接、可黏接。常見的方法是先用白芨等黏著劑暫時固定位置,然后撤點焊藥,經加熱熔化,焊藥冷卻后達到焊接目的。焊藥的主要成分一般用硼砂、金粉、銀粉按比例混合而成,高超的焊技幾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跡。兩漢金器上裝飾性很強的魚子紋或聯珠紋大都足以金珠焊黏而成的。
根據科技考古測定。我國境內的早期焊珠制品(唐代之前),不論珠粒還是主體,都是組成成分不同的黃金合金材質,如李任冠飾上某粒金珠的組成成分為金49.9%、銀48.5%、銅1.6%,基座成分為金58.2%、銀40.3%、銅1.5%。然而,來自馬西格利亞納的7世紀胸針是金粟焊接在鍍金銀基體之上,公元前2350年至公元前2100年之間的特洛伊針飾是金珠粒焊接在銅基體之上,文獻資料里又有記載來自希臘、歐洲中部和北部的銀質焊珠工藝制品,還有15世紀西班牙馬具上的銅質焊珠。
金粟工藝還常與掐絲工藝和鑲嵌工藝同時使用。河北定縣東漢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的掐絲金辟邪與掐絲金羊群,動物形象通體以金絲構成但其外部輪廓卻綴滿金珠。西安沙坡村出土的東漢時期金灶,通體近橢圓形,灶門為長方形,裝飾有金絲和金珠。灶身用掐絲法制成,內嵌綠松石。灶面上有一釜,釜內盛滿了金粟米,制作極其逼真。此器制作先后采用打制、掐絲、壘絲、焊綴和鑲嵌等工藝,整體感覺繁復但精巧,代表了東漢時期最為先進的工藝。
進入盛唐時代,出現了將金粟與鑲嵌結合的“金筐寶鈿”工藝,金粟工藝達到頂峰。該工藝運用廣泛,形制多樣,與同時期其他工藝,如寶鈿、花鈿、金(銀)鈿。鬧裝、寶裝等既有交叉又有區別。雖然此種工藝盛行于唐代,但實際在先秦至漢時期已開始流行。陜西省長安縣南里王村唐竇嗷墓出土的玉梁金筐真珠蹀躞帶就是唐代“金筐寶鈿”工藝的代表性作品。玉帶制作始于隋唐,是一種由數塊乃至十數塊扁平玉板鑲綴的腰帶,是古代官階品位的標志,以金玉最為珍貴。在每塊玉帶板的下方,帶有能掛載小物品的小勾的玉帶便被稱呼為“蹀躞帶”。玉梁金筐真珠蹀躞帶以玉為緣,內嵌珍珠及紅、綠、藍三色寶石,下襯金板,金板之下為銅板,三者以金鉚釘鉚合,造型精巧,裝飾豪華,是一件極精美的藝術珍品。
東西交融的產物
通過目前掌握的金粟工藝考古材料,我們可以得出中西方在金粟工藝發展交流中的時空線索。我國金粟工藝的發軔期是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時期,那時的金粟工藝制品尚不是裝飾的主流產品,它往往作為玉器的配角出現。發展至戰國晚期,北方草原地區的金粟工藝制品常以點狀或線狀焊接在器物表面,例如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的戰國鷹頂金冠飾,鷹身與尾羽連接處有兩行現狀金粟裝飾。這種焊接手法的來源是西方地中海國家,他們往往將四顆金粟焊為一組,并隨著地中海文明的擴張,影響到了我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之后又通過戰爭與貿易而間接將金粟工藝引入中原。
漢唐時期是金粟工藝快速發展,直至巔峰的時期。漢武帝時代的張騫通西域,使中原與西域的交往更加通暢,中亞風格的滿鋪金粟的風格傳人,1983年寧夏固原南郊九龍山漢墓出土的西漢鑲松石金帶飾上的工藝便是西域金粟工藝進入中原的有力證據。帶飾上下兩邊做成由小圓圈組成的陽文幾何圖案,中間用弧線與小圓圈做成桃形圖案,中間圓心呈陽文,鑲有紅綠相間的松石,制作工藝非常精巧。
而與陸路傳播相輝映的是東南海路的技藝傳人。廣州先烈路龍生崗西漢墓和江蘇邗江甘泉東漢墓等地出土的空心金粟小球,可能預示著金粟工藝進入中原的路徑更為復雜。這種羅馬風格的金粟球可能為西方傳入,也可能是本土仿制。空心金粟球同樣見于湖南長沙五里牌李家老屋的東漢墓(直徑1cm-1.5cm),共出土11顆,推測可組成一串項鏈。并且海路金粟風格的轉入,并未止于中國,公元6世紀的百濟國忠潔南道公州市武寧王陵出土了一串此類風格的金項鏈。因此說明金粟工藝的傳播由海路陸路并進,從實物、形制、工藝等多方面影響我國金粟工藝的發展演進。
金粟工藝延續數千年,今時今日依舊為大眾追捧,這就是“古為今用”的最好體現吧!古代的金粟工藝或許是繁復的,但現代飾品藝術已將其提煉創新,獲得了更多趣味。就好比現在我們再談及金粟,大家可能會想到的是梵克雅寶四葉幸運系列項鏈,它將傳統金珠工藝與寓意幸運的四葉草元素相結合,以金珠點綴方式與白色珍珠母貝進行強烈對比,極富幾何美感,線條簡潔輕盈,擺脫了傳統金珠首飾的厚重感,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