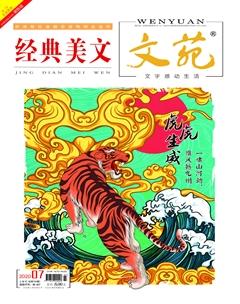姐姐張愛玲的青春見證
張子靜 季季
見證·姐姐的文學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姐姐在《天才夢》里的這句話,十分抽象,但也十分貼切。在她發展天才夢的過程中,我母親與我父親的角色是推動者,我姑姑的角色則是照顧者。這三個人對姐姐文學志業的發展,每一階段都有很深的影響。至于我,我是一個見證者。而且是如今,唯一的幸存者。
文憑才是真正的財富,知識才是獨立的力量,這是我母親從自身經驗得到的深刻體悟。在培育我姐姐的天才夢進程中,這種體悟煥發出來的母性光彩,完全迥異于一個傳統中國母親的角色。我姐姐很小的時候,她就教她認字,如我姐姐在《私語》里寫的:“每天下午認兩個字之后,可以吃兩塊綠豆糕。”稍大一點,她就教她背誦唐詩絕句,教她畫圖。她教的是中國的東西,但她的出發點是西方的。對我姐姐的教育,她從未放松,每一階段都適時地抓緊,幾次回國也都是為了我姐姐的教育問題。她可說是推動我姐姐天才夢的第一要角。
姐姐移居美國后,以十年的時間研究《紅樓夢》,后來出版了《紅樓夢魘》這本書,可見她對《紅樓夢》用情之深。而她研究《紅樓夢》的啟蒙師,就是我的父親。她十四歲時的習作《摩登紅樓夢》,回目就是我父親代擬的。
姐姐常介紹書給我看,也常和我談論文學。記得她常常談起的一些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馬》《牛天賜傳》《駱駝祥子》以及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冰心的短篇小說和童話等等。
至于外國文學,我印象較深刻的是她看過《琥珀》(《Forever Ember》)后說,書中描寫十六世紀倫敦大瘟疫之后,街道的荒蕪凄涼景象讓她覺得陰森可畏。至于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描寫香格里拉的《失去的地平線》(《The Lost Horizon》),她也覺得某些描繪“使人渾身發冷,好像跌進了冰窖”。她還介紹我看毛姆和歐·亨利的小說,要我留心學習他們的寫作方法。
一九四二年她從香港大學輟學回上海后,有一次又和我談到寫作。那時她尚未成名,但談起寫作已像一個經驗老到的作者。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她已為成名做好了周全的準備。她講的原話與我現在寫的,可能詞句有些出入,但意思是完全符合的。她說:積累優美詞匯和生動語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隨時隨地留心人們的談話;不管是在路上、車上、家里、學校里、辦公室里,一聽到后就設法記住,寫在本子里,以后就成為你寫作時最好的原始材料。
要提高英文和中文的寫作能力,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這樣反復多次,盡量避免重復的詞句。如果能常做這種練習,一定能使你的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進步。
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但沒有勇氣去努力實踐。因為我于文學只是欣賞,并無積極的創作欲望。
除了文學書籍,她的床頭還擺著美國的電影雜志。
除了文學,姐姐學生時代另一個最大的愛好就是電影。她當時訂閱的一些雜志,也以電影刊物居多。在她的床頭,與小說并列的就是美國的電影雜志,如《Movie Star》《Screen Play》等等。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著名演員主演的片子,她都愛看。如葛麗泰·嘉寶、蓓蒂·戴維斯、瓊·克勞馥、加利·古柏、克拉克·蓋博、秀蘭·鄧波兒、費雯麗等明星的片子,她幾乎每部必看。
中國的影星,她喜歡阮玲玉、談瑛、陳燕燕、顧蘭君、上官云珠、蔣天流、石揮、藍馬、趙丹等。他們演的片子,她也務必都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她到杭州去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親戚朋友很多。剛到的第二天,她就從報紙廣告看到談瑛主演的電影正在上海某家電影院上映,立刻就說要趕回上海去看。一干親戚朋友怎樣攔也攔不住,我只好陪她坐火車回上海,直奔那家電影院,連看兩場。迷電影迷到這樣的程度,可說是很少見的。但這也說明我姐姐與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格。對于天才夢的追尋,她一向就是這樣執著的。
見證·白描姐姐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島時期”,我和幾位同學決定合辦一個刊物——《飆》。希望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飆》能帶來一陣暴風雨,洗刷人們的苦悶心靈。記得當時約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樂山等。但編輯張信錦對我說:“你姐姐是現在上海最紅的作家,隨便她寫一篇哪怕只是幾百字的短文,也可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約稿。
還沒走到姐姐的住處,我就想到這樣貿然前去似乎不大穩當。姐姐當時可說是紅得發紫,向她約稿的著名報紙雜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個“寫作機器”也應付不了那許多約稿。果不其然,聽完我的來意,她一口回絕:“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說完她大概覺得這樣對我不像個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張她畫的素描說:“這張你們可以做插圖。”——她那時的文章大多自己畫插圖。
我從小被姐姐拒絕慣了,知道再說無益,就匆匆告辭。回來之后,張信錦說:“那就請子靜先生寫一篇關于你姐姐特點的短文,這也很能吸引讀者。”
我擔心姐姐看了會不高興,而在報上寫出聲明或否認的文章。但張信錦說:“不會吧?一來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認?二來稿子的內容一定無損于她的聲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顯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證不會出什么問題的。”
張信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氣。于是我憑著自小對她的觀察,寫了《我的姐姐張愛玲》:
她的脾氣就是喜歡特別:隨便什么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就拿衣裳來說吧,她頂喜歡穿古怪樣子的。記得三年前她從香港回來,我去看她,她穿著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顏色的底子,上面印著一朵一朵藍的大花,兩邊都沒有紐扣,是跟外國衣裳一樣鉆進去穿的。領子真矮,可以說沒有,在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只到膝蓋。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旗袍,少不得要問問她這是不是最新式的樣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種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這樣不夠特別呢!”嚇得我不敢再往下問了。我還聽別人說,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的哥哥結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去道喜,滿座的賓客為之驚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樣少見多怪。
還有一回我們許多人到杭州去玩,剛到的第二天,她看報上登著上海電影院的廣告——談瑛演的《風》,就非要當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樣挽留也沒用。結果只好由我陪她回來,一下火車就到電影院,連趕了兩場。回來我的頭痛得要命,而她卻說:“幸虧今天趕回來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難過呢!”
她不大認識路,在從前她每次出門總是坐汽車時多,她告訴車夫到哪里去,車夫把車開到目的地,她下車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讓我到工部局圖書館去借書,我問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說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覺得奇怪,我們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認識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總跟別人兩樣點吧。
她能畫很好的鉛筆畫,也能彈彈鋼琴,可她對這兩樣并不十分感興趣。她還是比較喜歡看小說。《紅樓夢》跟英國小說家毛姆寫的東西她頂愛看。……還有老舍的《二馬》《離婚》《牛天賜傳》,穆時英的《南北極》,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歡看的。她現在寫的小說,一般人說受《紅樓夢》跟毛姆影響很多,但我認為上述其他各家給她的影響也多少有點。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說:“你姐姐真有本事,隨便什么英文書,她都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學。”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寫法。至于內容,她不去注意,這也是她英文進步的一個大原因。她的英文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即使我再學十年,也未必能趕得上她一半。
她曾經跟我說:“一個人假使沒有什么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閑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大家都曉得有這么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這也許就是她做人的哲學。
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飆》創刊號發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讀者。姐姐給我的那張素描《無國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這是我們姐弟此生唯一的圖、文合作。
雜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給姐姐,她看了我的“處女作”,并沒有表示不悅,我才放了心。
摘自《我的姐姐張愛玲》(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