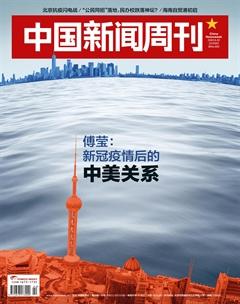憶那個帶我們“走出大峽谷”的人

余澤民
布達佩斯的清晨,我剛醒來打開微信,就獲知了噩耗:83歲的李西安老師于6月4日22時在北京病逝。
李老師在音樂圈里很有影響,因為他對中國音樂發展的貢獻可觀。作為融貫中西的作曲家,他既創作過《G大調鋼琴小奏鳴曲》,還寫過民族室內樂《婆羅門引》;作為民族音樂理論家,他留下了《漢語聲調與漢族旋律》和《中國民族曲式》;作為音樂教育家,他慧眼識珠,桃李滿天下。在李老師寬廣的音樂人生里,我頂多算一個過客,但李老師于我,卻是一個改變我生命軌跡的人。
19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風起云涌的黃金年代。作為中國音樂的弄潮兒和開拓者,李西安提出“在古老的傳統和現代的新學科之間,構筑一個巨大發展空間”的辦學方針,在他擔任院長的中國音樂學院親辟了幾塊跨學科的“試驗田”,其中有音樂教育、音樂治療、藝術管理和藝術心理。我就是在1989年作為藝術心理學碩士研究生被招進去的。那一年我從北醫臨床醫學系應屆畢業,本該去醫院穿白大褂、執手術刀,是他的教改給了我棄醫從藝的機會。
我記得很清楚,專業考場設在恭王府昏暗潮濕的一間老屋里。6萬平方米的恭王府號稱有“99間半”房,具體哪間我記不得了,只記得2月的京城還很寒冷。考試前,杜義芳和張鴻懿兩位主考老師特意帶我去跟李院長見了第一次。
李院長長發斜分,指間夾著一支沒點燃的煙,穿深藍色西服,沒打領帶,戴一副秀郎鏡,有一股我之前從未直面過的藝術范兒。他的音色低沉沙啞,聲調不高,雖然語速較慢,但也需要專注才能夠聽清。他說他已經了解了我的情況,期待我能通過考試,“歡迎你來學校幫助建設新學科”。這句原話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幫助”這詞讓我很受鼓舞,心里憋了一股要大干一場的勁。
后來我才知道,張鴻懿教授不僅是音樂學系主任、中國音樂治療學的創始人,還是李院長的夫人。本來我對音樂治療專業很感興趣,但由于那年這個專業只招大專生,所以我報考了杜義芳導師的藝術心理學專業。我學醫期間就熱衷于讀心理學的書,還憑興趣選了精神衛生研究所來做我的為期三個月的科研課題,原因就在于,我覺得醫學里心理學最文藝。
當我接到錄取通知書前去報到時,中國音樂學院已大部分搬到了葦子坑新校址,只留下一兩個專業在恭王府。李西安夫婦就住在學校對面的絲竹園小區,由于有些專業課程我跟張鴻懿老師的弟子們一起上,所以經常去他們家。
1991年秋我去匈牙利,他們夫妻也是鼓勵者。張老師說,搞新學科就需要放寬眼界,出去看看,并將幾位搞藝術心理學和音樂治療學的歐洲專家的信息抄在一張紙上叫我帶著。李老師則說:“既然決定出去闖,就闖出個眉目再回來。”
生活蹉跎,出國后我嘗盡漂泊的甘苦,最后走上文學的路。我每次回國都去看望他們,順便帶去我的新書。他們從未因我棄藝從文感到遺憾,而是說“文學跟音樂異曲同工”。的確,無論在寫作還是翻譯上,我在醫學院和音樂學院學到的知識都能派上用場。
李西安老師有一部影響很大的音樂文集《走出大峽谷》,記錄了他對中國音樂的思考和實踐。許多年來,他不僅帶領以譚盾、葉小剛、瞿小松、陳其鋼為代表的“新潮音樂群”走向了世界,也送我走進了更遼闊的天地。他自己更是一個披荊斬棘、尋徑拓路,從精神上走出大峽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