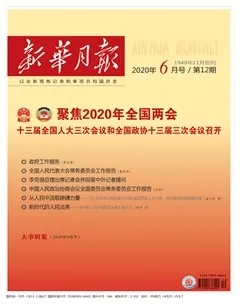當一扇門被關上,另一些窗注定會被打開
莫萬莉
作為一種誕生于18世紀的公共建筑,博物館為公眾打開了一扇通向一個廣闊的想象世界的窗。不過,很多人在參觀時,往往會忽略一件非常重要的展品:建筑。
當世界很多地方的博物館因為疫情而暫時關閉或有限開放時,不如我們來聊一聊博物館建筑。從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到巴黎盧浮宮,傳統(tǒng)的博物館建筑往往借鑒了紀念性建筑的形式主題,譬如運用希臘或是羅馬神廟的立面語言來塑造一種非日常的儀式感。莊嚴的山花,高聳的巨柱,行列式的柱廊,均暗示著在進入其中后,參觀者們便從日常生活中脫離開來,而進入到一個特殊的審美情境中。

時至今日,建筑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博物館不再僅僅倚重于經(jīng)典的建筑形式,而力圖探索著諸多可能性:既是一件空間意義上的藝術作品,以彰顯建筑藝術的獨特魅力,也與城市的文化身份和歷史記憶息息相關。博物館概念的寬泛化則進一步使得它們不再是往昔的令人生畏的藝術殿堂,而逐漸融入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邀請著名的建筑師將其打造成獨特的文化地標,使文博展館本身也成為了一件城市尺度上的藝術作品
一個為建筑師和文博界所津津樂道的案例便是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這座由美國著名建筑師弗蘭克·蓋里設計的作品或許是有史以來最為成功的一座博物館建筑,坐落于舊城邊緣、畢爾巴鄂河畔,由一系列鈦金屬表皮覆蓋的、如流水般靈動的體量組成。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既扭轉了曾經(jīng)的工業(yè)城市一度走向衰落的命運,也開啟了全球諸多城市借力于地標性的博物館、從而塑造其獨特文化身份的做法。
與傳統(tǒng)博物館的對稱布局和莊重外表相比,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顯得自由不拘。它的外觀猶如一組互相擠壓的漩渦狀海浪,又似乎是一簇綻放的金屬之花。無論如何,它與印象中的博物館的形象迥然相異。如果說傳統(tǒng)的博物館講究橫平豎直的對稱與平衡,那么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則恰恰突破了所有的形式法則。建筑師的恣意的想象力在此迸發(fā),形成了獨一無二的空間體驗。也正因為如此,它在建成之初,便吸引了全球的矚目,不僅在開館當年便為畢爾巴鄂貢獻了接近4%的財政收入,更進一步吸引了大量來自西班牙國內和海外的游客。它帶來的規(guī)模效應極大地推動了這座曾經(jīng)的工業(yè)城市的文化創(chuàng)意轉型。
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的成功被以“畢爾巴鄂效應”所命名,并成為當代文化產(chǎn)業(yè)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受到它的啟發(fā),在中東海灣地區(qū),受益于石油經(jīng)濟的阿布扎比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博物館之島——薩迪亞特文化島。對于這樣一片空白之地來說,借助博物館、打造文化地標的可行之道便是與業(yè)已成熟的博物館機構展開全球合作,并邀請明星建筑師為其打造具有標志性的場館。由此,古根海姆博物館與蓋里的再度合作便不足為奇。蓋里的設計延續(xù)著他一貫的解構主義風格,一系列形態(tài)迥異的曲面體力如積木般被堆疊,自由曲面構成的體塊、幾個高聳的筒狀結構和如紙片般被翹曲彎折的表面共同構成了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館的豐富幾何語言。
毗鄰這座未來博物館的則是業(yè)已建成的、法國著名建筑師讓·努維爾設計的阿布扎比盧浮宮。與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館類似,這座博物館同樣與歐洲老牌的盧浮宮進行了展陳計劃與展品收藏等方面的合作,而它的建筑則在具有標志性的形象之外,也與阿拉伯建筑文化產(chǎn)生著絲絲聯(lián)系。坐落于薩迪亞特文化島的入海口,一個由白色鋼鋁編織而成的巨大屋頂,仿若懸浮在半空之中,海港之濱。在它的下方,一系列簡潔的白色方盒子構成了一個個展廳空間。它們之間的組合并非一座完整的建筑,而被設想為一座博物館城市。小巷、廣場、庭院、走廊、河道,被引入其間,讓參觀者聯(lián)想到傳統(tǒng)的阿拉伯城市空間,而透過由八層不同的幾何圖案編織而成的穹頂,斑駁的陽光灑在建筑之間,仿佛透過阿拉伯花窗灑下的“光之雨”,被引入的河道的波光粼粼更使得整個場景顯得如夢似幻。整座建筑既無處不在地與阿拉伯文化產(chǎn)生著連結,也具有強烈的標志性。從海上遠眺之時,巨大的穹頂成為了博物館島乃至阿布扎比的新形象。

當下,博物館將其自身打造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藝術機構的雄心,也促成了諸多老牌博物館與新興藝術場址之間的合作。在上海,西岸美術館與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展開了一個五年的展陳合作項目,并邀請英國著名建筑師大衛(wèi)·奇普菲爾德設計了這一嶄新的文化地標。這位以極簡和古典的設計語言而著稱的建筑師并未如弗蘭克·蓋里或是讓·努維爾一般打造一座極具個性的建筑,而試圖通過平面的組織來構成一種反類型的美術館:觀看者不再被動地進入到另一個時空,而可以有所選擇,或是參觀展覽,或是訪問其公共空間。三個立方體展廳圍繞著中央的通高門廳布置,前者承載了主要的展覽功能,后者則成為一個連接起展廳、書店、咖啡等不同功能的開放空間。參觀者既可從西側的龍騰大道和東側濱江步道直接進入門廳底層,又可從下沉庭院或是經(jīng)由臨江廣場臺階,從二層露臺進入門廳上層。在東西貫通的門廳入口處,兩根上大下小的錐形巨柱構成了西岸美術館最為引人注目的部分。這兩根昭示著建筑入口的巨大柱體在抽象的立方體之間創(chuàng)造出一種具象的、擬人的化身。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競爭力往往是全球城市軟實力重要組成元素之一,而作為藝術載體的博物館則無疑是這種文化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如果說過去的博物館往往依賴于豐富的館藏作品和經(jīng)典的傳世之作,來吸引著大量的參觀者,那么在今天,博物館建筑的設計也構成了參觀拜訪的目的之一。邀請一位著名的建筑師來打造一個獨特的文化地標,這使得建筑本身也成為了一件城市尺度上的藝術作品。
在舊的工業(yè)遺存和新的博物館建筑之間,城市的記憶被編織于參觀者的空間體驗之中
正如展館誕生于一個現(xiàn)代性萌芽的時代,它也被現(xiàn)代性所塑造。現(xiàn)代社會對進步的癡迷使得博物館也同等程度地需要記錄、歸檔、展示和共享記憶來塑造進步。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核心,對進步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對歷史的梳理和對過去重拾的基礎之上的,而博物館和美術館即是整理和展示關于過去記憶的場所。伴隨著城市形態(tài)的發(fā)展與城市功能的變遷,它們不再只是往昔記憶的容器,作為建筑物,它們也往往承載著一段城市的記憶。
工業(yè)生產(chǎn)曾經(jīng)在城市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關鍵作用。然而,隨著第三產(chǎn)業(yè)的興起和全球化帶來的產(chǎn)業(yè)遷移,一些工業(yè)城市逐漸進入了轉型期,原先的工業(yè)廠房則被廢棄。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城市試圖通過工業(yè)場址的改造,既將這段城市記憶呈現(xiàn)于參觀者面前,又重新點燃工業(yè)遺存的空間活力。荷蘭大都會建筑師事務所(OMA)改造設計的魯爾博物館便是一個極佳的案例。魯爾工業(yè)區(qū)曾經(jīng)是全球最為重要的煤炭和鋼鐵重工業(yè)區(qū)之一,卻在上世紀后半葉由于世界能源的消費構成的改變等原因而逐漸衰落。魯爾博物館原為埃森關稅同盟煤礦遺址中的選煤廠。這座獨一無二的工業(yè)建筑原先依賴于巨大的戶外傳送帶將煤炭從建筑頂部傳送至選煤廠。如今,這條傳送帶則被改造為了戶外扶梯,將參觀者引導至博物館中。從頂部到底層,參觀者逐漸進入了一段關于魯爾地區(qū)的歷史漫游中。原先選煤廠的大部分機械設備被保留下來,提供著一種工業(yè)建筑所獨有的空間體驗。如果說傳統(tǒng)的博物館是靜思的審美體驗,那么魯爾博物館則在空間的運動中實現(xiàn)了展覽的目的。參觀者通過文字、圖像與展品了解那段城市記憶,與此同時也身處于這段記憶之中。
從工業(yè)場址到一座博物館,這些改造設計往往注重對往昔工業(yè)遺存的保留,并將它們視為設計的靈感來源。在大舍建筑設計的上海龍美術館中,一段場地中遺留的煤料斗卸載橋成為了設計的出發(fā)點。煤料斗卸載橋曾經(jīng)主要被用于運煤和卸煤,在使用時,一列火車會停在其下方,煤料則通過江邊的龍門吊、經(jīng)過傳送帶、通過漏斗而被導入每節(jié)火車的車廂中。如今,當煤料斗卸載橋喪失了其原有的功能之后,雖然運煤火車不再駛來,但火車車廂的尺度以及它所暗含的、曾經(jīng)在此發(fā)生的歷史卻被保存在了卸載橋的結構形式之中。由此,龍美術館不僅試圖通過新建筑與舊有的煤料斗卸載橋的并置來提示場地的歷史,也試圖在結構形式上與其建立一種類比。如同煤漏斗卸載橋一般,龍美術館的主體部分也由一個個重復的傘拱單元而形成。傘拱與傘拱之間,有時同向相接,形成一個具有軸線的對稱空間,有時則異向相接,形成一個更為自由的流動空間。最終,傘拱所形成的平面看似一幅蒙德里安的繪畫。傘拱在高度上的變化則使得空間更為流動和豐富:它不再如煤漏斗一樣是同一節(jié)奏的不斷重復,而仿佛如一片樹林。不同方向、大小各異的“樹冠”伸向天空,光線透過傘拱之間的縫隙灑落下來,如同樹林中透過葉片的縫隙而落下的陽光一般。
工業(yè)場址將一種融合了歷史與記憶的獨特性賦予于一座新建筑,而新建筑則恰恰使得那些一度被人遺忘的構筑物重新展現(xiàn)活力。在舊的工業(yè)遺存和新的博物館建筑之間,城市的記憶被編織于參觀者的空間體驗之中。

隱于城市的微型“博物館”猶如一個個建筑片段,顯露出藝術、生活與城市相遇之時所迸發(fā)的活力
如果說博物館在過去往往與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式的收藏相聯(lián)系,那么今天的博物館本身的定義或許業(yè)已被拓寬。它可以僅僅為一件收藏物而建造,或是隱匿于日常生活的街頭巷尾。
梓耘齋建筑設計的衡復微空間位于上海東湖路、新樂路、長樂路、富民路、延慶路的交匯口,曾經(jīng)是一座袖珍“博物館”。它坐落于一棟普通居民樓的底層,面積僅為30平方米。這一空間曾經(jīng)為一家輪胎店,常常由于維修和護理汽車的需求而占據(jù)街道空間。改造后的空間連帶居民樓的立面翻新,構成了五條道路交匯處的一個亮點。兩扇可360度旋轉的淺綠色大門是空間設計的關鍵性策略。它的開啟使得整個室內展廳能夠面向城市完全打開。匆匆而過的路人或許會不由自主地被兼做展墻的淺綠色大門所吸引,或是一窺展廳中的場景,而在展覽開幕或是特別活動之時,街道構成了室內展廳的延伸,城市空間也成為了展覽的一部分。如今,衡復微空間的運營已經(jīng)交給了當?shù)厣鐓^(qū)。這一富有創(chuàng)意的空間被保留了下來,其功能則從展示城市藝術變身為社區(qū)垃圾分類展示館。
位于上海新豐路的藝術微空間FlipPOP由兩位年輕的建筑師孫凱倫和劉金子設計,在市井之中創(chuàng)造出了一處為人們提供互相交流機會的文化場所。顧名思義,“flip(翻轉)”構成了這間約莫10平方米的小展廳的主要設計策略。一個兼門面、展架和立面于一體的可360度旋轉的“門”構成了這個極簡的展示空間與城市之間的界面。在這個普普通通甚至街道面貌有些雜亂的街區(qū),閉合的“門”透露著當代藝術的白盒子(用作常規(guī)藝術展示空間的統(tǒng)稱)的神秘感,而當它“翻轉”的那一瞬,藝術的空間被開啟,滲透至街道的日常生活中。
與上面兩個展示空間相比,建筑師相南設計的愚園路墻館則進一步將空間之“微”推向極致。如果說此前的藝術空間希冀著特定前來的參觀者,那么愚園路墻館則是一座完全為愚園路的過路人設計的“博物館”。建筑師構思了一個長約5.2米、緊貼原街道界面的超薄藝術空間。在人眼高度,一條寬約30毫米的玻璃槽成為了過路人窺視館內藝術品的窗口。過路人也可通過掃描二維碼的方式,提交自己的藝術創(chuàng)作作品。墻館的運營機構則會每月選取一位路人藝術家的作品進行展示。由此,這間占地不到一平方米的“博物館”成為了一個完全由路人完成創(chuàng)作與觀看的藝術空間。盡管最初愚園路墻館被設想為一個臨時建筑,但它因深受當?shù)厣鐓^(qū)居民和來往市民好評而被保留下來,直到后來道路翻新。
這些微型的“博物館”似乎也可以被視為一件件空間裝置。它們散落在城市之中,為人們在日常漫步的不經(jīng)意間,創(chuàng)造出一次與藝術相遇的體驗。或許從展品的質量或是重要性上來說,它們遠不能與機構化的博物館相比,但恰恰是它們的日常性和開放性使得藝術得以與生活融為一體。如果說作為文化地標的博物館建筑通過建筑師的具有標志性的設計語言建構起關于一座城市的“宏大敘事”,那么這些隱于城市的微型“博物館”則通過一個個片段顯露出藝術、生活與城市相遇之時所迸發(fā)的活力。
(摘自5月19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