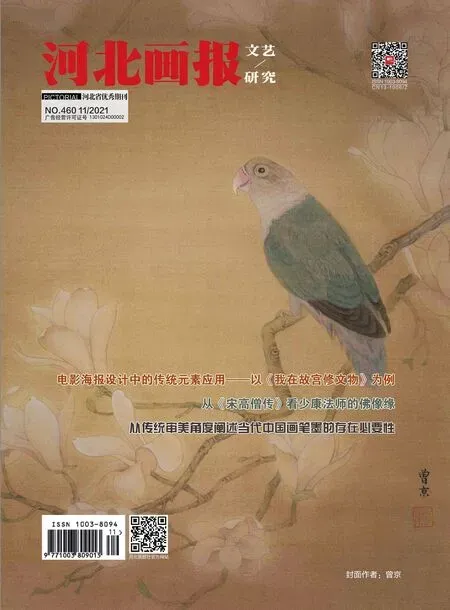試論中國中西部地區連珠紋裝飾的起源與文化特征
譚嫄嫄 張傅城
1.桂林電子科技大學;2.韓國又石大學
中國所見的連珠紋常用于陶器和金屬制品等器物的裝飾,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甘青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同時也是古代中國和其他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筆者在討論古代中國的連珠紋裝飾傳統時,主要聚焦甘青地區(甘肅、青海)和中原文化典型代表地區(河南、陜西)展開討論。
一、原始陶器上的連珠紋裝飾
甘青地區的彩陶是中國裝飾藝術的源頭,史前文化延續時間長,從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灣一期文化開始,延續5000多年,到距今2500年前的中國古代春秋晚期結束,不僅形成了完整的史前文化發展序列,而且每個文化均發現有彩陶,連珠紋是彩陶裝飾的其中一種典型紋樣,此類紋樣在彩陶裝飾中的不斷應用與發
展呈現出了一定的連續性。本文根據紋樣的形式對彩陶上的紋樣進行識別,發現在彩陶文化相關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將彩陶上重復連續排列的圓點描述為圓圈紋或圓點紋。這些紋樣形式豐富,除了單一的圓點連續紋樣,還有填充“十”字、“卍”字的組合圓點紋樣,以及圓點和鳥紋、神人紋間隔連續排列的紋樣組合圖像。彩陶上的紋樣是否能成為古代中華文明所見連珠紋的起源,需要通過紋樣在發展過程中的連續性和文化意義的甄別來判斷。史前文明的文化事項無共時性的文獻記載,只能通過紋樣的圖像語境(context)來進行文化意義的猜測。
關于甘青地區彩陶上的“圓圈紋”來源和意義,學術界爭議比較多,目前沒有定論。本文支持的學術觀點有以下兩種,一個是“太陽神”象征,另一個是珠串裝飾。(1)“太陽神”象征:從圓圈紋紋樣形式來看,紋樣通常是由同心圓或圓圈內加圓點構成。其文化意義被解讀為太陽崇拜的物化形式,是對太陽形象的描繪,是太陽神的化身。[1]馬廠文化類型時期,四大圓圈紋[2]繪制于陶器的明顯位置,每個圓圈皆以紅黑兩色繪成,內圈為紅色,外圈為黑色,周邊畫有直線紋和折線紋,從圖像形式看是對日出景象的一種描繪,從而推斷圓圈紋是對太陽形狀的模擬。與圓圈紋組合的“十”字紋、鳥紋、神人紋,也都是中國史前太陽崇拜的主題圖案。[3]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神人紋和連珠紋的組合圖像,力證了彩陶上連珠紋的太陽崇拜意義。神人紋的人像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巫師。《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記載:“夏后啟……乘兩龍,云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學界公認,夏族是以太陽神為至上神的。乘龍、操翳、持環、佩璜,夏后啟如此隆重登場,定是與祭祀其至上神“太陽神”有關。巧合的是,一件彩陶壺(甘肅省博物館藏)上的獸首人身圖案可與這則神話相印證。該壺上,怪獸裸體直立,右臂揚起,手中持一環狀物,和夏后啟的形象十分相似。這不僅是甘青先民持“石(玉)璧”向太陽祈禱的有力證據,而且進一步說明了手中“操環”的神人紋是巫師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齊家文化分布范圍內發現了6處“與祭壇的性質相類似”[4]的石圓圈遺跡, 其中位于甘肅省永靖縣(炳靈寺石窟的所在地)的秦魏家遺址有1處,大何莊遺址有5處。石圓圈遺跡,均是用天然的扁平狀礫石排列而成,直徑一般在4米左右,排列的形式與本文所討論的連珠紋形式一致。石圓圈旁邊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還有象征太陽光芒的赭石粉末,說明這些石圓圈遺跡亦是對太陽形狀的模擬。可以推測,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曾經在這些地方舉行向太陽祈求的儀式,死后,也虔誠地葬于其周圍,以便接受太陽神的召喚。(2)“珠飾”裝飾: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首飾,項鏈是全人類普遍擁有的審美文化現象,它們的誕生往往出于原始宗教祭祀活動的需要,后來才逐漸演化出禮儀、裝飾、身份象征等更多功能。部分彩陶上的圓圈紋是串珠配飾的表現。馬家窯出土的彩陶在人頭塑像和神人紋身體之間有一圈穿孔連珠紋,表示一串珠子裝飾項鏈。[5]。這個看法可以和墓葬實物相印證。馬家窯類型的青海陽洼坡遺址出土了3700多件陶環裝飾品,連珠狀是其中主要形制之一;在青海宗日遺址發現了6099粒骨珠,骨珠一般串系成項鏈、胸飾、腕飾。珠子對人體的裝飾有一定的文化意義,被賦予了神性。半山與馬廠類型時期存在著靈魂和祖先崇拜的習俗,在師趙村遺址發現的人像彩陶罐和臉部五官鑲嵌“骨珠”的石雕人面像。考古推測這些人像和人面像可能是作為信仰的偶像或巫師的靈物而被隨葬的。[6]彩陶上連珠紋的裝飾有可能是來源于祭祀儀式和人體裝飾的生活觀察的藝術再現。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彩陶上的連珠紋可能在長期的發展中從單純的裝飾,逐漸通過和其他紋樣的組合獲得了攜帶“太陽”神性的意義,在馬廠時期進入繁榮階段,后面在過渡到青銅時代的過程中,紋樣逐漸弱化直到消失。“凡是有太陽照耀的地方,均有太陽崇拜存在。”[7]太陽崇拜是史前文明社會里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甘青地區的先民也是一個盛行太陽崇拜的民族,其圓形的器物和遺跡有極大的可能是對連珠紋意義的最好詮釋;興盛的彩陶藝術,無疑成為他們表達太陽崇拜心理的最佳方法和途徑。連珠紋本身也因制作簡易、紋樣構成形式形象、容易被人接受而成為太陽的化身。連珠紋在陶器裝飾上逐漸減弱的原因可能是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青銅器替代了陶器承擔了祭祀儀式的功能,連珠紋也隨之轉移到新的物質媒介上,因為連珠紋也是青銅器裝飾的典型紋樣之一。連珠紋這個紋樣本身很簡單,是圓圈或者圓點連續發展的紋樣,理解它的文化意義需要考略時代的語境和它所依托的圖像結構關系。連珠紋的研究不應該脫離整體圖像的語境和圖式關系而去簡單解讀。彩陶圓圈紋,除了太陽、太陽神崇拜的文化表征,也是佩戴珠石裝飾鏈的視覺呈現。“連珠紋”的中文詞義,“連珠”詞義是指連起來的、有關聯的圓球狀珠串,連珠紋是表現串聯在一起的珠串裝飾紋樣。據此,可以將彩陶“圓圈紋”認為是中文語境下的“連珠紋”的原型,是古代中國甘青地區連珠紋的起源,連珠紋從早期階段就已經攜帶了明確的文化意義。
二、青銅制品上的連珠紋裝飾
燦爛的彩陶文化衰退后,隨著青銅冶煉技術的進步,中華文明進入了青銅時代,銅鏡和青銅容器成為這個時期的典型物質代表,連珠紋也作為典型紋樣出現在銅鏡和青銅容器的裝飾上,以及金銀器上。
(一)青銅境的連珠紋裝飾
早期銅鏡一直作為梳妝用具,兼作配飾,曾經也是宗教法器和等級地位的象征。目前考古所見,最早的連珠紋裝飾銅鏡應該是中原地區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單鈕鏡[8],連珠紋出現在銅鏡的邊緣位置,鏡緣二圈弦紋環間有51個小乳釘形成珠環,正圓布局的連珠紋環立體化的裝飾在圓形銅鏡的邊緣,增加了裝飾的層次感。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青銅鏡在兩個圓環間裝飾有一個大的十字形紋,就是兩個圓環中間區域做十字形分割并填充紋樣的裝飾布局。青海、甘肅等地出土的大量馬廠類型陶罐的鼓腹上都裝飾有這種十字布局的圓形紋樣。這表明,中原地區早期幾何紋飾青銅鏡上的十字形紋飾布局特征可能是對甘青地區彩陶紋樣裝飾傳統的借鑒。[9]另外,婦好墓青銅鏡的主體紋樣是葉脈紋,與甘青地區齊家文化時期青海貴南尕馬臺出土的七角星紋鏡和甘肅臨夏出土的重圈多角星紋銅鏡紋樣形式接近,都是用陽刻的直線段填充表現肌理,裝飾工藝相似,但是甘青地區的青銅鏡沒有裝飾連珠紋。
從時間上看,婦好墓出土的連珠紋青銅鏡年代要比甘青地區的青銅鏡要晚,三者存在裝飾特征的相似性。而甘青地區的青銅鏡鮮少見到連珠紋裝飾,并沒有繼承該地區彩陶紋樣的裝飾傳統;另外,彩陶的連珠紋雖然攜帶了一定的文化意義,但是從未作為主體紋飾使用,對外傳播的影響力很有限。因此,中國中原地區青銅鏡的連珠紋裝飾應該本土文化發展的結果,或者是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鈕式銅鏡在亞歐大陸多處文明地區使用,各個文明之間有可能存在交流傳播的途徑。西周時期的銅鏡出土不多,均為圓形,由于其中多為沒有紋樣裝飾的素鏡,對其象征意義無從探討。戰國時期,裝飾連珠紋的銅鏡漸多,在菱紋鏡、獸面紋鏡、純底紋鏡上均可見到,但裝飾部位不定,主紋區、分區帶上均可見。漢代銅鏡鑄造繼承戰國遺風,以連珠裝飾成為鮮明特征之一,基本出現在主紋區或鏡鈕的周圍。
(二)青銅器的連珠紋裝飾
青銅器上的連珠紋是管狀器制作的,形成一個一個小圓圈排列的規則裝飾,是青銅器的早期的紋飾之一。青銅器上的連珠紋可能是直接繼承陶器的幾何紋樣而來,后來由晉代的青瓷繼承了青銅器的連珠紋裝飾傳統。青銅器上連珠紋的表現形式由青銅鑄造工藝決定,普遍看來,比陶器上的連珠紋要規整和細密。連珠紋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持續流行到西周中后期[10]。關于青銅容器連珠紋裝飾意義,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連珠紋象征的是“玄鳥”的祖先崇拜[11],商代常見的連珠紋是表現尚族對玄鳥崇拜的抽象紋飾。《史記》記載,商人祖先‘簡狄’吞食了玄鳥卵而懷孕生下了商人的祖先‘契’。方鼎主要作為祭祀的禮器使用,多用于祭祀祖先,用圓形表現玄鳥卵既形象又容易呈現。因此,用連珠紋表示玄鳥卵,并裝飾在方鼎上,可能是用來表示使商人祖先的母親簡狄懷孕的玄鳥卵,以此表達對祖先的崇拜。另一種觀點是連珠紋形式來源于鱷魚皮膚肌理[12]。研究者通過連珠紋形式與鱷魚角質麟形態的對比,認為青銅器上的連珠紋裝飾是工匠觀察鱷魚頭頸部上的棱嵴之后,在青銅器紋飾上的藝術再現。而在青銅期饕餮紋的下面另外增加的連珠紋帶飾,可能是設計者從紋飾的整體感覺出發,對于構圖上的平衡感和形式美感的考慮,在后續的圖案中特意添加上去的。商代早期,隨著饕餮紋在青銅器上作為主體紋飾使用,連珠紋隨后轉變為輔助紋飾。河南省中牟縣黃店鄉出土的青銅爵[13]的腹部,饕餮紋的上緣有一排連珠紋與之相伴,而在商早期二里崗上層的失目饕餮紋的上緣,同樣也配有一排連珠紋。“饕餮紋+連珠紋”的組合樣式從商早期一直延續到商晚期,在青銅器上大量使用,形成了鮮明強烈的時代風格。裝飾有連珠紋的青銅器多見于中國的河南、陜西、湖北等地。
三、中國中西部地區早期連珠紋所蘊含的文化意義
綜上所述,連珠紋在中國起源于馬家窯文化時期。太陽的崇拜,引發了尚圓觀念的形成。中國古人很早就有著尚圓的觀念,在他們的認識中,天是岡形的。道教《定經》中寫道“天地之形,其狀如卵。六合之內,其岡如越。出沒,運行天之,一地之下。上東西,周行如輪。”人們對岡初步的了解來源對太陽的崇拜和對天體的識知。由多個圓形構成的連珠紋自然成為了中國文化的視覺傳達選擇。連珠紋的形式以圓形骨架為主,后續隨著紋樣填充的多變而拓展形式,形成相對穩定的藝術規范。早期的連珠紋單元有間隔,并沒有緊密相接,但是,俯視角度下的彩陶和青銅器上連珠紋形態特征十分明顯,后期的連珠紋很有可能就是從這里汲取靈感,或是直接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連珠紋裝飾藝術的發展具有程式化的特征,不論連珠紋是單獨使用,還是組合出現,這些反復出現的紋樣都體現出圖式化、格律化、規范化的程式特征。連珠紋的程式化發展既包含形式上的格式規范,也包含具有特定表現內容的藝術樣式本身。在裝飾藝術中,每一種紋樣的圖式都經歷了一個由初創的幼稚、模糊、不確定,到逐步成熟、清晰和模式化的過程。[14]彩陶和青銅鏡的連珠紋發展就是經歷了這樣的階段。這一過程顯示了與觀念形態相對應的藝術圖式的同步發展過程。紋樣的程式一旦作為模式確立下來,它便不僅成為濃縮著某種觀念意義的象征符號,同時也為后人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形式規范和藝術樣式。
中國文化語境下的連珠紋意義多元,從身體裝飾、太陽崇拜,變成祖先崇拜、動物神力的加持,隨著時代的變化不斷更新定位和內涵。中國式樣連珠紋的早期發展呈現出自主意識強烈和適應性強的文化面貌特征,極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