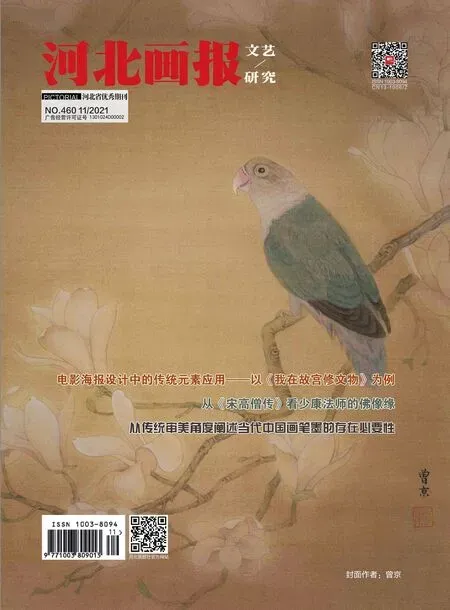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野下托馬斯·哈代的《還鄉》
王孟維
吉林大學外國語學院
托馬斯·哈代是19世紀英國最杰出的鄉土小說家和詩人,以他的“威塞克斯”小說聞名于世。他生動形象地描繪了英國的鄉村風光,再現了鄉村的風俗,他的作品著眼于描寫西方的工業化文明對鄉村淳樸風俗的“入侵”。本文將采用生態批評的視角,對哈代的小說《還鄉》進行分析,以期挖掘出作品中蘊含的生態思想,了解其具備的批判意義。
一、生態批評理論以及哈代生態思想的來源
生態批評的“生態”首先是指一種思想觀念——生態主義的思想觀念,其核心是生態整體主義;其次是指一種美學觀念——生態美學的觀念。
謝里爾·格洛特費爾蒂將生態批評定義為“生態批評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的研究。”我國的生態學專家魯樞元立足于傳統文化,在西方生態學的基礎上進行了研究和創新,提出具有比喻意義的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他從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三個層面對生態進行了解讀,為讀者呈現了一個更加立體和全面的生態系統。他認為:“自然生態體現為人與物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生態體現為人與他人的關系;精神生態體現為人與他自己的關系。”哈代的生態思想主要是在他的個人經歷以及英國文學傳統的影響下產生的。英國工業革命讓英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但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底層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們的生存環境也遭到工業化的污染。同時,人們的精神世界也悄然發生了變化,人們紛紛追逐蠅頭小利,淡漠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威塞克斯往日如同田園牧歌一樣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哈代痛感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希望改善人與生態之間的關系,通過描寫美好的鄉村風物來試圖重建人類精神家園。英國文學中有許多關于自然的名篇,詩人們親近自然,歌頌自然,從自然中得到創作的靈感。哈代經常閱讀著名詩人華茲華斯的詩歌作品,在華茲華斯的作品中有回歸自然的意愿和對破壞自然行為的指責。哈代和華茲華斯一樣有一種親近自然的氣質,這可能和他的鄉村生活經歷有關。哈代在小說中也隱隱地表露了他的生態思想,他認為人們應該尊重和敬畏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維持生態平衡。
二、荒原——命運的操縱者
《還鄉》中充斥著對埃格敦荒原的景觀的描寫,小說的開頭就是對荒原的描寫“十一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已近黃昏,埃格敦荒原這片尚未圈地的廣袤原野上,天色隨著一分一秒過去暗下去了。頭頂一片灰白色的寶蓋云,將天空遮住,便成了帳篷頂,于是整個荒原便成了地鋪。”哈代認為,人不能脫離自然,唯有與自然和諧相處才能實現人自身的價值。人們對待大自然的態度也影響著他們最終的命運。在《還鄉》這部作品中,荒原就像一個智者一樣默默守護著一切,從荒原對克林和游苔莎的不同態度和他們的不同結局中,我們可以看出哈代的良苦用心:人類必須尊重和熱愛自然,不能疏遠自然。這很好地表現了哈代的生態主義思想。
克林是小說中“荒原回歸者”的典型形象。哈代認為,人類只有回歸自然,才能感受到心靈的平靜,在自然中人類的心靈能夠得到治愈。哈代的小說里也有很多人物做出了從離開自然到回歸自然的選擇,他們從自己生存的小地方離開,到大城市闖蕩,希望有所成就,卻被城市的空虛和世俗所困擾,最終選擇逃離繁華都市,回歸自然。克林就是其中的一員。克林的童年和荒原是密不可分的,“任何看到荒原的人,十有八九會想到他”荒原就像養育了他的母親,對于他來說有獨特的意義,每次他失意的時候,都可以通過俯視荒原來得到安慰。他在母親約布賴特太太的精心培養和熱切期望下接受了教育,經人介紹去蓓蕾嘴做生意,然后又去了倫敦,最后去了巴黎,在一個珠寶店當了經理。他的母親很為他驕傲,覺得自己的兒子既然在大城市找到了如此體面的工作,就跟這些在荒原上生活的人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克林在繁華的巴黎卻感覺非常壓抑空虛,至于自己的工作,他認為“這是一件男人所從事的最無聊、最虛榮、女性化的工作”,讓他感到精神不振。因此,他選擇了回歸荒原,想在靠近埃格敦荒原的地方建一所學校,在他母親家在辦一所夜校,從而造福家鄉。最終時間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他最終在荒原收獲了新的人生。克林這個人物投射了哈代的個人愿望,反映了哈代對自然生活的熱愛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呼吁。
游苔莎是本書中荒原逃離者的典型形象。游苔莎出生于時髦的海濱勝地蓓蕾嘴,相貌出眾,我們可以從哈代對她的描述中看出“游苔莎·維爾本是做天神的料,稍稍打點一下,就能在奧林匹斯山上混的很好”“腦后一彎新月,頭上戴著一頂舊盔,散落的露珠系在她的前額上,像一頂王冠,這些飾物在她身上足以讓她分別展現出阿耳忒彌斯、雅典娜、赫拉三位女神的美麗,她和古典天神的相似度,不遜于許多尊貴的油畫里那些栩栩如生的女神。”這樣一個完美的女神在小時候便見過了大城市的輝煌,卻不幸在小的時候父母雙亡,于是隨著她的外公“老艦長”在埃格敦荒原上定居。盡管身在荒原,她的心卻從未屬于這里,她從來沒有領略荒原微妙的美,能感受到的就只有荒原上的縹緲云霧。她對荒原里的一切都感到厭惡,期盼著自己有一天能離開這里,她認為是荒原把她禁錮住了,阻礙她擁抱外面的世界。她的美貌又讓她覺得荒原上無人能及,她傲視一切,眼空四海,因而愈發冷漠,忽視了荒原人的善意,像一個行尸走肉一樣生活,希望一覺醒來就能回到之前的城市生活。
荒原的生活是寂寞空虛的,為了填補這種寂寞,懷爾狄夫被游苔莎理想化,與懷爾狄夫的交往成為她無聊生活中的消遣。懷爾狄夫曾經一度讓她看到回歸城市的希望,這時候,從巴黎榮歸故里的克林出現了,他的出現立刻取代了懷爾狄夫在游苔莎心里的位置,因為游苔莎相信克林一定能帶她到巴黎生活,到時候她也會成為巴黎的闊太太,享受紙醉金迷的生活。她甚至在見到克林之前就對他產生了感情,之后她設計接近這位巴黎歸客,拼命地想引起他的主意,最終夢想成真,兩人終于成婚了。但是與其說游苔莎愛克林,不如說她愛的是他背后繁華的大城市,她把她的愛情當作去巴黎的手段。婚后游苔莎就幻想她丈夫能帶她回巴黎,沉醉在對未來生活的幻想中,幻想著:著“有朝一日,她能成為某幢漂亮住宅的女主人,……捕捉到從大城市飄來的些許快樂氣息,她可是太適于享受這一切了。”結果克林卻不愿再回到繁華都市,鐵了心要繼續他的“教育事業”,每天努力看書。之后克林由于讀書過于用功幾乎雙目失明,這讓游苔莎不得不放棄幻想,讓她心如死灰。這時她的昔日情人懷爾狄夫在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后又來誘惑她,游苔莎的心里又產生了希望。他們密謀私奔,終于在一個暴雨如注的夜晚雙雙出逃。狂風暴雨暗示了這次出逃的悲慘結局,游苔莎和懷爾狄夫雙雙喪命。在死去之前,游苔莎高聲地呻吟道:“走得了嗎?走得了嗎?......就算走得了,我又有什么寬慰呢?明年還得挨下去,和今年一樣勉強,后年又照舊。我多想成為出色的女子啊,可命運老是跟我作對啊!.......我陷入如此糟糕的世界真是太殘酷了!我可以做許多事,就是一些我完全無法掌控的事情把我傷害了,破壞了,擊倒了!”由此可見,盡管游苔莎一生都計劃著從荒原逃離,荒原還是深深地融入了她的血脈,成為了她的經歷和性格的一部分。她窮其一生也無法真正地離開荒原,因此她離開荒原的嘗試以失敗而告終。
游苔莎和克林的不同結局讓我們知道,人和自然是共生共存的,任何背棄自然的行為都會帶來悲劇性的結局。不同的態度和選擇映照出不同的生活和命運,自然總是在冥冥和無形中警示著人類的命運和未來,游苔莎和克林對荒原的親疏選擇以及各自的命運結局便是最好的驗證。這一切都表明了人類只有親近自然,才能收獲平靜的內心,哈代借此表達了對構建生態和諧的社會的向往。
三、荒原美景——生態整體觀
在《還鄉》中,哈代以生動的筆觸描寫了荒原的美景,贊美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以文章第一章對荒原的描寫為例:“文明是它永遠的冤家對頭;自從植被出現以后,它的表面就已經被這件舊的棕色衣服所覆蓋;這是一種從未更換過的天然服裝,它只有一件古早的衣服,這諷刺了人們在服飾方面的虛榮心。一個人穿著有著時髦的顏色和樣式的衣服,來到荒原總顯著有些格格不入。因為大地只有這樣古老的服裝,我們似乎也得穿著極簡單極古老的衣服才顯合適。”荒原是個能自我調節的生態系統,它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文明是它的死敵。工業革命盡管沖擊著鄉村生活,荒原卻一直沒有變化,歷經世事變遷,滄海桑田,千百年來一直等待在這里。荒原的廣袤無垠更加襯托出人類的渺小,反映了宇宙的博大。
除了荒原的自然風光,本書中還有很多對動植物的生動描寫,表明了哈代對萬物的敬畏,構成了一幅生機盎然的生命之景。以哈代描寫石楠花為例,“它們是干枯的灰色石楠花,夏天里盛開,本來花瓣柔軟,呈紫色,現在叫米迦勒節的寒雨沖刷得失色,又讓十月的太陽曬成死皮了。花兒個體發出的聲音非常低微,所以成百上千合起來的聲音,剛剛能脫穎而出。”他對石楠花的刻畫細致入微,讓人有種畫面感。哈代是這樣描寫“綠頭鴨”的:“維恩面前就有一只綠頭鴨——剛從朔方的故鄉來到。這飛禽攜帶了有關北方的大量知識......但這只小鳥看著紅土販時,看上去像一個哲學家,似乎在想,當下的良辰美景,相當于過去十年的回憶。”生態整體觀強調包括各種生物在內的生態系統的總體利益才是最高價值標準,而不僅僅是把人類這一單一物種的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生態整體觀試圖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傳統思想觀念,從而建立一種人與自然平等友好的主體間性關系。哈代深受生態整體觀思想的影響,與自然和諧共生,因此他很擅長自然風光的描寫,尤其在刻畫動植物的時候能做到栩栩如生。
四、“自然之子”——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思想
哈代意識到了工業革命對人類精神家園和人們之間友愛關系的破壞,試圖在自己作品中保存鄉村的田園詩般的風貌,風俗習慣等。在《還鄉》這部作品中,哈代運用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和豐富的生活經驗,為我們描繪了壯美的埃格敦荒原和一群世世代代生活在荒原的自然人。
哈代在《還鄉》中塑造了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在這里人們世世代代安居樂業,遠離塵囂,在荒原上做工為生,他們自己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哈代描繪自然人時,把他們當成一種景物來進行描寫:“周圍一群人的臉和衣服上晃著明亮的光線和木炭陰影,丟勒般的力量和氣勢繪制了他們的臉和身體輪廓。 但是,我們不可能發現每個人臉上難以改變的精神狀況,因為活躍的火焰總是在上下跳躍,在周圍的空氣中四處游蕩,在人們的臉上涂上陰影色塊和光線 ,這些色塊和光線變形不斷移動。所有的一切都在變動,就像樹葉在風中顫抖,像閃電一樣閃爍。”這些人和荒原融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構成了一幅和諧的生存圖景。
紅土販維恩也是這些“自然之子”中的一員,他最初經營著一家奶牛場,向托馬辛求婚遭到了拒絕之后,決定成為一名紅土販,從此漂泊不定,四海為家。 他全身上下都被紅土染成了紅色,表明他與自然已經融為一體,不分彼此。書中描述了他如何在荒原上偽裝自己:“紅土販趴在地上,拖過兩塊泥炭,一個覆蓋頭和肩膀,一個覆蓋脊背和雙腿。這樣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也很難看到他;泥炭長著石楠的一面朝上,粘在紅土販的身體上,看起來就像它是在地面上生長的一樣”。這反映了他已與自然和諧交融。
五、結語
哈代生于鄉村,長于鄉村,也老死于鄉村,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的主要時光都是在多塞特鄉間度過的,也算是“自然之子”中的一員。因此,他經常在小說中描寫鄉間的一草一木,風序良俗,在他作品中有很強的生態思想。他認為,人類和大自然息息相關,大自然是一種神秘力量,能對人的命運產生影響,它會在游苔莎這種蔑視自然的人面臨災禍時“袖手旁觀”,也會讓親近它的“自然之子”維恩和克林等安居樂業,得到一個美好的結局。因此,人類只有尊重和敬畏自然,才能在這個世界上詩意地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