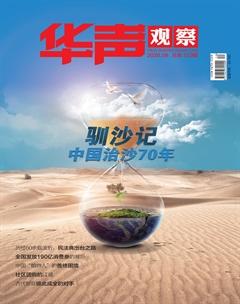社區團購的江湖
徐倩影

社區團購在各大小區興起
“雞塊快秒,上次63元,今天49元,我才看到其他小區搶了1000多份。”
“無籽紅提可拼單12元,2斤起拼,需要拼的親,發私包給我,備注就好了,明天到貨。”
“大家一直要求的單個榴蓮11:00限量加團,明天配送,價格低至94.8元/個,限量加團,手慢必無。
每天,彭弼臣和妻子姜英在“中海康城團購群”發布至少20件產品的分享鏈接,他們管理著4個微信群,共計1700多人。
這4個微信群涵蓋了廣州中海康城花園小區的“吃貨”“烘焙族”和“羊毛黨”。對彭弼臣這種“老團長”來說,他已不再看重拼群的活躍度,而更關注線下商品與小區居民之間的真實黏性。
如今,大部分客戶與團長之間建立了“小程序頭天下單、第二天自提貨品”的默契。團長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定時推薦好物、剔除發小廣告的臥底。
上午11點,兩輛小型貨車載著有150個品類的上千件商品抵達小區。根據前一天的訂單情況,彭弼臣將蔬菜、水果、凍品、日用百貨等商品進行分揀,方便業主取貨。
受疫情影響,2020年,幾乎每個小區業主手里都有數十個團購群,原本作為家庭消費補充渠道的社區團購,現已成為日常消費的常規渠道。
社區團購正在中國城市的各大小區興起。
需要“軟化”商品的推廣文案
彭弼臣認為,一個群其實并不是“人越多越好”每次有新業主人群,他都會看看是不是來自認識的業主的推薦。同時,他還需提防那些在群里發無關內容的人。
除了提防無關內容,彭弼臣還需“軟化”商品的推廣文案。“小程序上如今有上百種產品,但商業文案太生硬,我得轉化成正常的對話形式,然后推薦我試用后覺得好的產品。只要在我這‘拿過貨的業主,我都能記住他們的名字。”
兩年前,只要有100來位好友,就可以做團長,彭弼臣當時把多少年不聯系的同學都加到群里,也才90多人,勉強做了團長。由于團長的保護機制,他必須搬家,重新找一個適合發展社區團購的小區。他搬到中海康城花園,當時這里有6個團購平臺,競爭壓力不小。
當時平臺每天只有8件產品,雖然價廉物美,但品類有限,“前三個月基本沒賺到錢,還要承擔6000元房租”。
彭弼臣記得,有次他在一天之內賣了120箱阿克蘇蘋果,分揀時被業主們看到了,他們覺得蘋果好,通過相互推薦,群里增加了200多人。到了第四個月,月營業額終于超過10萬元。
一般而言,團長可以拿到銷售額的10%作為提成。根據十薈團2019年的全年收人統計,彭弼臣獲得年終銷售大獎,以及年終大促活動凈營業額50萬元以上類第一名,公司獎勵了他一輛價值10萬元的車。
一年前,開水果撈連鎖店的睿哥開始做社群營銷,他通過發優惠券集合了十多個群。疫情期間,他的實體店全部關門,于是他索性做起了線上水果生意。
當別人都說沒生意時,睿哥告訴朋友珂珂,“你來我群里賣東西”。
“你能拿到的進貨價格,其實很多人都能拿到。”珂珂經營小吃店十多年,認識很多生鮮類的上游供應商。2020年3月,他在群里賣雞蛋,有朋友告訴他,同小區的團長和他賣同一個廠家的產品,價格低15元,而這意味著業主對珂珂的信任度會下降。
“當時我就慌了,潛入對方的群里觀察,
發現人家賣的確實和我的產品一樣,而且屬于同一個供應商。所以要不眼睜睜看著客戶被搶走,要不就收編它。”
珂珂選擇了后者,他決定和對方談一談。畢竟在實體店沒有恢復正常前,社區團購還是很好的銷售增量方式。
“有35%的利潤空間”
“社區團購絕對賺錢,晚上發完產品,早上起來就有幾千塊的收人。”珂珂做了一個月社區團購后,想搭建平臺,他開始琢磨找朋友開發小程序,以此尋找更多貨源渠道,收編各個小區的散團長,打通當地的物流體系。
隨著電商下沉市場的布局,在甘肅白銀市平川區做蔬菜批發生意的張立軍也看到了社區團購的紅利。
“從了解模式到決定搭建平臺,我總共用了5天。”他在行業公眾號里找平臺談加盟,一個小程序花費1.98萬元,如果協助開店又要花好幾萬元。
“疫情前,一個月最多20單;疫情期間,每天訂單都上百了,有時晚上12點我都在給客戶送菜。
據張立軍介紹,疫情期間的蔬菜批發利潤極低,但社區團購不一樣,“有35%的利潤空間,除去物流費用,一天凈賺2000多元”。
2019年末,張立軍陸續在縣城的幾個小區門口開了蔬菜零售店,但都因為收人不理想關門了。他打算在疫情后擴大社區團購,增加生鮮和水果的售賣,于是買進保鮮柜、儲存庫、冷凍柜,組建了一個分揀配送中心。他和朋友前后共投,人20萬元,目前看來,回報率還不如做實體批發。
平川最近開了一家更專業的生鮮團購店,也讓張立軍慌了起來。他認為,“過于山寨”的小程序限制了自己的團購發展。
2018年,長沙某社區團購平臺一天之內銷售了2萬包速凍水餃。這個數字是當年商店、超市平均日銷量的20倍,對于大部分廠家和供應商來說,確實足夠誘人。
作為凍品的一級供應商,劉娜娜所在的平臺有價格優勢,物流也可以自己配送。“但當我招募了25個團長,每天為送貨耗費大量物流成本、為引流提高成本促銷時,卻發現團長并不上心,這也導致凍品損耗非常大,銷量也并不高。
做了一年社區團購后,劉娜娜發現自己在“白忙活”。她花大成本爭取來的流量最終無法轉化,即使后臺有上萬個用戶數據又能做什么呢?
在她看來,供應商無法做平臺的原因,在于搭建平臺需要上游供應商支持,“我了解海鮮行業,但并不懂水果和蔬菜行業,純粹通過單品,你很難提高獲客率”
既然沒有盈利,社區團購的價格為什么如此之低?“除了大平臺融資貼補之外,熟悉這個行業的人都知道,有些小平臺通過電商銷售臨期貨。我們通常只看到產品的銷售量,卻從來看不到平臺的退貨率。有部分產品因為退貨成本太高,顧客會放棄退貨。目前,社區團購還沒有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劉娜娜說。
摘編自《新周刊》20204年5月8日文中睿哥、珂珂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