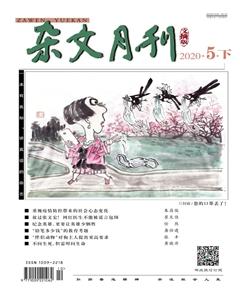范滂有母終須養
陳鵬舉
先前讀《宋史·蘇軾傳》,讀到一個名叫“范滂”的古人,第一眼就被“滂”字吸引了。感覺“滂”字單獨出現很好看,比“滂沱”之類更有古意。趕緊想了解范滂這人。就去看了《后漢書·范滂傳》。
范滂官階不高,風骨出眾,有“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曾被太尉黃瓊征召。黃瓊是當時名人,“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么好的句子,就出自著名的李固《遺黃瓊書》中,至今膾炙人口。當時,范滂調查有關官吏行狀的歌謠,彈劾了二十多個刺史和享有二千石俸祿的權貴。
延熹九年,范滂獲罪“黨人”結黨,被押黃門北寺獄。中常侍王甫奉旨過堂。范滂一行頸、手、腳戴枷鎖,布袋蒙頭,排列階下。范滂越序前行,面對王甫責問,坦蕩陳詞。最后他說,古人求善道能求得多福,今人求善道竟然身陷死罪。我死后請埋首陽山下。王甫聽了很哀傷,當場解除了階下所有囚犯的枷鎖。
三年后,朝廷決意捕殺范滂。督郵吳導到了范滂鄉里,在驛舍抱著詔書,閉門伏床大哭。范滂聞訊說,他一定是因為我。隨即去自首。縣令郭揖寧愿棄官,和他一起逃亡。范滂說,我死了,事情就了了,不敢連累你,還讓我老母親流離外鄉。
《范滂傳》接下來的最后一段文字,讓范滂和《范滂傳》不朽:“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家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意思說,范滂母親和他訣別。他對母親說,弟弟孝敬,會供養你。我隨父親命歸黃泉。生死各得其所。還望母親割舍難舍的恩情,不要再悲傷了。母親說,你今天能和李膺、杜密齊名,死也無憾。有了好名聲,再求長壽,這兩者可以兼得嗎?范滂下跪受教,拜別母親。回頭對他兒子說,我想要你為惡吧,惡實在是不可為;要你為善吧,我不為惡,竟是這般下場。邊上的人聽了,無不流淚。這一年,范滂三十三歲。
《宋史·蘇軾傳》是開篇就提到《范滂傳》的: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蘇軾才10歲,母親就教他讀《范滂傳》。他問母親:如果他是范滂,母親允許嗎?他母親說:如你是范滂,我難道就不能是范滂的母親嗎?
在我印象里,蘇軾在意兩個人:陶淵明和范滂,一個是真的歸去來兮——隱居了,一個是那樣壯烈地赴死了,都是懷抱澄清的人。蘇軾一生效仿的大概也就這兩人。只是這兩人現世中的行狀區別太大,蘇軾想合一為之,很難。事實上,蘇軾一生使勁的就是這合一為之的努力。他鍥而不舍。也就這點,他有了人緣。當初和如今的許多人,都和他有相似的努力,所以和他投緣。
再回到范滂。范滂對兒子說的話,該是他的人生遺言。前一句,人不可為惡,說出了人之為人的底線和尊嚴。后一句,為善竟沒好下場,說出了世間的無情和悲涼。
蘇曼殊有首詩,也提到范滂。《束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云雷亦歸漢土,感成此絕》:“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伶豈是歸。萬里征程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蘇曼殊在詩中依著歸省的思緒,提到了人子得其所的問題。詩中除了范滂,還提到范滂同代人張儉。張儉名聲也好。他被追捕,到處逃亡,見有人家就躲進去。人家都會收留他,甚至愿為他遭難。所謂“望門投止”,說的就是張儉。蘇曼殊說,即使是望門投止的張儉,也是不得其所。而范滂,作為人子,母親終是要贍養的。范滂有母終須養,說出了范滂有母難養的徹骨悲涼。蘇曼殊這首詩,字面上是說范滂,還有張儉,其實也是說他自己。他是詩僧,也只三十幾歲的壽命,飄搖家國,悲歡莫名。
有母終須養,說起來、做起來都平常不過。范滂有母終須養,竟是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