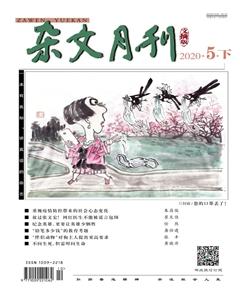茶客留言

愿“敢言”不再是“一種高貴的品格”
王海銀(山西太原)
讀了《敢言,是一種高貴的品格》(《雜文月刊》2020年3月下),我深深為張笑春醫生敢說敢當的精神所感動。要不是她公開質疑用核酸檢測確診新冠肺炎的可靠性,建議用CT影像作為診斷主要依據,數以萬記的新冠肺炎患者仍然會被當成疑似病例在家中隔離,得不到有效的治療和嚴格的隔離,我們與新冠病毒的戰斗,恐怕不會取得今天的成果。
但同時,也感覺有點心酸。說真話本應是人最基本的品格,而如今竟然成了一種高貴的品格!這應該能夠說明,目下在個別地方,還容不得真話,說真話還要冒一定的風險。雖然也有許多說真話者安然無恙,有些甚至受到了賞識和重用,但這都是因為有幸遇到了大度、開明的領導。
常有人說,對待不同的聲音,包括錯誤的、偏激的聲音應該予以包容。此話聽起來似乎很正確很好聽,仔細推敲就會發現,這種所謂的包容,實際上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恩賜。說真話,表達個人觀點,是公民的一項最基本的權利。因此,最理想的輿論環境,是我說了真話,表達了某種觀點,觸犯了某些人的利益,這些人對我恨之入骨,但卻拿我毫無辦法!我的意思是,從根本上講,表達自由的保障,要靠法律,而不能靠他人的大度和開明。
也應防止雜文泛化
梁勤學(山西運城)
近一兩年,因事連向《雜文月刊》“茶客留言”和“三人行”中試寫點文字也都未能顧上了。
已是《雜文月刊》18年的老必訂老必讀老學生,也沒少讀雜文寫作本身的作品。去年12月底外出,身帶本月《雜文月刊》,讀感甚多。然看文摘版《茶客留言》中郭明進老師的《傳播正能量也是雜文的任務之一》,也還感到關于雜文的議題還在路上。10下期曾刊莫小米老師的《的士司機說:做夜班我盡量送她們回家》,寫了關乎人的安全的小故事,余也感動,堪為正面入手傳播正能量的好文章。鑒此郭老師提出:“雜文應把動人的故事傳播,而且要把它作為主要任務之一……時代變化了,雜文的寫法和功能也應變化。”余未敢盡同,試與郭老師商榷。
“茶客留言”是作者和讀者的交流園地,編輯老師一般不表意見。本期50余篇文章,如《“知識就是力量”,無需靠財富證明》《奢靡現象為何詔令難禁》《警惕“偽民俗”》《詩還是城市的心跳嗎?》等等,絕大多數只看題目就可想而知。余對《政府通告錯20處,反思不能止于個案》也有同感。當年12月余在某地某村兩委門口前,見了一條并無前言后語聯系的紅布標語:“天上掉餡餅,地上有陷井。”雖非出自政府,也屬業務單位,負面作用恕不能用文字表達了。《不能有一片樹葉,管理潔癖要不得》《煙火氣:城市的活力與生機》,說的問題不少地方存在。葡萄牙、西班牙余都去過,這么發達和注重生態的國家,也沒搞成“地面上看不見一片樹葉”。馬德里地鐵已經比較落后,并沒有實行高度現代化的改造;太陽門街上依然有著接著地氣的“煙火氣”的“烏煙瘴氣”。《由朱大典而想到的》《清代官員郭璓的“蛻變”》,從人性到心理學上詮釋了某些官員由惡變善的說怪不怪。《堅實的桃核》是對“樸實”大媽騙人引出的思考。李國文老師的《肉食者鄙》,寫史也絕非“發思古之幽情”。也寫司馬遷正能量,實際是對唯古人唯名人阿附作風的尖銳批判。如此等等,進一步研讀《名家新作》游宇明老師三篇力作,余自信自己所持的觀點不錯,如游老師所說:“雜文的職能是批判(也含批評)。”郭老師的提議很好,但所說的寫法主要應是報告文學,表揚稿,先進材料等文的事了。
近年來也鑒于雜文難做,有人提出了實行雜文轉型或多樣化,但是有的也是隨意把什么文章都當成雜文了。我是這樣認為,不管雜文怎樣改革怎樣變化,雜文總歸是雜文,應有雜文氣雜文味雜文職。雜文主要應是通過批判批評假丑惡來維護發展正能量,不能搞成雜文泛化……
誰消磨了
讀書人的骨氣?
吳蘭友(山東聊城)
《雜文月刊》2020年3月下轉載了《中國青年報》上的一篇文章《讀書人為何丟了書卷氣?》,讀后感慨良多。讀書人丟了書卷氣本夠讓人失望的,但其實那還是小事,因為丟了書卷氣僅是丟了讀書人應有的氣質,更讓人擔憂的是很多讀書人丟了骨氣,這可是讀書人的根本。
暫不說我們能看到身邊有幾個有錚錚鐵骨的讀書人,即便為了正義為了維護社會底線勇于抗爭的人也少見了,倒是一些人與不良社會行為沆瀣一氣,做的很多事不以為恥甚至反以為榮,最典型的是一些所謂讀書人為了職稱論文,粗制濫造花錢發表還是小事,有的人不惜抄襲他人成果、數據弄虛作假等,這哪里還有讀書人的樣子?最近西南一大學的某教授,著名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一方面發表國家對嫖宿幼女罪處罰過輕的文章,一方面涉嫌強奸幼女,且可能存在知法犯法嫌疑,這樣的讀書人更是讀書人的恥辱。
讀書人應是什么樣子?至少應有為了社會正義不惜犧牲自我的正氣,至少有不為五斗米折腰敢于抵制不良風氣的勇氣。但誰消磨了讀書人的骨氣?再以讀書人很看重的職稱看,很多人每年要發表若干論文,也就是成果,歸其根源與一年一度的考核有關。然而,就思想創新、科學發明等領域,其成果能以年來評判嗎?不要說彪炳千古的思想家、科學家,他們一生多僅以一兩本書、幾項發明立身,即便近百年來每年都評出若干的諾貝爾獎,獲獎者也多靠一兩項獨創的理論獲獎。
終其一生,沉下心來,安心讀書,靜心思考,努力鉆研,不為今年要出什么成果,或明年要發表什么論文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