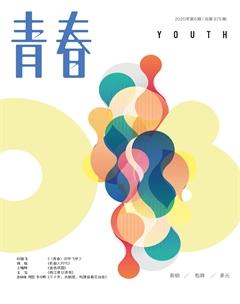我最初的寫作
沈喬生
題目寫下了,卻不知道該如何界定,我初中二年級時寫大字報也能算寫作嗎?如果不算寫作又能算什么呢?
事實很清楚,當時出身黑色家庭的都要造老子老娘的反。要命的是,就像數(shù)學函數(shù)會變一樣,這個也會變,今天說是黑五類,明天卻說是黑七類了,范圍擴大了,讓人茫然不知所適。不過,話說回來,凡是家庭出身帶黑的,不管是五類、七類、九類,哪個敢不識相?
哥哥們從大學回來,召集底下的弟弟妹妹,低聲商量,看來這一關(guān)逃不過了,樣子總要做的。不過,你要做樣子,傷心的一定是父母。但有什么法子呢?雖然是父子、母子關(guān)系,但造反形勢在那擺著,只好大難臨頭各自飛了。
盡管外面的形勢一片紅火,但我們還是有點像做賊。幸好父母都沒有回來,我們恢復了活力,嘁嘁促促,像一伙快樂的小蟑螂。因為我小時候是學毛筆的,所以由我執(zhí)筆。怎么寫呢?哥哥說,不能不寫,也不能寫得太嚴重。眾兄弟姐妹都覺得對,于是你一句他一句,有的說,父親看不起勞動人民;有的說,從小向我們灌輸剝削階級思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有的說,“灌輸”好像太嚴重了,是不是改成“宣揚”?“宣揚”也蠻嚴重的,改成“散布”吧。
現(xiàn)在想來有點奇怪,大家一邊說,一邊嘻嘻哈哈,好像是在做游戲,搞幽默,其實是在減輕心里的負擔。
我握一支毛筆,也不動腦筋,大家講一句,我寫一句。心里反而在琢磨毛筆字,8歲開始學書法時,母親讓我學柳公權(quán),我卻喜歡上了顏真卿。我一邊寫一邊想,現(xiàn)在寫的字像顏呢,還是像柳?
大字報寫好了,二版《人民日報》那樣大,貼在后門上。剛貼出去就有人圍過來看,叫起來,快看,這家人貼他們老頭子的大字報!
我們飛一樣逃回來,關(guān)緊后門,再也不敢出去。
父親回來了,他看見了,臉色凝重,腮幫一邊鼓起,像牙齒痛一樣。母親也看見了,不響。
等到“文革”的烈焰小了許多,一次在飯桌上,父親放下筷子,說,自然災害辰光,我和你們媽媽天天想著要給你們吃好,你們在長身體,吃得不好要虧一生的。你們媽媽一直跑到七寶去,問農(nóng)民買高價肉、高價魚給你們吃,誰想到腦子吃壞了!
我們面面相覷,沒有一人說話。
三年后,我下鄉(xiāng)到了農(nóng)場,黑龍江有漫長的冬天,沒有事情可做。好多人打牌、下軍棋。我偶然玩玩,大部分時間用在寫作上。放一只箱子在炕上,盤起雙腿,成一只龍蝦的姿勢,就可以寫了。
不知哪里來的熱情,一口氣寫下《雪原揚鞭》《開渠新歌》等作品,也不知道算不算小說,當時三突出的作品就是這么寫的,我不過是依樣畫葫蘆。身邊的朋友看了,驚奇了,咦,這個人還會寫小說,于是就拿了去看,還蠻好看,寫的是農(nóng)場里的事,我們上海知青是主角。我探親時還帶回上海去,給兒時的伙伴看。伙伴看了,噢,你在黑龍江是這樣的。天真冷,吐一口痰,到地上就是冰。還有不少勞改犯,發(fā)配到那里去了。就這樣慢慢傳開了,好多人都知道,七星泡農(nóng)場十一分場有個寫小說的上海人。
說來也是奇怪的,舞文弄墨有風險,不是不曉得,我耳朵都聽出老繭來了。前面那么多寫文章的人被打倒,上吊、跳樓、投湖,不是看不到。我怎么還像著了魔一樣去寫?而且沒有一分錢的稿費。只能說,出鬼了!
接下來的變化是我沒有料到的,大概是農(nóng)場宣傳科頭頭看到我的小說了,粗粗一讀,不錯。于是,一紙調(diào)令過來,調(diào)我到宣傳科工作。我大吃一驚,又有說不出的欣喜。從此,我脫離苦海,不用參加大地勞動了,也算開始了職業(yè)寫作,開始了我逍遙自在的一生。誰說寫小說沒有好處,這個好處夠大了。
不過,我還是不明白,七星泡農(nóng)場是個大農(nóng)場,前前后后來了近2萬名知青,哈爾濱、上海、天津,老高中多得很,家庭出身好的多得很,會寫的人也一定不少。偏偏頭頭看了我的小說,也不管我出身資產(chǎn)階級,就能發(fā)出一紙調(diào)令?這真是稀奇。看來,我的頭頭那時思想已經(jīng)夠解放了。
不過,我又是一個驕傲的人。我這人筆頭子特別快,往往總場開一個有線廣播大會,我就握一支筆在邊上,他這里會議剛開完,我那邊報道文章也已完成,立刻送往廣播站。
宣傳科還有幾個筆桿子,但他們寫文章的速度無法跟我比,我這個特點很快被人發(fā)現(xiàn)了,就有人吹捧我。一次吃酒,有人當場說我是作家。
我卻搖頭,說,寫這狗屁文章就能算作家?這作家也太好當了。你抓一條狗來,把筆綁在它爪子里,放一根肉骨頭在邊上,它也會寫作。現(xiàn)成的套路,在“批林批孔”運動的推動下,在場黨委和各分場黨總支的領導下,廣大農(nóng)場職工戰(zhàn)天斗地……過兩年,只要改一句話,用“反擊右傾翻案風”替代“批林批孔”,沒有一點問題。我記得,聽的人都翻白眼。
等到酒醒來,我仔細一想,極度恐懼。我說了什么混賬話,要是被人告發(fā)了,這輩子不就交代了!
我連忙去找一起喝酒的人,偷看他們神色,還好,似乎沒有異樣,我慢慢把喉嚨口的話咽回去。三天過去了,沒有人去揭發(fā),那桌人都厚道。我安然無恙。
人都是不滿足的,寫通訊稿算什么,太容易了。我的志向是寫小說。當時全國只有一家文學刊物——《朝霞》,是我的老家上海辦的,實質(zhì)是“四人幫”掌管。一次,有個知青告訴我,劉征泰是她的鄰居,劉的爸爸和她的爸爸都是上海科學院的專家,是同事。
我聽了又驚又喜,那時劉征泰寫了《英王陳玉成》,如日中天。我看過,十分佩服。我忙說,能不能把我的小說送他看看?她說,可以啊。于是,我的小說就通過這條渠道送給了劉征泰。
前幾次都不成,后來有一篇,劉說還可以,送到《朝霞》去了。我就有點興奮,過了一些日子,又告訴我,留用了。我更加興奮了,心里就想,什么時候能登出來呢?誰知道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四人幫”粉碎,《朝霞》停刊。我知道泡湯了,當時是手寫的,也沒有留底稿,也無處去尋,就當作廢了。雖然是個打擊,但“四人幫”粉碎了,是個大好事。
不知過了多久,一天,忽然有個老先生敲我家的門。他姓范,長得慈目善眉,說了原委。“文革”結(jié)束了。重新成立上海美術(shù)出版社,一時間哪有稿子,老范幾個只好到被封門的《朝霞》去找,翻了幾只麻袋,就翻到我的稿子。前后一看,寫得不錯,最重要的是沒有斗“走資派”,寫的是倉庫保管員和盜竊分子作斗爭,這沒有問題,正等米下鍋,要我馬上改編成連環(huán)畫。
我悲喜交加,這稿子大難不死,劫后復生。幸虧我當時回上海探親,要不然他也找不到我。我馬上行動,連夜改起來。范先生告訴我一個道理,叫大餅和花卷,大餅的芝麻是撒在面子上的,而花卷的蔥花是卷在里面的。連環(huán)畫就是要做花卷。畢竟不是很難,很快就改好了。那天范先生看過稿子,在我肩上拍一下說,大功告成!
等我考進大學,到華東師大報到,連環(huán)畫《長青松》剛好出版。第一版印30萬冊,不過當時都這樣的。
大學二年級時,1980年,我寫了中篇小說《月亮圓了》。寫兩個年輕人,少年時是好朋友,“文革”來了,一個出身資本家,受到歧視;另一個的父親是干部,變成了走資派,也受到?jīng)_擊。兩個人由此成了敵人,一起到了黑龍江,偏偏分到一個分場,到了草原上,就兩個人在一起,放牛放羊。這里有點我的生活影子。兩人之間沒有語言,你喜歡那頭小母牛,另一個就把它打得遍體鱗傷。另一個人喜愛一只鳥,我就把它連籠子一齊塞進火爐里。草原上的月亮似乎從來沒有圓過,彎彎尖尖的,像秤鉤鉤住了人的心。后來,來了一個女孩子,叫小茜,她可愛,善良,用真情和友愛化解了他們之間的敵意。在嚴酷的斗爭之后,月亮圓了,它皎潔的光輝寧靜地照耀著草原、森林、河流……
寫完了,我交給班上的同學郟宗培,他是我的福星,幾十年來都如此。前后關(guān)照過此篇小說的有江曾培、邢慶祥、張森、謝泉銘、左泥、章惠琴等編輯前輩。因為當時的小說并不多,所以我這個年輕人就有這份幸運。
不過,過程比較折騰。當時上海文藝社沒有刊物,就讓我改成長篇小說,出單行本。原來小說只有5萬多字,要拉長到10多萬字,可是,前半部只有兩個人物,后半部加上小茜,也只有三個人,場景始終在草原上,難度不小。我只得挖空心思,亂搔頭皮。改來改去,終于有13萬字了,一讀,自己都覺得水分太多。就這時,《小說界》創(chuàng)刊了,可以拿到刊物上去發(fā)表,又讓我縮短,改成6萬多字,發(fā)在創(chuàng)刊的第二期上。
那時我讀了許多詩,所以這篇小說富有詩意,也挺優(yōu)美的,受到許多青年讀者的喜愛,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但是,我心里總有不平。當時文壇上都是抨擊“文革”,揭露殘酷的迫害,而我的小說卻寫了敵對方之間的諒解和寬容,大部分中國人還想不到這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是正常的。
兩年后,我寫了第二部中篇小說《苦澀的收獲》,寫當時高考恢復后的大學生,這部小說挺寫實的,有我自己的深切體會。
沒想到題目出問題了,看三審的人說,收獲怎么能“苦澀的”呢?苦澀兩個字,有點陰暗。當時大概是反擊什么風,三審的總編就十分謹慎。編輯跑來告訴我,我叫苦不迭,把“苦澀的”三個字拿掉,就變成了收獲,這有點不像樣,而且跟那家老牌刊物重名了,也不好。
幾個回合下來,編輯就對我實話實說,看來不行,名字不改,有可能小說通不過了。
我想想算了,不過是個名字,登出來最要緊。收獲就收獲,我們不苦澀了。
第二年,《小說界》評首屆作品獎,通知我,說我的《收獲》得獎了。我又驚又喜,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得文學獎。以前也算得過獎,是在農(nóng)場,當上勞動模范,得到一朵紙折的大紅花。
我那時已到南京工作,去上海領獎才知道,原來候選篇目中沒有我的《收獲》。但是評委看下來,對候選作品均不滿意。這時,評委之一、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中杰先生說,他的女兒也在復旦讀書,她看了刊物上的《收獲》,覺得好,她的很多同學也看了,也都覺得好。他的女兒就推薦給爸爸看,吳中杰先生看了,也覺得很不錯。聽他這一講,會議主持人叫人把這部小說找出來,給每個評委兩小時,當場看,當場發(fā)表意見。居然都覺得好。
就這樣,我的《收獲》因了復旦一個女生的關(guān)系,僥幸獲獎。那屆中篇獎就兩個,另一個就是日后寫出《白鹿原》的陜西作家陳忠實。幾天接觸,他的樸實、誠懇,和對寫作的專注,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那次,我們一起坐了游輪,暢游黃浦江,風和日麗,極目遠眺,江上百船競發(fā)。一起暢游的有鄧友梅、李國文、魯彥周、陳忠實、陳村、汪浙成等作家,還有江曾培、郟宗培、邢慶祥、魏心宏等編輯同仁。
后來出小說集子,我又把題目改回來了,還是苦澀好。苦澀的收獲。人生能有多少事,不帶一點苦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