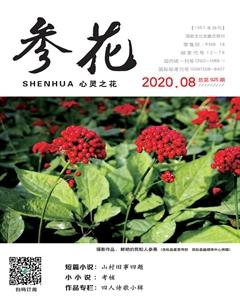英美新批評視域下的師陀小說《父與子》
摘要:《父與子》是現代作家師陀于20世紀30年代創作的一篇出色的短篇諷刺小說。在英美新批評視域下,該作品在三個層面上充分展現了文本自身獨特的文學與藝術魅力:主人公的預想與情節發展背道而馳構成的反諷,既使人物特征更為鮮明,又不斷突破了讀者的期待視野;父子沖突及其相對性關系對“新”“舊”沖突及其相對性關系的象征,通過對父子沖突無法調和并呈現出循環發展趨向的暗示,給讀者帶來了悲劇性的情感體驗;小說由情節構造出的種種矛盾在人物塑造中得到了統一,并形成了文本上的結構張力。
關鍵詞:英美新批評 師陀 《父與子》 反諷象征
師陀,即蘆焚,20世紀30年代初期步入文壇,后因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谷》獲得《大公報》文藝獎而受到文壇廣泛關注。盡管在創作之初就因鄉土小說而成名,但除鄉土小說外,師陀在30年代也創作了部分優秀的諷刺小說,而《父與子》正是他于該時期創作的短篇佳作。
這篇小說主要通過一個中學教員45篇篇幅短小的日記記錄了主人公自1917年到1937年間的生活變化。作家巧妙地通過這些日記生動地呈現了兩代人的父子沖突,這種父子沖突敘事又與此前傳統的父子沖突敘事有所不同,在文本中的反諷、象征和張力中,凸顯出作品本身獨特的藝術與文學魅力。
一、主人公的預想與情節發展背道而馳構成的反諷
“反諷”一詞源于古希臘文Eironeia,最早出現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是指一種表明實際意義與字面意義對立的修辭手段。英美新批評又將這一修辭廣泛運用到文學批評中。在師陀小說《父與子》中,它主要體現在主人公預想與情節發展背道而馳所構成的反諷。
《父與子》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他年輕時懷揣著理想投身教育事業并無心仕途,可隨著時間的流轉與生活的壓力,他開始對此熱心。在校長這一職位空缺后,更是一心想接任校長職務。他自以為無論資望還是學識,眾人皆不如自己,“這把椅子大約八分坐牢了”。校長的職位被他人占去,他就又自我安慰“不必著急,教員總還當著”,那人也只是代理,“總將實授于某也未可知”,最后他的愿望卻終是落空,他更為此而懊惱不已,譴責這時代妒賢嫉能。甚至在此事過后許久,校長再度撤換,他依舊因自己未能任職而耿耿于懷,在日記中悲憤罵道:“媽的,某只配一世做驢。”主人公對自己的未來不斷地進行美好設想,又經歷了不斷地落空,這正達到了一種反諷,也將主人公這一“官迷”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此外,小說主人公對自己的長子從不關心,卻想著“究竟父子情義,骨子里是有的,他將分擔一部分責任也未可知”。他氣脈不濟時,期待著長子也許會想些辦法。可事實上,他不過是自作多情,他的長子在信中稱他為“先生”,更從未想過承擔贍養他的責任,甚至在信中咒罵他“日子已經不多,請放心啐幾口唾沫罷”。他在需要長子時總惦念著他,可在長子入獄后,卻毫不猶豫地與其斷絕父子關系以避免自己遭牽連。無論是主人公希望謀得校長職務的落空,還是他希望長子能承擔起贍養責任的落空,顯然都呈現出一種反諷意味。總體來說,這種反諷手法的不斷運用既突破了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形成的期待視野,同樣也是作者自身一種非凡的敘事策略的體現。
二、對“新”“舊”沖突及其相對性關系的象征
象征是一種語言的修辭格,在新批評語言研究中,象征這一修辭也成了一大研究要素。
《父與子》中所涉及的象征,主要體現在文本中父子沖突及其相對性關系對“新”“舊”沖突及其相對性關系的象征。
這篇小說通過45篇篇幅短小的日記記錄了主人公20年來主要的人生經歷,也記錄了兩代人的父子沖突。小說的主人公年輕時是受過新式教育的“五四”青年,他因不滿被父親包辦婚姻而遠離父親追求自由戀愛,并堅持認為“新式小家庭總是不錯的”。他不滿父權而主張父子平等,與父親的沖突十分激烈,甚至在日記中直接斥責父親為“封建余孽”。
在一個家族中,父與子的身份總是具有相對性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主人公的身份也因此具有了多重性。他在父親的兒子這單一身份上,又添加了父親的角色。他作為父親,與自己的兒子也一直沖突不斷:他在日記中斥責小兒子是“流氓”;他從不關心長子的教養,卻希望已成年的長子能承擔起家庭責任,為自己分憂解難,使自己安享晚年。他與自己的父親一樣,也只是將兒子作為自己的所有物而企圖加以控制。
小說卻顯然不只體現出父子沖突本身,這種沖突背后實際上也潛在地象征著“新”與“舊”的沖突。正如文本中的父子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父輩的舊思想對子輩新思想的抵觸。作者又通過兩代父子的沖突來表明“新”與“舊”的沖突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甚至具有持續性。
此外,正如父子關系是相對的,文本中呈現出的“新”“舊”關系也是相對的。小說中的主人公,與自己的父親相比,年輕時的他作為典型的“五四”青年自然象征著“新”,但隨著時間的變遷,他也成了“父親”,亦不再是當年那個懷有新思想并關心新思想的青年,與自己的兒子相比,他顯然又成了“舊”的象征。
因此,作家實際上通過父子沖突的呈現進行了一種具有哲學意味的關于“新”與“舊”的象征,這種象征同樣又暗示出文本中的父子沖突如同宿命般無法調和并呈現出一種循環的發展趨向,并由此給讀者帶來了具有悲劇性的情感體驗。
三、由情節節奏推動產生的文本結構張力
英美新批評家艾倫·退特提出了張力的概念,此概念取自于英文詞內涵與外延,意謂緊張關系。《父與子》整篇小說在情節安排上充滿波折與沖突,呈現出一種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具體由情節節奏所推動,并由此體現出一種文本上的結構張力。
小說的開篇就呈現出主人公對同學進入政界的不解與不滿,他對同學的職業選擇感到詫異,更視政界如“污水缸”,而這正體現出主人公與外界的一種思想沖突。這種沖突隨著情節的推動而不斷加劇:他創作的新劇被反對上演,與校內同事的關系緊張甚至因此被校長約談,與自己新婚的妻子也因家庭瑣事開始發生矛盾,與此同時,他又因支付鄉下妻兒的贍養費與父親產生沖突。在讀者已然形成期待視野后,卻發現,主人公隨著時間的推移,已逐漸被普遍的社會思想所同化。他開始熱心仕途,對新劇與新思想卻不再關心。鄉下的父親去世后,他亦不再支付鄉下妻兒的贍養費。就在主人公好似已與外界達成和解之后,他卻又與子女的沖突不斷,他反對女兒出演新劇,在懷有新思想的長子被捕后與其斷絕父子關系。隨著整個情節的推動,主人公的形象在讀者眼中發生變化。主人公與外部的矛盾此起彼伏,前后的矛盾又形成一種對照,可這種種矛盾最后又統一于對于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使得人物形象飽滿而又立體。
因此,文本中由情節構造出了種種矛盾,而這些矛盾在文本的前后形成對照,又在主人公的塑造上得到了統一,從而形成了一種文本結構上的張力,而這種張力又顯然被小說的情節節奏所推動。
夏志清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曾對師陀的這篇《父與子》作出較高的評價,稱其為“出色的諷刺作品”。而我們在對此類優秀作品進行考察時,實際上不僅要挖掘其內在的思想內涵,更應當注重對其藝術形式與藝術效果進行一定程度的探討。本文在英美新批評視域下,對師陀的這篇《父與子》從反諷、象征、張力三個維度,試圖進行有益的探索,也是對于文本本位原則的一種有益的堅持。
參考文獻:
[1]劉增杰.師陀全集[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2]劉增杰.師陀研究資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5]楊義.中國小說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唐旭,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延邊大學,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