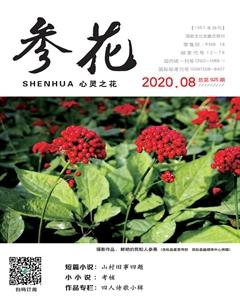黃自藝術歌曲歸鄉情結初探
摘要:黃自的藝術歌曲是我國聲樂藝術中一筆寶貴的財富,其中的歸鄉情結更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亙古不變的情懷。本文試圖通過對藝術歌曲《思鄉》歌詞內涵、旋律特征、和聲織體的分析來闡述“歸鄉情結”在黃自藝術歌曲中的體現,從而為更深刻全面地理解黃自的音樂作品奠定基礎。
關鍵詞:黃自 藝術歌曲 歸鄉情結 《思鄉》
黃自(1904—1938),字今吾,我國近現代音樂的奠基人,在作曲、音樂理論、音樂教育和音樂社會活動各方面都為我國音樂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其音樂創作領域涵蓋豐富的題材,包括管弦樂作品、弦樂四重奏、賦格曲、創意曲、大型聲樂套曲、藝術歌曲和其他類型歌曲。黃自率先將歐美音樂體裁形式和作曲技法與我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在音樂理論和音樂教育方面,黃自更是不遺余力地推動了我國近代音樂事業的發展。
一、黃自藝術歌曲創作概況
現今普遍對藝術歌曲的定義是集音樂、詩歌和鋼琴伴奏三位一體的具有較高藝術性的歌曲形式。在黃自的所有音樂作品中,各種類型的歌曲數量居多,而嚴格意義上的藝術歌曲所占比重較少,只有10首,同時對后世作曲家的歌曲創作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這些都是后世學者研究黃自音樂的密切關注點。
黃自的10首藝術歌曲分別為:《思鄉》(韋瀚章詞,1932年),《春思曲》(韋瀚章詞,1932年),《玫瑰三愿》(龍七詞,1932年),《花非花》([唐]白居易詞,1933年),《雨后西湖》(韋瀚章詞,1933年),《下江陵》([唐]李白詞,1933年),《點絳唇·賦登樓》([宋]王灼詞,1934年),《燕語》(韋瀚章詞,1935年),《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蘇軾詞,1935年),《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宋]辛棄疾詞,1935年)。這10首藝術歌曲的歌詞來源于我國唐宋詩人的經典詩詞或韋翰章、龍七(龍榆生)的詩作,風格精致哀婉,和聲語匯清晰規整,體現了古典文學和西歐作曲技法的高度融合。韋瀚章是我國近代提出“歌詞”這一名稱的第一人,他主張當時所寫的詞應采用舊詩詞的長處和造句格律方式,同時在內容上又要具備現代的思想、題材和語匯,因此便產生了區別于古代詩詞和現代詩歌的“歌詞”。
二、黃自藝術歌曲中歸鄉情結的體現
“歸鄉”一詞,在狹義上即為對自己故鄉的眷戀和向往,在廣義上可以理解為精神家園和心靈棲息地的構建。“家”是人生活的中心載體,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層面,人終其一生都在循著“家”的蹤跡前行,“歸鄉”是回家,更是靈魂的回歸。
按照創作時間順序,將黃自藝術歌曲歌詞中的歸鄉元素做一梳理。《思鄉》分為兩段,第一部分引用《西廂記》的名句“一聲聲道:‘不如歸去!”和末尾“我愿與他同去”形成呼應與對照,都是思鄉情感的直接寫照。《春思曲》中“恨只恨,不化成杜宇,喚他快整歸鞭”,思郎心切,只恨自己不能化作啼鳴“不如歸去”的杜鵑,催促丈夫即刻啟程歸鄉。《玫瑰三愿》雖不是直接表現了歸鄉情愫,但其精神內涵可延伸為追尋安寧的心靈棲息之地,渴求內心的慰藉,這亦是終極的歸鄉情結影射。白居易經典詞作《花非花》以“春夢”和“朝云”比喻往事的不可回首,一切有如夢幻泡影,想抓住卻是無形的悵惘,一“來”一“去”皆在“無覓處”的瞬間,是想要有所寄托和對往事、故人的留戀,也是精神內在歸鄉情結的體現。《燕語》借燕子的口吻表達了對家的永恒依戀,“我但愿共春同住;我但愿主人無故,我便從頭筑起新巢,哪怕辛辛苦苦”,只要主人無恙無故,便不懼怕千辛萬苦,心靈依托的精神家園便是歸鄉情結的主旨。
三、藝術歌曲《思鄉》的歸鄉情結分析
《思鄉》結構為A+B二段曲式,降E大調,意境唯美動人,詩詞、曲調與和聲織體一氣呵成,是許多歌唱家音樂會的保留曲目。
(一)歌詞的歸鄉元素體現
1932年清明過后,離開家鄉珠海七年,久居上海的韋瀚章在暮春景色的映襯下對故鄉的思念之情愈加濃烈,寫下詩句:“柳絲系綠,清明才過了,獨自個憑欄無語。更那堪墻外鵑啼,一聲聲道:‘不如歸去!惹起了萬種閑情,滿懷別緒。問落花:‘隨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我愿與他同去!”
歌詞形式與宋詞結構相似,并引經據典,以《西廂記》中的“一聲聲道:‘不如歸去!”道出從古至今游子的歸鄉情結,是畫龍點睛之妙筆。上片寫出時間地點和人物環境,當詩人面對春色想起家鄉的親人,只能在院中獨自倚靠欄桿無語相對,卻怎想又有墻外的杜鵑,這叫聲像及了“不如歸去”。“問落花隨渺渺煙波”一句的“問”與《點絳唇·賦登樓》中“問春無語”的“問”如出一轍,而“煙波”也同時是《點絳唇·賦登樓》中“山無數,煙波無數”的寫照,可見韋瀚章對宋詞的喜愛與推敲。“是否向南流”,正是朝著詩人韋瀚章家鄉的方向,歌詞下片層層推進,直至“愿與他同去”的歸鄉情愫感嘆。
(二)旋律對歸鄉情結的描繪
《思鄉》全曲是柔和婉約的旋律特征,為自然流暢的行板速度,其中的弱起節奏形式、變化音運用以及半音級進是旋律進行中的顯著特點,也為思鄉之情引起的歸鄉情結做了很好的詮釋。
1.弱起節奏形式
A段每一樂句都在四四拍的第三拍后半拍上進入,只有“一聲聲道”的對應旋律是三連音的節奏,并從強節奏位置上展開,其后“不如歸去”也從弱拍開始,并且幾乎每一樂節均為帶休止的節奏。這樣的節奏節拍形式是作曲家內心憂愁情緒的表達,也與之后舒展流動的旋律形成對比。三小節間奏之后,B段的旋律也以第三拍后半拍開始,“滿懷別緒”是第二拍上的弱起。直到全曲旋律最高音的“問”字,才沒有了弱起,是強拍上情緒飽滿的爆發,隨即又是下行的旋律伴隨漸弱的力度表情,似流水漸行漸遠,亦似對故鄉的想念幻為若隱若現的內心寄托。
2.變化音與半音級進
旋律從升F音開始,第一個音便是調式主音上方增二度,是優柔迂回旋律走向的基礎。緊跟其后的還原E,與調式主音形成更緊密的小二度,在下一句“獨自個”中完成變化音的不穩定性向調式主音的過渡,回到降E音,然后是更流暢清新的旋律展開。
B段由主音上方大三度的全音和半音級進開始:G—A—降B—升C—D。“萬種閑情”處還原A與主音形成增四度關系,刻畫出離愁別緒的苦澀與艱辛,再到“滿懷別緒”一句的增六度向調式導音的級進,層層遞進,情緒在一陣陣推波助瀾般的旋律行進下以四度小跳又到達主音上方大三度G。這一系列的級進前后,以完滿的純八度在G音上展開對思鄉感懷的高度抒發,歸鄉情結由此達到頂點。
(三)鋼琴和聲織體對歸鄉情結的詮釋
鋼琴聲部的和聲行進以分解和弦為主,像春日流水,也像作曲家心中不斷涌動的歸鄉思潮。一開始便用了導向大調Ⅲ級和弦的升Ⅱ級音,隨后是導向大調Ⅱ級和弦的升Ⅰ級音,屬于離調式模進的手法。間奏部分用大三度以八度重復的方式形象地模仿了杜鵑的啼鳴,一強一弱的對比充滿生動的趣味,之后又是分解和弦,以漸慢漸弱的處理引出一連串的柱式和弦:以Ⅲ級上的三和弦變化為Ⅲ級上的七和弦,再到導七和弦、Ⅱ級七和弦,和聲織體加厚加強,力度也隨之漸強起來,營造出歸鄉心切的“萬種閑情”和“滿懷別緒”,最后停留在屬和弦上形成Ⅱ級七和弦到屬音三和弦的解決。在“問落花”處回到主和弦,又以流動的分解和弦平穩進行至曲終。
藝術歌曲《思鄉》中歌詞、旋律與鋼琴和聲織體統一地體現出“歸鄉”這一主旨,具有濃厚的歸鄉情結,為近代藝術歌曲中的典范之作。
參考文獻:
[1]周培源.黃自遺作集·聲樂作品分冊[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2]金婷婷.世變中的藝術歌曲——論黃自音樂美學[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0(01):62-70.
[3]劉再生.憑詞寄意 柔情似水——近代詞作名家韋瀚章[J].中國音樂教育,2014(02):48-50.
(作者簡介:張娜,女,碩士研究生,天水師范學院,研究方向:藝術學理論)(責任編輯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