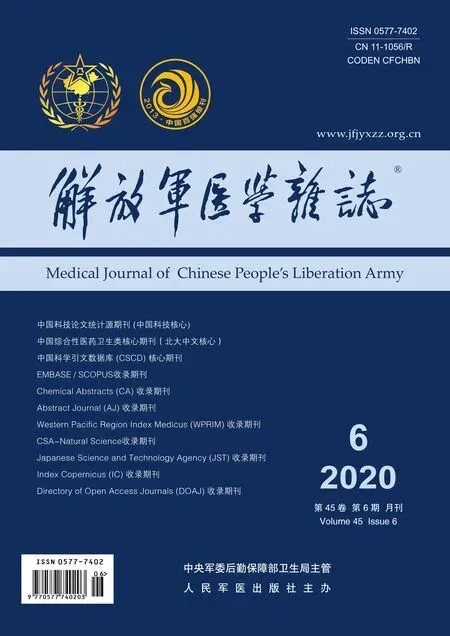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患者房性心律失常與V1導聯P波終末電勢及左心房直徑的相關性
曾曉杰,溫華知,朱紅紅,謝萍,謝宇平
1甘肅中醫藥大學臨床醫學院,蘭州 730000;2甘肅省人民醫院心內科,蘭州 730000;3甘肅省人民醫院鼾病科,蘭州 730000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是誘發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AF)的危險因素[1]。AF為一種常見的心律失常,占發達國家人口的1%~2%,且發病率隨人口老齡化明顯增高[2]。由于OSAS和AF是臨床常見疾病,二者關系密切,嚴重影響人類的健康且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因此,早期識別OSAS患者AF的發生并揭示其具體機制,對于OSAS患者AF的治療具有重要意義。慢性OSAS可誘導永久性心房重構,為AF的發展創造了基礎。既往研究發現,OSAS的嚴重程度與左心房(left atrial,LA)的異常心電信號有關,表現為高V1導聯P波終末電勢(P-wave terminal force V1,PTFV1)[3]。本研究主要探討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情況,并分析其與PTFV1及左心房直徑(left atrial diameter,LAD)的相關性。
1 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收集2017年9月-2019年4月在甘肅省人民醫院鼾病科初次住院的257例OSAS患者的臨床資料,排除數據缺失的病例,共納入247例,其中男197例,女50例,年齡18~76(48.3±11.8)歲。OSAS的診斷標準為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會睡眠呼吸疾病組制定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診治指南(基層版)》[4]。納入標準:①年齡≥18歲;②12導聯心電圖診斷為竇性心律;③有睡眠監測報告、動態心電圖及心臟彩超檢查結果。排除標準:①睡眠監測當天服用影響睡眠監測的藥物及飲料,如酒精、咖啡、濃茶,服用鎮靜安眠藥、中樞興奮類藥物及抗心律失常藥物等;②其他睡眠障礙性疾病如中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發作性睡病等;③有嚴重基礎心臟病如心力衰竭、風濕性瓣膜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冠心病、心肌病;④伴有嚴重神經系統疾病如腦卒中、癲癇、癡呆、腦炎、腦外傷等;⑤伴有嚴重肺部疾病如支氣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感染、肺間質性疾病等;⑥合并內分泌疾病如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多囊卵巢綜合征、肢端肥大癥、腺垂體功能減退癥、原發性醛固酮增多癥等;⑦伴有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嚴重電解質紊亂;⑧長期嚴重酗酒;⑨接受氧療。根據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apnea hypopnea index,AHI)將患者分為對照組(AHI<5,n=22例)和OSAS組(AHI≥5,n=225例),然后再將OSAS組再分為3組:5≤AHI<15為輕度OSAS組(n=37例);15≤AHI<30為中度OSAS組(n=46例);AHI≥30為重度OSAS組(n=142例)。本研究經甘肅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編號:2020-116)。
1.2分析指標 ①多導睡眠監測(polysomnography,PSG)檢查:入院2 d內完成PSG檢查,夜間持續監測時間≥7 h。所得結果通過電腦自動分析和專業技術人員判讀。監測當晚測量受試者的身高、體重等基本指標,并計算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BMI=體重/身高2(kg/m2)。②24 h動態心電圖監測:所有納入病例均采用世紀今科(MIC-12H-3型)12導聯全信息實時心電記錄儀進行動態心電圖監測,連續記錄24 h動態心電圖,分析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情況,包括房性早搏、房性心動過速、陣發性AF。③超聲心動圖檢查:由經驗豐富的超聲醫師使用荷蘭飛利浦(S5-1)心超儀進行測量。取二維超聲心動圖胸骨旁左心室長軸切面測量左心房直徑(LAD)。④心電圖檢查:患者取平臥位,在靜息狀態下描記常規12導心電圖(25 mm/s,10 mm/mV)。心電圖要求V1導聯基線平穩無干擾,P波清晰。根據Morris等[5]的理論,本研究將PTFV1定義為:常規體表12導聯描記,以竇性心律為前提,當V1導聯P波呈直立狀態時,PTFV1記為0;P波呈正負雙相時,負向P波的時限乘以終末負向P波振幅,以絕對值計算(單位:mm·s)。如圖1。

圖1 PTFV1的測量方法Fig.1 Measurement method of PTFV1
1.3研究方法 收集所有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吸煙史,飲酒史,高血壓、糖尿病、外周血管疾病史,以及PSG指標、動態心電圖指標、PTFV1、LAD等,觀察OSAS患者的性別、年齡、個人史及疾病史特征,分析OSAS的危險因素。觀察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及其與PTFV1、LAD的相關性,探討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機制。
1.4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4.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進一步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數據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的比較采用χ2檢驗。相關分析中,計量資料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計數資料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各組基線資料比較 與對照組相比,輕度OSAS組、中度OSAS組、重度OSAS組性別、AHI、高血壓比例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與女性相比,男性OSAS的患病率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相比,中度OSAS組、重度OSAS組夜間最低血氧值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相比,中度OSAS組年齡、重度OSAS組BMI等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他各項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表1)。

表1 各組OSAS患者基本資料比較Tab.1 Comparison of basic data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2.2房性心律失常發生情況比較 與對照組(0%)相比,OSAS組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率(18.7%,42/225)明顯升高(Fisher's確切概率法,P<0.05);與對照組相比,輕度OSAS組(16.2%,6/37)、中度OSAS組(23.9%,11/46)、重度OSAS組(17.6%,25/142)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率均升高(χ2=3.92,P<0.05;χ2=4.93,P<0.05;χ2=3.94,P<0.05)。輕、中、重度OSAS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2.3相關性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PTFV1與夜間最低血氧飽和度呈負相關(r=-0.173,P<0.01),與AHI、年齡、BMI均呈正相關(r=0.131,P<0.05;r=0.153,P<0.05;r=0.172,P<0.01);在控制上述變量后,PTFV1仍與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呈正相關(r=0.394,P<0.01)。此外,LAD與夜間最低血氧飽和度呈負相關(r=-0.142,P<0.05),與AHI、BMI呈正相關(r=0.355,P<0.01;r=0.177,P<0.01);在控制上述變量后,LAD仍與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呈正相關(r=0.235,P<0.01)。
3 討 論
OSAS是臨床常見病,以間歇性缺氧、二氧化碳潴留、反復微覺醒及睡眠結構紊亂為主要特征[6], 由其引起的一系列機械、血流動力學、化學、神經及炎癥反應均會對心血管系統造成不利后果。年齡、男性、肥胖、高血壓為OSAS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7-8]。
隨著年齡的增長,OSAS的發生風險亦增高,可能是因與年齡相關的慢波睡眠(即深度睡眠)減少所致,而慢波睡眠對睡眠呼吸紊亂及氣道塌陷有保護作用[9]。但在本研究中,中度OSAS組的年齡較對照組更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輕度、重度OSAS組未表現出此差異,可能的原因是對照組病例數較少,未包含各個年齡段。
在肺容積匹配的情況下,與女性相比,男性的氣道直徑長、咽部長度增加,且可折疊氣道增多,這些差異使男性患OSAS的風險大于女性[10]。此外,絕經后接受激素替代治療的婦女OSAS患病風險降低,這表明雌激素的喪失會增加OSAS的患病風險[11]。由于雌激素在呼吸控制系統多個部位的作用,更年期雌激素水平下降對呼吸穩態構成威脅,包括對上氣道穩定性的挑戰[11],再加上衰老本身對上氣道力學的有害影響,圍絕經期時雌激素對肌肉氧化還原穩態的保護作用喪失可能會增加女性上呼吸道肌肉功能障礙的風險,這可能會抵消女性在控制氣道直徑方面的優勢[10,12]。本研究發現,與對照組相比,輕、中、重度OSAS組男性的構成比均明顯增高。
OSAS風險增加與BMI、腰臀比及頸圍增加相關[13]。Pillar等[14]發現,肥胖與OSAS之間相互促進:肥胖會增加OSAS的風險,但另一方面,OSAS也會使體重增加。肥胖可導致上呼吸道結構變窄、呼吸功能受損及激素變化。與OSAS有關的碎片化,睡眠可能導致饑餓及食欲增加[15]。碎片化睡眠減弱了下丘腦中的瘦素信號通路,導致胃饑餓素分泌增多,瘦素分泌減少[16],從而導致食欲不受控制,食物攝入過多則導致了體重增加及肥胖。另外,碎片化睡眠可誘導內質網應激并激活下丘腦的未折疊蛋白反應,從而破壞能量平衡,最終導致體重增加[15-16]。此外,肥胖易引起OSAS的原因還包括:全身脂肪組織增多時,氣道脂肪組織也增多,導致氣道變狹窄;上氣道的通氣功能降低,肺活量降低[17]。與上述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也發現,BMI隨著OSAS的嚴重程度增加而增高。
OSAS與高血壓有許多相同的危險因素,如肥胖、性別(男性)及年齡的增長[18],因此OSAS與系統性高血壓之間有明顯的重疊[19],提高對OSAS的認識及早期診斷對減輕心血管疾病負擔至關重要。OSAS的上氣道塌陷致間歇性缺氧,使交感神經輸出及內皮素系統過度激活,進一步使腎上腺素能張力升高,最后導致高血壓[20]。本研究中,高血壓的發生隨著OSAS的嚴重程度增加而增多,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7]。
OSAS如果長期未得到有效治療,就會導致AF或使AF的易患性增加[21]。與之前的研究結果[22]一致,本研究發現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一方面,反復的阻塞性呼吸暫停可引起低氧及高碳酸血癥。OSAS患者夜間睡眠時,由于心肌氧的需求及動脈血氧含量不足從而引起心肌缺血、缺氧;低氧狀態可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內皮素-1等表達增加,睡眠時反復出現的低氧-復氧使OSAS患者體內產生過多的氧自由基,使心房細胞受損[23],從而導致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此外,高碳酸血癥可導致心房有效不應期延長,隨后有效不應期恢復至基線水平,而傳導則在高碳酸血癥糾正2 h后才恢復。在高碳酸血癥過程中AF的觸發被削弱,而隨著血碳酸恢復正常后又明顯增強,這提示有效不應期及傳導的恢復可能使AF的發生率明顯增高[24]。本研究結果提示,中重度OSAS組患者夜間最低血氧值明顯低于對照組。另一方面,在阻塞性呼吸暫停期間,患者會產生胸內負壓,使上呼吸道阻塞,從而增加左心室跨壁壓力,進一步導致左心房(left atrial,LA)擴張[21]。 Schlatzer等[25]發現,模擬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引起的胸腔內壓力波動提高了房性早搏的發生率。但目前仍不清楚胸膜腔內壓的變化是如何導致心房傳導異質性的,是通過心房形態變化或交感迷走神經不平衡或肌肉間電連接中斷還是三者相互影響尚不明確[26]。LA的異常為AF的發生提供了底物。本研究發現,重度OSAS組LAD明顯大于對照組,且LAD與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呈線性相關。
P波形態異常已被證實可以反映LA的結構重構及電重構。既往研究已經驗證了與OSAS有關的各種P波指數的關系,以更好地理解OSAS與AF之間的病理生理聯系,但是產生了不同的結果[27-29]。Maeno等[30]發現,在轉診到睡眠診所的患者中,以AHI表示的SDB嚴重程度與12導聯心電圖的Ⅱ導聯的平均P波持續時間明顯相關。與之相反,在一項來自不同種族社區群體的研究中,多變量調整后,AHI與最大P波持續時間無明顯關聯。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P波持續時間及離散度(最大P波持續時間與最小P波持續時間之差)上,分別反映了心房傳導延遲及心房傳導的不均勻性。PTFV1是心房間傳導異常的P波形態指標之一,因其與AF及多種心血管并發癥的關系,最近引起了廣泛關注[3]。
在心臟彩超、心臟磁共振等先進成像技術出現之前,即使在無已知結構性心臟病的情況下,PTFV1的增加也已被證實與AF有關[31]。現代電生理研究表明,在沒有結構性心臟病的患者中,PTFV1與AF射頻消融后AF的復發風險增加獨立相關[32]。目前,關于OSAS患者是否表現出更多的PTFV1異常及其與AF關系的研究較少。Kwon等[33]發現,以AHI表示的睡眠呼吸障礙嚴重程度與PTFV1提示的亞臨床LA疾病相關。PTFV1可能是連接睡眠呼吸障礙及AF的重要心電圖標志物。同樣的,Corotto等[3]發現,OSAS的嚴重程度與異常升高的PTFV1有關。上述研究是在排除了房性心律失常的人群中進 行的。
本研究發現,AHI與PTFV1的升高相關,在調整了與PTFV1相關的變量AHI、年齡、最低血氧值后,PTFV1升高仍然與OSAS患者房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相關,這可部分解釋OSAS患者AF的發生與LA的電重構及結構重構有關,也表明PTFV1可能成為OSA患者AF發生的預測因子,可幫助我們早期識別OSAS患者中可能發生AF的高危患者。本研究未進行長期隨訪,未觀察OSAS患者經有效治療后LAD及PTFV1的變化,因此結論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本研究是臨床研究,需要進行動物實驗及細胞實驗進一步驗證OSAS誘發的房性心律失常在細胞水平及分子水平的變化,進而闡明OSAS誘發房性心律失常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