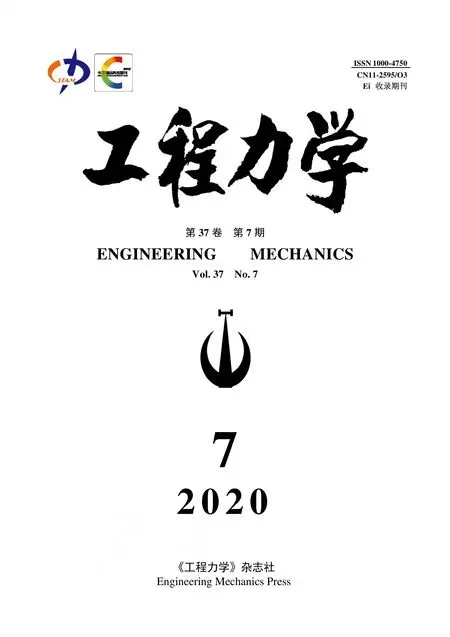矩形鋼管混凝土柱-H 形鋼梁外頂板式節點抗震性能試驗研究
付 波,王彥超,童根樹
(1. 杭州鐵木辛柯建筑結構設計事務所有限公司,杭州 311215;2. 浙江大學高性能建筑結構與材料研究所,杭州 310058)
傳統鋼結構住宅體系多采用矩形鋼管混凝土柱[1]作為結構的豎向承重構件。常規的矩形鋼管混凝土柱截面高寬比一般為1~2,且柱截面寬度超過200 mm,很容易在室內出現凸柱現象,影響建筑空間使用。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內的一些企業和高校開發了很多創新的鋼結構住宅體系[2-4],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如隱式框架鋼結構住宅體系[5]。該體系通過增大矩形鋼管截面的高寬比和減小柱截面寬度的方法,實現了將柱子隱藏于建筑墻體中,從而避免了室內凸柱問題。
對于矩形鋼管混凝土柱與鋼梁的連接節點,目前工程中常用的是隔板式梁柱節點。針對這類節點,部分學者[6-15]進行了大量的試驗研究和數值分析,規范[1]也給出了相應的設計方法。與普通矩形鋼管混凝土柱相比,隱式框架的柱截面寬度較小,一般為160 mm~200 mm,而為了方便柱內混凝土的澆筑,規范[1]要求柱內隔板上應設置孔徑不小于200 mm 的混凝土澆筑孔,因此隔板式梁柱節點已不再適用于隱式框架結構體系。
在柱內無隔板的情況下,一種新的節點構造思路是:通過在柱子外表面設置若干連接板,將連接板和鋼梁進行連接來完成內力的傳遞。Kang 等[16]給出了一種T 形加勁板節點,其基本構造方式是:H 形鋼梁的翼緣側面與四塊T 形加勁板通過角焊縫進行連接,T 形加勁板的端部與鋼管側壁通過對接焊縫進行連接。試驗研究[17-18]表明,這種節點在反復荷載作用下存在水平加勁板破壞、豎向加勁板破壞、梁端破壞共三種破壞模式,節點具有較好的滯回耗能能力和延性,能夠滿足“強節點弱構件”要求。其他文獻還報道了幾種T 形加勁板節點的改進形式,具體有:梁翼緣狗骨式節點[19]、梁翼緣蓋板式節點[20]、梁翼緣開孔式節點[21]。
為解決隱式框架結構的梁柱節點連接問題,本文提出一種矩形鋼管混凝土柱-H 形鋼梁外頂板式節點。通過對7 個新型節點試件進行擬靜力試驗,研究節點的破壞模式、承載力、延性、剛度退化、強度退化和耗能能力,并對節點傳力路徑進行了分析。最后,針對試驗中觀察到的各種節點破壞模式,分別給出相應的設計建議供工程應用參考。
1 試驗方案
1.1 試件設計
矩形鋼管混凝土柱-H 形鋼梁外頂板式節點取消了柱子的內隔板,鋼梁翼緣通過四塊設置在柱子外部的楔形板件(頂板)與柱側壁直接進行焊接,如圖1 所示。

圖1 外頂板式節點構造 /mm Fig. 1 Details of connection with external stiffeners
某高層鋼結構住宅項目的梁柱節點擬采用該新型節點形式,本試驗以該項目為原型,共設計7 個試件,變化參數有鋼梁截面尺寸、頂板厚度、頂板長邊高度等,各試件的具體參數取值如表1 所示。試件鋼管混凝土柱全部采用矩形截面300 mm×150 mm×8 mm,鋼管、鋼梁和頂板材質均為Q345B,柱子內灌混凝土強度等級為C40。為使外頂板和柱長邊對齊,各試件的鋼梁翼緣寬度加上兩側頂板厚度之和均與柱寬度相等。試驗主要關注節點區域的受力性能,故取試件的柱子高度和梁端加載點到柱邊的距離均為1 m。

表1 試件參數Table 1 Properties of specimens
對制作試件所使用的鋼板進行取樣,通過鋼材拉伸試驗得到各種厚度的鋼板材性指標如表2所示,鋼材屈服應變約為2000 με。澆筑鋼管柱內混凝土的同時,制備了邊長為150 mm×150 mm×150 mm 的混凝土立方體試塊,并將立方體試塊與試件放在相同的環境中養護。試驗開始前,實測混凝土立方體試塊抗壓強度為42.3 MPa。

表2 鋼材材性試驗結果Table 2 Material properties of steel
1.2 試驗裝置和加載方案
本試驗在重慶大學結構試驗室進行。試驗采用臥位加載的方式,水平往復荷載采用電液伺服系統(MTS)施加,以反力墻作為水平荷載的反力基座;豎向荷載通過液壓千斤頂施加,以自平衡反力架作為豎向荷載的反力基座,加載裝置如圖2 所示。
本試驗采用擬靜力試驗方法[22],在對梁端施加水平力之前,先對柱子施加軸壓力,并在整個試驗過程中保持軸壓力的恒定。試驗軸壓力取柱子的設計軸壓比0.45 所對應的軸壓力設計值。《建筑抗震試驗規程》[22]給出的加載制度分為屈服前和屈服后兩個階段,在試驗過程中需要判斷試件在何時進入屈服。根據以往的經驗,一般以加載曲線出現了明顯轉折來看作試件進入屈服的標志,但這種方式主要依靠人為判斷,隨意性比較大。故此次試驗參考FEMA 461[23]的規定,梁端水平往復加載采用位移控制的方式,取一定的位移極差來對試件逐級進行加載,每級位移增量為2 mm,每級循環3 次,水平加載制度如圖3 所示。當水平力下降到峰值的85%以下或觀察到試件發生明顯破壞時,停止試驗。
1.3 量測方案和測點布置

圖2 試驗加載裝置Fig. 2 Test set-up

圖3 水平加載制度Fig. 3 Horizontal loading history
試驗量測的內容如下:柱頂的軸壓力以及梁端水平荷載;梁端水平位移;鋼管、鋼梁和頂板的應變等。各試件的測點布置方案如圖4 所示。在鋼梁加載點布置一水平向位移計,用于量測加載點的水平位移。在鋼梁的上下翼緣各布置4 個應變片,用來測量翼緣與頂板起始連接處的翼緣應變和靠近鋼管壁處的翼緣應變。在每塊頂板上靠近柱邊的位置各布置2 個應變片,用來測量頂板的應變。在鋼管左右壁板外側共布置8 個應變花來測量鋼管的應變,其中4 個布置在鋼管豎向軸線位置,另外4 個布置在靠近頂板的位置。圖4中的梁下翼緣指的是靠近作動器一側的梁翼緣,并約定使下翼緣受拉時的水平加載值為正。
2 試驗現象和破壞情況
各試件的破壞過程如下所述:
1) SJ1-1:首先對柱子施加軸力到設計荷載值,隨后進行梁端水平往復加載。當梁端位移Δ 達到8 mm 時,觀察到節點連接區域以外的梁腹板出現明顯鼓曲,表明塑性鉸在鋼梁上形成。當Δ=12 mm 時,下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當Δ=-14 mm 時,上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當Δ 達到-18 mm 時,上下翼緣的裂縫發展至腹板,試件發生明顯破壞,如圖5(a)所示。

圖4 試件測點布置圖Fig. 4 Strain gauges and LVDT arrangement

圖5 各試件破壞形態Fig. 5 Failure modes of specimens
2) SJ1-2:加載前期的現象與SJ1-1 相似,隨著位移值的增大鋼梁首先進入塑性。當Δ=14 mm時,下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同時頂板以外的上翼緣出現明顯屈曲。當Δ=-14 mm 時,頂板以外的下翼緣出現明顯屈曲。當Δ=-16 mm 時,上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而下翼緣的屈曲更為明顯。當Δ 達到18 mm 時,下翼緣的裂縫沿著翼緣寬度方向出現較大發展,試件喪失繼續承載的能力,如圖5(b)所示。
3) SJ1-3:破壞過程與SJ1-2 基本相同,當Δ=14 mm 時,下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同時頂板以外的上翼緣出現明顯屈曲。當Δ=-16 mm時,上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下翼緣發生屈曲。當Δ 達到20 mm 時,下翼緣的裂縫發展至腹板,最終當Δ 加至-24 mm 時,上翼緣的裂縫沿著翼緣寬度方向出現較大發展,試件破壞,如圖5(c)所示。
4) SJ1-4:Δ=16 mm 時,觀察到下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的現象,同時上翼緣出現明顯屈曲。當Δ=-16 mm 時,上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下翼緣發生屈曲,此時還觀察到上翼緣與頂板之間的連接焊縫發生受剪破壞。當Δ 達到-22 mm 時,上翼緣的側面和頂板幾乎完全脫開,如圖5(d)所示。
5) SJ1-5:Δ=16 mm 時,下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的現象,同時上翼緣出現明顯屈曲。當Δ=-18 mm 時,上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下翼緣發生屈曲。當Δ=20 mm 時,下翼緣裂縫發展至腹板;當Δ=-22 mm 時,上翼緣裂縫發展至腹板。當Δ 加至-26 mm 時,上翼緣的裂縫繼續沿著翼緣寬度方向發展,試件破壞,如圖5(e)所示。
6) SJ1-6:Δ=14 mm 時,下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同時上翼緣出現明顯屈曲。當Δ=-16 mm時,上翼緣與頂板連接處開裂,下翼緣發生屈曲。當Δ=18 mm 時,下翼緣與頂板連接的另一側也出現開裂現象。當Δ=20 mm 時,下翼緣因為受拉使得裂縫迅速沿翼緣方向發展;最終當Δ 加至-20 mm 時,上翼緣的裂縫也發展至翼緣中心附近,如圖5(f)所示。
7) SJ1-7:該試件的頂板厚度與鋼管壁厚之比為1.5,在加載過程中未觀察到鋼梁翼緣出現開裂現象。當Δ=-16 mm 時,上翼緣一側的頂板與鋼管壁的連接處被拉裂。Δ=20 mm 時,又觀察到下翼緣一側的頂板與鋼管壁的連接處被拉裂。Δ=-20 mm 時,上翼緣另一側的頂板與鋼管壁之間也被拉裂。最終加載至Δ=-24 mm,上翼緣的兩側頂板連帶著其連接的部分鋼管壁與柱子幾乎完全脫開,同時清晰可見柱內的混凝土,如圖5(g)所示。
綜上所述,本次試驗的7 個矩形鋼管混凝土柱-H 形鋼梁外頂板式節點試件共出現了三種破壞模式,分別是梁翼緣受拉破壞(SJ1-1、SJ1-2、SJ1-3、SJ1-5、SJ1-6)、梁翼緣與頂板連接焊縫破壞(SJ1-4)、頂板與柱連接處的柱壁破壞(SJ1-7)。
3 試驗結果和分析
3.1 滯回曲線
各試件的梁端水平力-水平位移滯回曲線如圖6所示。其中SJ1-2、SJ1-3、SJ1-5 和SJ1-6 的滯回曲線比其他幾個試件都要飽滿,曲線形狀呈梭形,表現出較好的滯回耗能能力。SJ-4 的滯回曲線在正向加載的后期出現一定的捏攏現象,這是因為負向加載到16 mm 時,上翼緣與頂板的連接焊縫發生破壞,兩者之間出現間隙,在隨后的正向加載過程中,需待間隙閉合后試件剛度才能得到恢復。在SJ1-1 和SJ1-7 的加載后期,由于節點連接區域出現了明顯開裂,導致最后幾個滯回環的坡度變得越來越平緩,呈現出顯著的滑移特性。比如SJ1-7 的上翼緣兩側頂板和柱壁在受拉時幾乎完全脫開,在反向加載時要經過一定的變形之后該裂縫才能閉合,這一過程在滯回曲線上表現為曲線需經過一段較長的滑移之后,荷載才能有所上升。
3.2 骨架曲線、承載力和變形能力
圖7 給出了各試件的骨架曲線,由該曲線可得到試件的承載力和變形能力等抗震性能指標,將各試件的主要性能指標匯總如表3 所示。表中的屈服荷載和屈服位移定義為柱邊鋼梁截面彎矩達到屈服彎矩My時所對應的梁端力和位移;極限位移取荷載下降到峰值荷載85%時對應的位移;延性系數為極限位移和屈服位移之比;節點超強系數為峰值荷載與柱邊鋼梁截面彎矩達到塑性彎矩時所對應的荷載之比。
由SJ1-1、SJ1-4 和SJ1-7 的結果對比可知,隨著頂板厚度的增加,節點承載力有明顯提升。由SJ1-1~SJ1-3 和SJ1-4~SJ1-6 的結果對比可知,隨著頂板長邊高度的增加,節點承載力也有所提高。而從各試件變形指標的對比來看,加大頂板截面對試件變形能力沒有直接影響,極限位移較小的幾個試件主要是受鋼梁翼緣裂縫開展較早(SJ1-1、SJ1-2)、頂板和翼緣連接焊縫破壞(SJ1-4)以及鋼管壁板被拉裂(SJ1-7)的影響。由圖7 和表2 可知,試件的屈服位移角為1/209~1/132,平均值為1/158,各試件均滿足彈性層間位移角不小于1/300 的要求[1]。試件極限位移角為1/84~1/38,平均值為1/49,部分試件沒能達到彈塑性層間位移角不小于1/50 的要求[1],針對試驗反應出的問題,有必要采取措施確保節點變形能力滿足設計要求,第4 節將為此進行討論。延性系數為2.17~3.67,平均值為3.21,表明該節點具備一定的變形能力。節點超強系數為1.18~1.50,平均值為1.36,說明節點能夠滿足“強節點弱構件”的要求。


圖6 梁端水平力-水平位移滯回曲線Fig. 6 Hysteretic loops of horizontal force-displacement

圖7 試件骨架曲線比較Fig. 7 Comparison of skeleton curves of specimens

表3 試件性能指標Table 3 Performance indexes of specimens
3.3 剛度退化
試件剛度的退化情況采用環線剛度[24]來進行表征。環線剛度定義為某級荷載下,各次循環的加載峰值絕對值之和與峰值位移絕對值之和的比值。計算得到的環線剛度-梁端水平位移變化曲線如圖8 所示。從圖8 可知,剛度退化速度也與試件的開裂情況密切相關。SJ1-1 的梁翼緣裂縫出現最早,SJ1-2 的梁翼緣裂縫擴展較快,因此這兩個試件的剛度退化速度均比較快。SJ1-4 在上翼緣與頂板連接焊縫出現破壞后,負向剛度出現迅速下降,而正向剛度的退化則保持平穩。SJ1-7 的上翼緣頂板與柱壁連接處開裂嚴重,導致負向剛度退化很快,正向剛度在最后兩級加載時也呈現加速下降趨勢。另外3 個試件的剛度退化情況比較一致,其共同特點是梁翼緣裂縫出現較晚且發展速度較慢。

圖8 環線剛度退化曲線Fig. 8 Stiffness degradation curves
3.4 強度退化
試件強度退化情況采用強度退化系數[24]來進行表征。強度退化系數定義為某級荷載下,第i 次循環荷載峰值與第1 次循環荷載峰值之比。計算得到的強度退化系數-梁端水平位移變化曲線如圖9所示。從圖9 可知,在同一級荷載的循環作用下,SJ1-3、SJ1-5 和SJ1-6 的強度退化系數始終保持在0.95~1.00 之間,荷載循環次數的影響很有限,說明這3 個試件在低周反復荷載作用下,強度退化程度比較小。其余幾個試件則受到節點連接區域板件開裂的影響,在某一級荷載作用下,試件承載能力隨著循環次數的增加而快速下降,在圖9 上表現為曲線存在陡降段,之后試件的強度退化系數又會有所增加,這表示試件在發生破壞之后還具有一定的殘余承載力。
3.5 能量耗散

圖9 強度退化曲線Fig. 9 Strength degradation curves
試件的耗能能力可用等效黏滯阻尼系數[22]來表示,圖10 給出了各節點試件的等效黏滯阻尼系數和循環數的關系曲線。從圖10 可知,加載初期,由于試件還在彈性階段工作,等效黏滯阻尼系數較小。隨著荷載值的增大,試件進入塑性,等效黏滯阻尼系數相應穩步上升到0.2~0.3。對比各類節點耗能能力的數據[3],新型外頂板式節點的耗能能力要遠好于鋼筋混凝土節點,與型鋼混凝土節點的耗能能力比較接近,但要略低于傳統的隔板式節點,這與各試件出現不同程度的開裂現象有關。對于裂縫開展較嚴重的試件,在加載后期,等效黏滯阻尼系數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另外在同一級荷載的循環作用下,隨著循環數的增加,等效黏滯阻尼系數也會略有降低。

圖10 等效黏滯阻尼系數-循環數曲線Fig. 10 Equivalent damping coefficient-number of cycles curves
3.6 節點剛度分析
若要判斷梁柱節點是否為剛接節點,最直接的方法是在試驗過程中測量節點相對轉角,得到節點彎矩-轉角曲線,根據該曲線計算使用荷載下節點的轉動剛度ks,然后將ks與一定倍數的梁線剛度ib進行比較[25-26]。
目前常用的節點相對轉角測量方法有以下兩種:一種是在試件上布置若干位移測點,根據測點間的幾何關系,利用測點位移值來計算節點相對轉角;另一種是在試件上布置多個傾角儀,根據各測點傾角數據的關系來得到節點相對轉角。上述方法均屬于間接測量法,計算得到的節點相對轉角很難準確扣除鋼梁和鋼柱變形的影響[27]。鑒于節點相對轉角測量技術的不完善,本文采用梁端位移比較法來評估新型節點剛度的大小,具體做法如下。

根據現行鋼結構設計標準[28],鋼梁的承載能力設計值為1.05My,假定鋼梁應力比限值控制在0.9,另外再考慮1.3~1.5 的綜合分項系數,則在正常使用狀態下的鋼梁彎矩值約為0.63My~0.73My,故使用階段荷載Fs取柱邊鋼梁截面彎矩達到0.7My所對應的梁端力。式(1)計算值對應梁柱節點為理想剛性的情況,若節點存在相對轉角,則該轉角相當于使鋼梁發生了剛體轉動,從而使梁端位移值增大。故考慮節點相對轉動的梁端位移wb2由式(2)來進行計算:

參考歐洲規范EC3[25]的判別標準,對于有側移框架的梁柱剛接節點,ks應不小于25ib,這意味著式(2)中的ks最小可取25ib。將試件骨架曲線上Fs所對應的梁端位移值與式(1)計算值、式(2)中ks=25ib的計算值進行比較如表4 所示。

表4 梁端位移比較Table 4 Displacement comparison of beam ends
由表4 可知,SJ1-1、SJ1-4 和SJ1-6 的式(1)計算值和試驗值很接近,說明這三個試件接近于理想剛接節點。其他試件按式(2)得到的計算值與試驗值也符合比較好,說明剩余試件能夠滿足EC3 對剛接節點的要求。從SJ1-1、SJ1-4 和SJ1-7 的結果對比來看,隨著梁翼緣厚度的增加,式(1)計算值和試驗值相差越大,表明節點剛度有減小的趨勢,而由SJ1-4~SJ1-6 的結果對比可知,增加頂板長邊高度,節點剛度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強。
3.7 應變分析
以SJ1-3、SJ1-6 和SJ1-7 的應變數據為例,對加載過程中,試件各部分的應變情況進行分析。
3.7.1 試件SJ1-3 應變
圖11 分別給出正向加載達到6 mm 和14 mm時的SJ1-3 應變分布情況,位移值分別對應試件即將進入屈服和達到峰值荷載。圖中的數據均取自與鋼梁下翼緣同側的測點。對于柱壁應變,給出的是測點位置的最大主應變,由式(3)來進行計算:


由圖11(a)可知,試件即將進入屈服時,梁翼緣兩側靠近頂板處的應變已超過鋼材屈服應變2000 με,頂板和柱壁則未進入屈服,表明塑性鉸將首先出現在鋼梁上。梁翼緣應變沿著翼緣寬度方向的分布很不均勻,翼緣和頂板連接處是頂板傳遞內力的起始點,此處具有剛度突變的特點,應變水平比較高,且該處同時是焊縫的起點,容易存在焊接缺陷,故鋼梁翼緣的開裂首先在該位置處產生;翼緣中心應變則要遠小于翼緣兩側的應變。靠近柱邊的梁翼緣中心應變始終都很小,說明從翼緣和頂板連接處開始,翼緣內力主要通過翼緣兩側的頂板向柱子進行傳遞。頂板應變和頂板邊的柱壁最大主應變基本相等,當試件達到峰值荷載時,這兩處的應變也會進入屈服,但塑性發展程度有限,應變大小約為屈服應變的1.5 倍~2.25 倍,此時柱中心的柱壁最大主應變很小,說明柱壁屈服區域主要集中在頂板附近,柱子整體的應力水平并不高。
3.7.2 試件SJ1-6 應變
圖12 分別給出正向加載達到6 mm 和12 mm時的SJ1-6 應變分布情況,圖中的數據均取自與鋼梁下翼緣同側的測點。由圖12 可知,梁翼緣應變分布規律和內力傳遞路徑與SJ1-3 相同。由于試件的頂板厚與柱壁厚之比為1.25,柱壁相對較薄,故頂板邊的柱壁最大主應變要大于頂板應變,且當加載達到6 mm 時,有一側的頂板邊柱壁與梁翼緣同時進入塑性。隨著荷載的增加,梁翼緣塑性的發展程度要遠大于柱壁,因此可認為試件的塑性鉸仍然形成在鋼梁上,最終的破壞模式也表明該試件是梁翼緣發生破壞。柱中心的柱壁最大主應變始終比較小,說明柱壁屈服區域仍主要集中在頂板附近。

圖12 SJ1-6 應變分布Fig. 12 Distribution of strain (SJ1-6)
3.7.3 試件SJ1-7 應變
圖13 分別給出正向加載達到6 mm 和14 mm時的SJ1-7 應變分布情況,圖中的數據均取自與鋼梁下翼緣同側的測點。該試件的頂板厚與柱壁厚之比達到1.5,由圖13 可知,加載6 mm 時,頂板邊柱壁的一側應變水平已比較高,達到屈服應變的2.25 倍;梁翼緣應變雖然仍是呈兩側大,中間小的特點,但最大應變沒有超過屈服應變,表明試件的塑性發展部位從鋼梁轉移到了頂板邊的柱壁上。隨著荷載的增加,先進入屈服的頂板邊柱壁塑性發展程度很快,導致兩側柱壁應變值相差很大,同時使得鋼梁應變沿翼緣厚度方向呈線性分布,最終該試件的破壞模式為頂板邊的柱壁被拉裂。

圖13 SJ1-7 應變分布Fig. 13 Distribution of strain (SJ1-7)
4 提高節點變形能力的措施
傳統內隔板節點的極限位移角約為1/30[29],而本次試驗得到的新型外頂板式節點極限位移角要低于這一數值。試驗值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部分新型節點試件發生了脆性破壞。為確保新型節點具有足夠的塑性變形能力,針對試驗得到的三種節點破壞模式,可分別采取以下措施來避免脆性破壞的發生。
1) 頂板與柱連接處的柱壁破壞
當柱子與厚翼緣鋼梁相連且柱壁相對較薄時,由試驗結果可知,在鋼梁上不一定能形成塑性鉸。為避免節點塑性發展區轉移至柱壁上,此時柱壁相對于鋼梁應具有足夠大的承載力。
根據外頂板式節點的傳力特點,可認為鋼梁彎矩完全通過兩側頂板傳遞至柱壁。記鋼梁形成塑性鉸時的翼緣內力為Tpb=Mpb/(hb-tf),Mpb為鋼梁塑性彎矩,hb為鋼梁截面高度,tf為鋼梁翼緣厚度。假定鋼梁塑性鉸位于頂板和梁翼緣連接處,則塑性鉸距柱邊長度為lp,此時柱壁內力Tpc=0.5Tpb/(1-lp/lb),lb為鋼梁長度。取柱壁受力高度與頂板長邊高度相等,則柱壁極限承載力為Tuc=fuhp2tc。對于Q345 鋼[28],屈服強度fy=345 MPa,極限強度fu=470 MPa。將各試件的Tpb、Tpc和Tuc匯總如表5 所示。由表5 可知,SJ1-7 的柱壁承載力沒有達到超強要求,因此該試件的破壞模式為柱壁破壞。注意到SJ1-4 出現的是翼緣與頂板連接焊縫破壞,剔除該試件的結果,其余試件的破壞模式均是梁翼緣破壞,Tuc/Tpc最小值為1.18,平均值為1.30。根據試驗結果,為保證柱壁不先于鋼梁發生破壞,建議工程設計時取節點連接系數[30]等于1.4 來驗算柱壁極限承載力。

表5 柱壁承載力計算Table 5 Strengths of wall plates of steel tubes
2) 梁翼緣與頂板連接焊縫破壞
出現這種破壞模式主要是因為焊接質量的問題。試驗后檢查試件SJ-4,發現在試件的破壞部位,焊縫金屬和母材并沒有熔合在一起(圖14)。翼緣與頂板連接焊縫是節點區域的主要傳力焊縫,在構件制作方面,應強調對該條焊縫的焊接質量進行嚴格控制,另外設計時同樣應按連接系數1.4 來對焊縫進行極限承載力驗算。

圖14 焊縫破壞形態Fig. 14 Failure mode of weld
3) 梁翼緣受拉破壞
由試驗結果可知,這種破壞模式表現出一定的塑性變形能力,但是當翼緣和頂板連接處過早產生裂縫時,該裂縫的發展會降低節點的延性和耗能能力。為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可考慮對矩形鋼管混凝土柱-H 形鋼梁外頂板式節點做出以下改進,如圖15 所示。前兩種形式屬于梁端加強型節點,后一種屬于梁端削弱型節點,其目的都是為了避免翼緣和頂板連接處出現裂縫,從而使鋼梁塑性變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后續擬針對這幾種改進型節點做進一步的試驗研究和分析。

圖15 改進型外頂板式節點示意Fig. 15 Modified connections with external stiffeners
5 結論
通過對矩形鋼管混凝土柱-H 形鋼梁外頂板式節點進行擬靜力試驗研究,可得到以下結論:
(1) 往復荷載作用下,外頂板式節點試件出現了梁翼緣受拉破壞、梁翼緣與頂板連接焊縫破壞、頂板與柱連接處的柱壁破壞共三種破壞模式。
(2) 外頂板式節點的延性系數為2.17~3.67,等效粘滯阻尼系數在0.2~0.3,所有試件的極限位移角平均值為1/49,節點剛度能夠滿足歐洲規范EC3 對剛接節點的要求,節點抗震性能滿足“強節點弱構件”要求。
(3) 增大外頂板的厚度或長邊高度,可提高節點承載力,但對節點變形性能影響不明顯。若節點區的鋼梁翼緣、翼緣和頂板連接焊縫或柱壁過早出現裂縫,則節點延性和耗能能力均會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4) 為避免柱壁和連接焊縫的破壞,除了應嚴格控制焊接質量外,在驗算柱壁和連接焊縫的極限承載力時,節點連接系數應取1.4。為確保外頂板式節點具有足夠的塑性變形能力,可考慮采取梁端翼緣加強或削弱措施,以避免梁翼緣和頂板連接處過早產生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