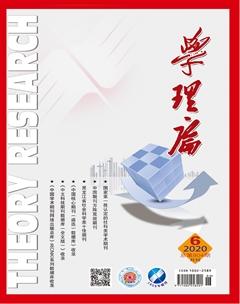荀子正名思想探析
羅康
摘 要:荀子正名思想,在繼承孔子名實相符的基礎上,對制名的原則、名實的辯證關系進行詳細的論證,從而形成了一套客觀性、功利性的禮義道德規范,其所強調的天人相分、化性起偽和隆禮重法等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
關鍵詞:荀子;孔子;正名;禮義
先秦時期,諸子各家大都重視形名之學的研究,“老子要無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說言有三表,楊子說實無名、名無實,公孫龍有《名實論》,荀子有《正名》,莊子有《齊物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1]“名”成為各個學派闡述學術思想的窗口,通過辨正名分、循名責實,為解決社會混亂、實現社會政治的有序性提供理論依據。
一、正名的提出
孔子作為正名觀念的最早提出者,乃是迫于春秋末期周文罷弊、名實乖亂的時代現象,而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天下無道、王綱解樞的局面,必須從正名做起。“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孔子言正名,單就現實政治而言,與后來名家的純名理邏輯之辯不同,目的在于通過德性的恢復,重塑社會秩序。
正名作為“為政”之首要,由“正”到“政”,由人倫秩序上升至政治秩序,具體表現為:正己和正道。“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政者,正也。子帥以正,誰敢不正?”(《論語·顏淵》),孔子立足于個體,注重個人的修養,尤其是為政者的德行,為政者只有自身德行端正才能做到修己安人,百姓才會樂于臣服。“邦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邦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在于貴賤有序,君與臣、父與子、賢者與小人的名位要符合“禮”的規定,如此才能實現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穩定。
二、荀子正名思想的內容
荀子所處的時代“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孟子·滕文公下》),辯詰之風盛行,名家、墨家、楊朱學派等將“名實”之論的核心由政治倫理轉移到了自然界,發展為純名理邏輯之辯,擾亂了人們對是非的正常判斷。荀子論述正名,首先明確制名的目的和重要性,制名的目的在于上辨同異,下明貴賤,實現“名定而實辨”,從而為圣王制名、合乎禮法提供依據。
(一)制名的原則
1.循舊名,作新名。荀子作為儒家堅定的衛道者,積極倡導君主“行先王之道”,“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荀子·非十二子》)在荀子看來,即便擁有著無上的權威和地位,但是卻不遵從先王制定的禮義制度,終究逃不過身死國滅的宿命。
“后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荀子·正名》)
荀子認為,現在的君主用以維持社會秩序和交流而確定的名稱,多是沿襲之前朝代的,因為歷史證明,這些典章制度是在不斷地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歷史精華,遵循比妄改更重要。雖然荀子主張“循舊名”,但并不意味著舊名全是合適的、有益的,而是在今世進行驗證,對于那些不符合現實需求的,就要進行修正,正如韓非子所言,“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
2.約定俗成。荀子認為事物的命名沒有本來就合適的,之所以確定了這個名稱,是由于人們共同約定而成的,“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荀子·正名》)約定俗成即得到大眾的認可,就算得上名實相符。
3.稽實定數。“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荀子·正名》)荀子指出,事物的存在狀態千差萬別,有兩個相同事物在不同的位置,有同一個事物但改變了形狀的,事物名稱的同異和數量沒有必然聯系,形狀雖然相同但處在不同位置,雖然可命為同一名字,確是兩個不同的實體;僅僅是形狀改變本質未變,仍是一個實體。荀子承認客觀事物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對名家使名實分離的詭辯進行了有力駁斥。
4.圣王制名。刑名、爵名、文名等一系列典章制度皆由后王所制定,“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荀子·正名》)君王確定事物的名稱,幫助民眾分辨事物,以便人們互相溝通,君王制名要尊重民眾約定俗成形成的名稱,也避免民眾肆意命名。王者制名的合理性在于君王既能夠明分使群,又具有制定禮義的合法性。
(二)正名以明分
荀子通過制名辨別了同異,區分貴賤差等,“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荀子·正名》)荀子強調分的重要性,在于他認為“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荀子·王制》)假若國家內人人身份地位相同,沒有貴賤等級之別,那社會必將變得無序,有差等既是保持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也是人的天性所使然。
1.天人之分。荀子認為,天不為而成,不求而得,雖有其運行規律卻不是世間最高主宰,天既無客觀的意志也沒有控制國家興衰的能力,荀子以極為客觀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天,“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荀子對天的理解不同于孔子的主宰之天、孟子的義理之天,而僅代表自然之天。相對于天的客觀無為,人是具有主觀意志并有作為的,不同于既往所強調的天人合一觀念,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荀子·天論》)天的職分在于生養萬物,人的職能在于治,即在禮義的規范下進行社會性活動。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禮論》)荀子劃分了天和人的功用,把人的地位提升至與天同樣的高度。天人之分,不僅要識別天的職分,也要區別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實現小人向君子的轉變。
2.性偽之分。荀子主張人之性惡,并運用正名原則,對性進行分析梳理。“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荀子·正名》)“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荀子·性惡》)荀子指出,性本身無善無惡,人性也有基本的自然需求,只是因為過分追求食色之欲而產生爭奪,以至于辭讓禮儀消亡。
荀子在批判孟子性善之論時對性和偽進行了區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能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人之天性無善無惡,善是人在后天所習得的;偽,即作為,是對先天之性有目的的改造,是為了避免性朝惡的方向發展而進行的引導,也是圣王進行教化的出發點。
在荀子看來,正因為有了性與偽的區分,才有了圣人“化性起偽”的必要,也為圣人制禮義法度提供依據。荀子通過論述人的自然欲望存在的合理性,指出人之性惡,繼而引出圣人制禮義以化性起偽的政治功效,為解決當時治亂的問題提供理論保障。
(三)正名以隆禮
荀子用“分”確立了社會內部等級差別,用“辨”規范了人們對禮義的認知。荀子繼承了孔孟關于倫理道德的思想,并始終將“禮”看作最高的政治標準,從個人、社會、國家的角度把“禮”的內涵外在化、客觀化、功利化。對個人來說,禮是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禮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對于社會,禮是進行社會分工、維護等級差別的工具,“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富國》)對于國家,禮是法度綱要的衡量標準,是政治秩序的保障,“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荀子·不茍》)
荀子把“禮”的地位提升至政治理論層面,乃是因為“人性惡”作為荀子禮制思想產生的道德前提,為了避免其肆意放縱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也為了保證社會規范穩定的發展,但無論把“禮”提升至何等崇高的地位,它仍是一種非強制性理想化的倫理規范。鑒于此,荀子借鑒法家的治理經驗,援法入禮,將“法”提高到與“禮”具有同等政治效用的治國手段,建立起先秦禮法合一的獨特關系。“治之經,禮與刑。”(《荀子·成相》)荀子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傳統儒家只重禮制忽視刑罰強制約束力的不足,他對禮法的不同功效做了不同解釋,并把二者作為互補的兩個方面,因事而異,區別處置,“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荀子·王制》)禮作為約定俗成的軟規則,依靠道德輿論維持,強調禁未發之前;法則刑已發之后,用強制性手段達到震懾效果。
雖然實現了“禮”“法”的結合,并不等于荀子承認了“法”在政治層面與傳統的“禮”具有等量齊觀的地位,相反,荀子還是更突出強調“禮”的倫理規范作用,“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惡》)隆禮重法,既為禮增加了強制力量,又使禮本身的規范教化得以擴展,使禮同時具備了法律屬性合道德屬性,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更有操作性和控制性,作為更加完備的“治道”設計,荀子的禮法教化思想在秦之后的歷代王朝一枝獨秀。
三、荀子正名思想歷史意義
儒家強調名正言順、名實相符,荀子所倡導的正名思想不同于名家墨家的名實邏輯之辯,實是以“禮法”為核心的政治倫理的基礎,旨在辨明社會等級界限,確定君臣行為準則,規范社會道德秩序。韓非子和李斯作為荀子的高足,較為全面地繼承了荀子在制名、集權和一天下的思想,為封建專制集權大一統之治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及至漢朝初期,董仲舒承繼荀子人性論、禮法兼重和立足現實經世致用的思想,吸收孔子道德之天的理念,改造傳統的天人觀將天神圣化,正式確立了儒學的獨尊地位,影響后世歷代王朝。
參考文獻: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