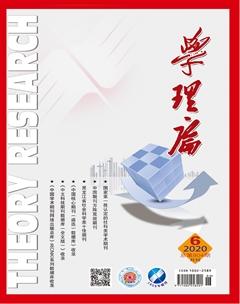晚清四川綠營軍器研究
伍星堯
摘 要:盡管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中已經見識過西方武器的巨大威力,中國的軍事將領們卻仍然對使用這些武器抱有疑慮。1851年開始的太平天國戰爭所帶來的現實需求顯然有助于推動中國軍隊的將領們打消顧慮。大規模的內戰,不單有以湘淮軍為代表的新式勇營部隊興起,舊式的綠營軍隊中亦通過總結戰爭經驗而產生了相應的變化。有關淮勇營部隊的研究成果已較為豐碩,而針對這一時期綠營軍隊發展態勢的研究卻鮮有報道。本文以清代晚期同治、光緒年間的四川地方志作為主要材料,考察這一時期四川綠營軍的軍器種類、性能和實戰效果。通過分析發現,西方武器的影響已經可以見諸于軍隊的各個方面。
關鍵詞:晚清;綠營;軍器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通過對比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和英國雙方軍事裝備的編制、性能及制作手段和保養效果,對戰前及戰爭過程之中的中國軍事技術水平與西方的差距進行了詳細的闡述[1]。羅爾綱先生在《綠營兵志》中,對清代綠營軍隊的武器裝備及其編制進行了考證研究[2]。歐陽泰先生的《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從火藥武器在中國的起源開始,對自唐宋一直到晚清的東方火器發展及同時期的西方火器進行了梳理和比較[3]。大略而言,上述研究對19世紀40年代在西方影響之下中國軍隊的武器及技戰術水準做出了較為詳盡的論述,而關于之后出現的湘淮勇營部隊的研究成果則更為豐碩。
相對而言,綠營軍隊軍事裝備的發展態勢,包括兵器裝備的種類、編制、性能和使用情況等等問題,則尚少有提及。本文擬以清代晚期同治、光緒年間的四川地方志作為主要材料,考察這一時期四川綠營軍的軍器種類、性能和實戰效果,以期對該時段內中國軍事的發展進程研究有所補遺。
一、咸豐、同治年間的四川綠營軍器:編制與庫存
19世紀50-60年代接連而起的太平天國、捻軍等諸役,使得西方的新式火器及其他技術漸次傳入中國。
在軍事層面上,西式的前膛燧發槍、擊發槍乃至于較早型號的后堂撞針槍械的傳入,大大增強了以湘淮軍為代表的勇營部隊及其對手太平軍的火力,亦促使軍事戰術產生了變化[4]。在同一時期,綠營作為清朝主要軍事力量的職能開始為“新式”的勇營所取代。然而,勇營人數有限,綠營仍然是維護地方治安的主要力量。在四川這樣的內陸省份,綠營依舊是清廷所能依靠的主要軍事存在[5]。
在軍器編制上,《皇朝兵制考略》對四川駐防軍隊的軍器總額做了記載。據其書《直省各標鎮協營原設槍炮數目》表載,四川各軍共有大小炮七百六十四位,鳥槍一萬八千七百六十桿。其后,《各省增添槍炮數目》表中又載四川本地于道光二十一年(1839)五月,經由“駐藏大臣孟(保),奏添抬炮二十尊”,咸豐二年(1851)十月,“總督徐,奏捐鑄劈山炮五十尊”[6]。與同表其他各省比較,四川省的大小火炮存量為全國最少,較之第二少的湖北(八百九十五尊)尚有百尊之差,而鳥槍則尤其之多,較京畿重地的直隸省多出四百余桿。若再以同書所載道光三十年(1848)兵部冊檔中的四川兵額總數,則四川駐軍中的火器配備概率,當不低于總兵數目的百分之六十[6]。
咸豐、同治年間駐防四川各地的綠營兵,在其軍事裝備上體現出一種輕裝化、火器化的特點,這既是清廷依據各地地勢及水路的具體情況,令綠營軍“因地制宜,酌定規制”的體現,亦說明四川的綠營在裝備上有一定的獨特之處。
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39)刻《龍安府志·武備志》中即載,龍安“現存各營汛實在馬步戰守兵四百六十二名”,而“額設劈山炮五位,子母炮五位,威字號纏絲鳥槍二百七十二桿。”此外,尚有“東西二門各安鐵炮一位,南門安設銅炮一位”[7]。從數字上看,龍安營中鳥槍兵已經占總兵力的六成。營中所設劈山炮、子母炮,是兩種輕型火炮,關于其性能,《蘭州紀略》中稱:“至蘭州舊存子母炮僅與鳥槍無異,施放不能及遠,又威遠炮八尊,子重十六兩至二十兩,轟擊稍遠,而施放時易于跳動,又無準頭,俱不甚得力。現已照四川劈山炮式樣制成二十尊,擊打賊營,甚為便捷得力。”[8]可見所謂子母炮者僅僅是威力比同鳥槍的羽量級火器,而劈山炮則其射程、準確度及威力都要較前者為佳。
另一個事例則來自同治九年(1870),在時任會理知州的鄧仁垣所修《會理州志》第七卷《武備志》,對駐扎當地的會川、永定二營軍隊所配備軍器的種類、數額及添補情況有詳細的記載。據載,會理州內會川營額設“馬兵四十三名,戰兵八十七名,守兵三百一十三名,共馬步戰守兵四百四十三名”;永定營“馬兵十五名,戰兵六十二名,守兵一百六十三名,共馬步戰守兵二百四十名”。熱兵器方面,會川營按編制擁有劈山炮五位,大槍三十五桿,五子炮一位,鳥機三桿,鳥槍二百二十二桿,后又新添劈山炮六位,鎮邊劈山炮一位,抬炮六位,抬槍三十九桿,鳥槍六十桿。所謂“大槍”同《大清會典圖》所記載的“自來火大槍”類似,是一種大型的火槍[9]。據《中西兵略指掌》所載,五子炮乃是與劈山炮、佛郎機、狗頭炮并列的“中土舊式”火炮,其“母炮背開一闕,以子炮入之,藥裝于子,五子互換,終日不息”,是一種“佛郎機炮”式的輕型子母火炮[10]。至于鳥機,按焦勛述所撰《火攻挈要》所記,“佛狼機系西洋國名,鳥機即狼機之極小者。”[11]則其也是一種輕便的子母銃火器。冷兵器方面,會川營有腰刀四百口,戰箭五千五百七十只,以后又添加牛耳腰刀二百把,長矛一百四十九根。永定營按編制有劈山炮二位,五子炮一位,鳥機二桿,鳥槍一百二十一桿,雙手帶刀十把,腰刀二百零九口,戰箭二千五百三十只[12]。
觀察會川、永定兩營所裝備的軍器,可以看到,兩營軍隊軍器中火器所占據的比例都應當在六成之上,而按會川、永定二營總的馬步兵及其軍器配額中鳥槍、腰刀的數量來看,則兩營中的鳥槍及弓箭步兵,應也同時佩戴有腰刀,以作近身搏戰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會川營新添的軍器之中,除鳥槍、腰刀之外,尚有抬槍、抬炮、長矛三種不曾見于前冊的武器。須知長矛雖然為綠營制器,然而早在雍正年間朝廷議定各省軍器編制時便有人提出,長矛“遇險狹地方,不能旋轉任意”,而應當“改為藤牌”。抬槍、抬炮兩種武器雖然早經使用,但其不單未見于兵部議準的各省規定編制中,即使工部等處所造軍器,在乾隆、嘉慶乃至道光年間都少有提及。那么,會川營中新增這三種不見于造冊的武器,其緣由又是怎樣的呢?對此,《會理州志》中沒有直接的記載,如果考慮到以下事實,則這種軍器裝備上的變化亦可說是有跡可循。
在《重修會理州志序》中,鄧仁垣曾言其致力重修州志的部分原因是“況兵燹之后,忠孝節烈者尤為昭茲若示亟早圖修前徽亦沒后沒弗彰處。”[12]所提及之兵燹,按時間而言,應當包括太平天國及之后云南、四川一帶的數次起義。更加直接的證據來源于《州志》卷六人物志中的忠孝一節,此節之下所記載的“道光三十年從征湖北江南發匪陣亡兵丁”,這之中“湖北江南匪”顯然是指當時在中國南方占據城池的太平軍,而陣亡人數高達一百零三人,從側面也說明其參與戰事當較為激烈。忠孝一節中還記載有“咸豐十一年剿辦滇匪陣亡兵丁”十四人,以及同治元年及二年“堵剿匪”陣亡兵丁二人,此兩件事分別為杜文秀起義及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入川[12]。又據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卷一,咸豐元年(1851)六月賽尚阿等人抵達廣西桂林招募廣勇潮勇,又合“先后所調滇黔川楚兵勇約三萬余人”[13]。從時間上來說,會川營兵丁參與到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之中,應該是在此前后。考慮到無論是在太平軍還是之后的湘軍勇營之中,抬槍,抬炮及長矛劈山炮的使用都相當廣泛,會川營中補添的上述三類軍器,很可能是該營在對太平天國的作戰期間,根據戰場經驗進行補充的結果。從兵器的角度而言,劈山炮、抬槍、抬炮都是需要多人操作的較大口徑火器,而其性能上則尤其以能發射散彈,壓制敵軍步兵最為可貴。《中西兵略指掌》中說:“至水陸戰事,擊遠者固屬可貴,多食群子者尤為可寶,二者不可得兼,則舍擊遠而取食群子者。”當時江西、兩湖等地所造劈山炮“頗能擊遠”,被軍中認為是利器,而曾國藩卻仍“尚以其不能食群子為嫌。”[14]抬槍、抬炮則除能在近距離射擊中使用“馬口鐵盒,實以群子,以漆固之,出口后亦能四散撲人”的散彈之外,更可以利用“十五口徑以上之炮”,“越山越城”“自上而下”地打擊遠距離目標,以收到“炸物焚營”的效果[15]。至于長矛的補添,有兩條信息可以略作探源:首先,在冷熱兵器混用時代,火藥武器由于發射速度較慢,且射程威力也不足以給予敵軍決定性的殺傷,因此當時的戰爭雖然大量使用火器,但勝負之數,最終還是要回到白刃戰斗中來決定。其次,作為會川營等綠營軍隊對手的太平天國部隊,其士兵“雖無技藝,然齊一心智,誓死以斗。”在戰場上則“以無技為技,以人眾為技,以敢死為技”,而“其打仗亦有熟習之技,每遇我兵槍炮齊施時,皆伏貼于地,候彈稍稀,雀躍而猱進,轉已至槍兵之前,甚至舉刀矛傷我一二人,此時我之火器已屬無用,若刀矛兵退縮,鮮有不敗者。”[16]由此可知,早期太平軍能憑借以制敵取勝之處即在敢于近身搏戰,而同時與之對陣的綠營軍雖然火器眾多,能夠“槍炮齊施”,但火力卻不足以對太平軍造成足夠的傷害。一旦近身“火器已屬無用”之后,勝敗則仍然取決于使用冷兵器的刀矛手的強弱。綜合這些材料,可以認為,會川營中補添長矛的行為,或許正是針對當時綠營軍在實戰中暴露出來的近戰能力不足這一問題的一種補救措施。
除卻會川、永定兩營軍隊的軍器之外,《會理州志》中還有“練器”一節。所謂“練”即是團練,而“器”則是武器。據其記載,制造這些團練器械的原因在于“咸豐十年,滇省回逆竄據州城”,當時官員因而“練團勇,新鑄將軍大炮四尊”。等到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后,一切團練武器都被知州徐傳善“設靖邊局備貯,以御邊防”[12]。除大炮之外,靖邊局中還有“抬槍四十桿,滑炮十五桿,叉子槍三十桿,鳥槍六百桿,劈山炮十二位,懷抱雷二位,子母炮三位。”從數量上來說,會理靖邊局所存的火藥兵器,甚至要比會川、永定兩營的正規軍的器械之和還要多,而冷兵器則極少。這種情況一方面與嚴如煜“百姓各有身家”“不值與賊拼命”,進而提倡多用火器的主張相合,在另一方面卻也或許也能說明,經歷太平天國及其后逐次大亂的清朝政府和綠營軍隊,已經很難以像叛亂之前那樣繼續提供相對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治安保障,這種狀況反應到民間上的結果,即是如同會理州這樣,出現民間不得不自行設局籌器,聚集團練自保,且團練裝備的火器甚至還要超過當地駐軍的情形[12]。
綜合來看,盡管咸豐、同治年間的四川綠營軍隊在軍器的裝備上即有按雍正、乾隆年間的定制所規定的鳥槍、藤牌一類,同時也根據其自身的作戰經驗,更新裝備了更類似于勇營部隊的抬槍、長矛。在性質上而言,它仍然是一只冷熱兵器混用的部隊。
二、綠營軍器與19世紀中期的四川攻城戰斗
在太平天國戰爭中,除卻大規模的野外會戰之外,交戰雙方的許多重要戰斗,往往發生在擁有城墻工事的城市附近。如太平軍攻取全州、長沙、武昌,以及擊破清軍江北、江南大營的戰斗,還有之后湘軍攻擊安慶、天京等役,都是圍繞城池或營壘工事進行的攻防作戰,而重要城池的得失,又往往能夠決定戰略大局的走向。如此眾多的攻守城戰役的產生,客觀上固然是因為地域上長江沿岸地區人口繁密,城池眾多,而在軍事的角度上,則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的中國城墻高大敦厚,而太平軍及湘軍所裝備的劈山炮、五子炮等黑火藥火炮對堅固工事毀傷效果不佳[15]。另一方面,也是由當時交戰各方依據其裝備的武器而選擇的戰術所決定的。湘軍統帥曾國藩曾經說:“賊來尋我,以主待客也。客氣先勝而后衰,主氣先微而后壯。”[17]其中所謂“主”且“待客”的,即是一般戰術意義上的防御方,而“客”則是進攻方,防御方預先占據了戰場的有利位置,并且可以利用進攻發起之前的時間排列陣形、修筑簡易工事,這段時間越長,準備工作越充分,士兵也就更加具有信心,這便是“先微而后壯”。進攻方則往往需要在遠程武器射程之外展開,并且通過戰術上的沖鋒來快速通過遠程武器的打擊范圍,將對手逼入近身作戰當中。進攻方士兵在沖鋒過程中不單在心理上將勇氣發揮到最大,生理上亦因為發起沖鋒的長距離奔跑而完成了“熱身運動”,其體能也到一個極致的狀態,較之堅守在原地、身體尚未充分展開運動的防御方士兵而言自然更具優勢,這即是所謂“先勝”。沖鋒完成之后雙方進入近戰,這時若防御方未能因為沖擊的殺傷而動搖,而攻擊一方的氣勢又漸漸消退,這即是“后衰”,正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雙方膠著越久,攻擊的一方便越難以取勝。因此,曾國藩總結道:“故善用兵者,最善為主,不喜做客。”由他率領的湘軍在作戰之中,也經常采用預先占據陣地的防御反擊和伏擊的戰術,其具體戰術意圖一般是先使用火器和遠程冷兵器盡量削弱敵軍,逼迫其陷入“要么快速發動沖鋒進入勝算難料的近身戰斗,要么便在火力打擊下先行崩潰”的兩難選擇之中,然后再選擇合適時機發動反擊[4]。
盡管綠營軍隊在武器裝備上有所改善,但他們既不如湘軍那樣尚有較強的組織力度,亦不可能像太平軍一般有著摻雜著樸素民族主義情感的狂熱,于是更加依賴城墻一類的現有工事作守城作戰。如咸豐十一年(1861)的營山縣攻守城戰斗,交戰雙方圍繞著城墻反復爭奪,動用了鳥槍、火炮、地雷及火箭等武器。據同治九年(1870)刊刻的《營山縣志》記載,在咸豐十年(1860)冬天,由于云南李永和、藍朝鼎農民起義的影響,當時的知縣濮文一方面“督同紳民晝夜監修”趕造城墻,一方面也“練鄉團,募丁壯”,希圖整備軍械,以防御農民軍攻打。然而,不待營山縣城墻完全竣工,李永和部便于次年(1861)十一月壓境而來,其時李部“先攻岳池不下,知營邑城工未完,遂謀潛襲。”而駐守營山的綠營把總向陽春“在防偵知”,遂先行趕回縣內進行布置。十一月初四,義軍先鋒李洪春統領“紅衣賊萬余人蜂擁而來,直薄西門城根”,把總向陽春乘其不備,“手大銃擊之,立斃洪春,賊始卻。”按縣志中此條目題為“賊黨李洪春薄城把總向陽春炮斃之”,再考慮到之后十一月初六農民軍三面圍城,又“伏數千人于北門楊姓宅內”,城中“以大銃擊之,轟折瓦屋,壓斃紅衣賊十余人”,則這種“大銃”在威力上足以擊塌房屋,亦可以殺傷人員一類的軟目標,雖然其具體形制未有記載,但其性能大略同綠營軍使用的五子炮、劈山炮相近。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營邑城墻未能修筑完工的部分,縣志載為“城無腰墻垛口”,所謂腰墻、垛口,即建在城的基礎夯土墻體上,作為掩體而為防御者提供遮蔽的矮墻,按光緒年間《順天府志》所載,當時京師外城墻“應厚二丈,收頂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磚為腰墻,基應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18]營山縣城池自然不能如同京師一般高大,但其腰墻位置及筑城比例應當與之相近。為了解決城池有墻而不能使得占據其上的防御者藏身掩蔽的情況,城中“旋運各街階石堆砌,上安木板箱,實以土石為垛,內豎板。”即將街道上的石板堆砌在墻基之上,又用填充了土石的木板箱作為垛墻,由此使得巡防之人“始有障蔽而無懼心”[19]。
十一月初八日,農民軍正式展開攻城。其前隊以竹子為原料編制籬笆,“狀如藤笠,人各一頂,以御炮矢。”手持長矛、云梯等兵器的戰士跟在籬笆之后,乘著夜色攻擊城墻,城中防守方則“伺賊將來時,詭呼火藥已完,速赴大局取來,勿遲勿遲。”誘使農民軍發起攻擊后,再以“鳥銃并擊,斃賊數十人”。可以看到,火藥兵器在戰斗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對于攻城方而言,即使制作了簡易的盾牌器具,亦不敢直接面對鳥銃、大銃的炮火,而只能夠“乘夜撲城”,防守一方則沉著冷靜,以詐術騙取攻方士卒“爭涌至”,方開槍射擊。而若從軍器的角度來說,則鳥銃火器在當時戰場上的威懾力顯然是較大的,但在上述記載中,這類武器的弱點也相當明顯:一來其耗費火藥量大,裝填不易,而使得城下的農民軍在得到“火藥用完”的錯誤情報后,敢于迅速涌入城內。二來則是其在準確度和射程上亦不盡如人意[19]。
除去嘗試傳統的云梯登城之外,農民軍亦使用過類似于湘軍攻擊天京的掘進攻城戰術。對此,城中守軍的應對方法是“扎木城,深內濠”,即在城池周圍建筑簡易的木質塔樓,并且挖掘壕溝。至于農民軍安設的攻城地雷,城內守軍則“縋勇伏濠,挖通地雷,灌以糞水”,使其火藥信捻失效。可惜守軍在挖掘時疏漏一處地雷未能清理,使其得以“于二十一日夜四鼓后轟發,聲撼山岳,瓦石皆飛”。與此同時,城外農民軍“各手云梯一架,蟻附而登”,守軍亦以槍炮還擊,雙方交戰直至天明,攻城農民軍見久不能得手,方才退兵,而城內已然到了“婦女皆運石助戰死拒”的地步。之后農民軍亦嘗試以竹草填壕,門板護身攻擊城墻,而為守軍火箭火彈燒退[19]。
營山縣守城的戰斗從當年十一月初四開始,一直持續十二天,盡管其戰事規模并不很大,但攻守雙方使用的兵器、戰術卻極其眾多。在兵器的使用上,農民軍一方仍然以大量的冷兵器為主,而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其挖掘地道、埋設地雷的作戰方式。事實上,土工掘進一向是中國傳統的攻城手段之一,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這類手段也經常出現,除去湘軍攻擊天京的戰斗之外,鮑超、多隆阿軍攻擊安慶時,因攻城不利,便“開挖地道,潛運火藥,其中定期五日內轟城”[20]。金國琛在孝感、德安作戰時,也曾因為“賊眾尚堅韌死守”而“分挖地道,轟城屢坍”[13]。太平軍方面亦在圍攻常昭城行動中,先因大炮轟塌城墻而未能攻克,轉而“潛在相近河岸開挖地道。”[21]咸豐二年洪秀全率軍攻擊長沙時,也曾“偷挖地道三次,轟陷城垣數十丈”[22]。盡管如此,從實際效果來說,挖掘地道進行攻城卻又更像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后手段。營山縣的攻城戰斗中,農民軍裝備瓠敗,卻依舊先嘗試依靠云梯攻擊城防,在攻城失敗后才轉而采取掘進。清軍、太平軍之間進行的較大規模攻守城戰時,也往往先以其他方式攻城,直到最后才用挖掘之法,即便展開挖掘,亦需要“一面籌挖地道,一面仍當拼力進攻,勿徒恃有地雷轟擊,復蹈從前呂公車等覆轍”[23]。除此之外,就算地道地雷等成功轟塌城墻,亦不代表攻城方即可順利入城,如前述太平軍攻擊長沙時已經以地雷擊垮城墻得手,卻仍然遭到清軍“竭力堵住,立時擊退”[22]。這些記載表明,至少直到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為止,中國本土的火炮及其他攻城技術,都還不足以取得對傳統的要塞式城市防御工事的絕對壓制。一般而言,防御方若能依靠工事,強化火力,“多用大炮,百發百中”,則自然可以收到“賊便不敢再來窺”的效果[24]。于是,時常居于防守地位的綠營軍及各地方的團練部隊,對鳥槍等遠程火藥武器的愈加青睞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小結
中國在19世紀40年代之后的數十年間所遭遇的各種戰爭,促使軍事技術“井噴”式地爆發性發展。通過分析晚清時期四川綠營軍的軍器種類、性能和實戰效果,可以發現,雖然更多還是在傳統軍事經驗中尋求幫助,但西方武器的影響已經可以見諸于軍隊的各個方面。
參考文獻:
[1]茅海建.天朝的崩潰[M].北京:三聯書店,2014.
[2]羅爾綱.綠營兵志[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3]歐陽泰.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4]趙魯臻.危機下的變革:晚清陸軍戰術及訓練研究——以湘軍、淮軍與新建陸軍為中心的討論[D].天津:南開大學,2014.
[5]陳平.四川綠營兵研究——以貫徹安民政策為中心[D].昆明:云南大學,2009.
[6]翁同爵.皇朝兵制考略[M].清光緒刻朱墨套印本.
[7]鄧存詠.龍安府志[M].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8]阿桂.蘭州紀略[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劉啟端.大清會典圖[M].清光緒石印本.
[10]陳龍昌.中西兵略指掌[M].清光緒東山草堂石印本.
[11]焦勛述.火攻挈要[M].清海山仙館叢書本.
[12]鄧仁垣修,吳鐘.會理州志[M].清同治九年刊本.
[13]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M]清同治群玉齋活字印本.
[14]陳龍昌.中西兵略指掌[M].清光緒東山草堂石印本.
[15]丁日昌.海防要覽[M].清光緒敦懷書屋刻本.
[16]張德堅.賊情纂[M].清鈔本.
[17]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M].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增修本.
[18]張之洞.順天府志[M].清光緒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19]翁道均修,熊毓藩.營山縣志[M].清同治九年刻本.
[20]陳昌輯.霆軍紀略[M].》,清光緒八年刻本.
[21]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M].民國景金陵原刊本.
[22]蕭盛達.粵匪紀略[M].羅爾綱藏本.
[23]王先謙.東華續錄[M].清光緒刻本.
[24]錫檀修,鄧范之.通江縣志[M].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