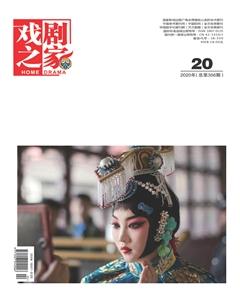越劇老旦藝術的現景與愿景
俞巧萍
【摘 要】在越劇舞臺上,老旦行當的劇目比較匱乏,優秀人才也相對比較匱乏,主要是因為越劇藝術學校、越劇表演培訓機構對老旦行當的漠視,越劇老旦沒有一套系統規范的表演套路,劇團領導對老旦演員的栽培力度不夠等。而通過招生培養、業務戲的開拓、戲曲組織的再培養以及新戲創作等多個途徑的協同合作,有望改善越劇老旦行當青黃不接的不利局面。
【關鍵詞】越劇;老旦;行當;繼承
中圖分類號:J82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19-0025-02
2019年盛夏,為了展現近年來江、浙、滬、閩等地越劇青年演員培養成果,促進青年藝術家的誕生,由江蘇省戲劇家協會、浙江省戲劇家協會、上海市戲劇家協會和福建省戲劇家協會共同參與指導的《越美中華——越劇青年演員大匯演》盛大開賽,我有幸進入了復賽。進入復賽后,我是喜憂參半:喜的是難得有這么好的平臺來展現自我,還可以同其他院團的各位選手相互切磋學習;憂的是作為越劇行當里的配角老旦,劇目比較匱乏,選擇合適的劇目參賽真是不小的困擾。不得不承認,如何規范運用唱念做打來塑造各種老旦角色和如何創作新的劇目來豐富老旦的舞臺藝術風采,是我們青年越劇老旦演員面臨的群體性困惑。
一、越劇老旦藝術的現景
在上世紀“越劇十姐妹”鼎盛時期,越劇界曾涌現了像周寶奎、金艷芳、魏蘭芳等優秀的越劇老旦表演藝術家,她們也為廣大觀眾呈現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角色,如《紅樓夢》中的賈母、《碧玉簪》中的陸氏、《珍珠塔》中的方朵花、《孔雀東南飛》中的焦母、《血手印》中的林母等等。隨著這些老藝術家相繼離開舞臺,越劇老旦行當便逐漸陷入了低迷狀態。許多院團為應對和扭轉老旦青黃不接的局面,便采取了用其他行當演員來頂演老旦角色的做法。越劇界一直有老生演員出演老旦角色的傳統,像張桂鳳、鄭忠梅等越劇老生表演藝術家都曾兼演過老旦角色,而如今的越劇界以老生來頂演老旦的情況更是俯拾皆是,像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老生演員董柯娣在《西廂記》中飾演崔夫人,溫州市越劇團的老生演員鄭曼莉在紹興演藝公司版《紅樓夢》、《西廂記》中出演賈母、崔夫人,上海越劇院的老生演員章海靈在《真假駙馬》、《玉簪記》、《孔雀東南飛》等劇中出演老旦角色等。而像盧灣越劇團的張小巧和浙江越劇團的屠笑飛,這種以丑行來串演老旦的傳統也是沿襲至今。此外,在越劇舞臺上還出現了某些小旦演員中年之后開始轉至老旦行當的情況,如浙江越劇團的周云娟在《楊乃武平冤記》中飾演夏母,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洪瑛在《陸游與唐琬》中飾演陸母等。
雖然上述這些老師在舞臺上把老旦角色也都塑造得很成功,但是越劇老旦演員缺失的問題依然持續存在。而且老旦行當繼承與發展的問題,已經顯而易見地擺在了越劇舞臺藝術發展的面前。老生演老旦,盡管有氣勢,也有分量,卻缺少了老旦那種母性的慈祥感,臺步也過于生硬,少了些許柔美。而丑角來反串,其實更多適用于一些彩老旦,如《碧玉簪》中的陸氏、《紅絲錯》中的張母等,而對于一些有身份的、上了年紀的蒼老旦,非正規老旦往往難以駕馭,除非這位演員已經擁有對任何年紀段的老旦角色都游刃有余的實力。還有些小旦演員來反串的,往往容易缺乏年齡感,不夠深沉。因而,對于越劇老旦演員的培養,已是一個十分值得深思與探究的重要課題。
中國戲曲是一門博大精深的藝術,在舞臺上為了體現各種性別、年紀、身份的角色,創造了生、旦、凈、丑這些行當。每個行當都有自己的表演和聲腔特色,使我們戲曲舞臺絢麗繽紛,百花齊放。所以,戲曲演員的培養絕對是重中之重,那么為什么越劇老旦會如此缺乏優秀人才,越劇老旦的經典片段又為何如此匱乏?簡而述之,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各地越劇藝術學校及越劇表演培訓機構長期以來對老旦行當的漠視。眾所周知,越劇以小生小旦、才子佳人戲為主,因而這些越劇人才培養單位往往以是否適于小生、小旦來決定演員培養,并以此為依據而分成兩大類,即小生組和小旦組。等到學習了一定時間后,那些經過培訓后被認為不太適合小生、小旦的學員,如唱腔不夠成熟或身高形象不盡人意的,則相繼分為老生、小丑,最后才派發去學習老旦,這也是越劇老旦在各方面往往不夠優秀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學員進入劇團之后開始擔綱一些角色時,雖然很多戲里都有老旦角色,然而老旦的戲份往往不重,而且越劇老旦本身沒有一套系統規范的表演套路,一些駐團技導和一些年長的演員老師也只是用她們自認為準確的、合理的表演方式來教授,加之又缺乏在戲中擔綱重要角色的歷練,因而老旦的訓練機會相當有限。所以,在從學員成長為正式演員的過程中,老旦演員的表演技藝也往往難以提升。
此外,即便隨著老旦演員的慢慢成長,她們對自己飾演的角色逐漸有了相對準確的理解,不少劇團領導仍會忽略對這些老旦演員的培養,認為越劇就是要培養小生、小旦,老旦演員再優秀也往往被忽略,只能演一些配角,像專門排演折子戲或送去進修學習的機會是少之又少。
二、越劇老旦藝術的愿景
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改變上述現象,使越劇老旦行當盡量規范、輝煌起來,是值得所有越劇人深思的。現在的越劇舞臺是多元化的,在劇本創作、音樂設計、舞美體現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飛躍,觀眾對舞臺上各種演員、各個行當的需求也越來越內行。解決越劇老旦行當面臨的上述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嘗試從以下幾點來入手:
(一)從藝校招生培訓開始,一定要把老旦行當的名額列在計劃內。挑選嗓音渾厚、身形俱佳的學員,從入學開始就要系統規范地學習老旦發聲、臺步、身段等。如果缺少師資,可以去京劇或昆曲等其他兄弟劇種聘請在老旦行當有完善的培養系統的老師來教學,也可以采取定向培養方式,打破劇種和地域局限,送到更加專業化的院校專門跟班學習,取其精髓,來改善我們越劇老旦行當沒有規范的培養大綱的不足。
(二)對于在各院團的青年老旦演員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學習一些有老旦基本功的折子戲來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不能陷于“老旦大花臉,吃飯拿工錢”的誤區,而要樹立起“行行出狀元”的信心,讓自己在舞臺上的形象更生動、豐滿。在現有的越劇老旦折子戲劇目中,改編自京劇的劇目《八珍湯》里的《風雪街頭》,還有2007年俞珍珠導演創排的《目連救母》中的《滑油山》都是鍛煉老旦演員唱腔等各方面基本素質的折子戲,還有京劇《罷宴》也是一出對表演、唱腔都要求很高的折子戲,我們青年演員都可以借鑒來排演,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
(三)經常開辦一些對各院團青年人才的“回爐”培訓,如“新松計劃”研修班,請來全國頂尖的老師給青年演員上課,讓我們這些已經在舞臺上積累了一定演出經驗的成熟演員再來接受一些更高層次的學習,使我們能獲得“質”的飛躍。我對此深有體會,在2014年“新松計劃”研修班上,京劇老旦名家袁慧琴老師傳授老旦名段《對花槍》,這出文武兼備的戲對于越劇老旦而言有很大的挑戰,但是我覺得對成熟演員來說,學習一出大難度的戲讓自己在各方面都有大的提高,并能學以致用,不斷開拓自己的戲路,正是我們的表演生涯中所需要的。
(四)在各種越劇大戲創作中,對于老旦的唱腔部分,要敢于打破局限,嘗試用各種曲調及風格來豐富老旦的唱腔,更加生動、準確地塑造老旦行當在各種戲中的人物形象。譬如在本中心2002年創排的歷史劇《蔡文姬》中,作曲陳鈞老師獨具匠心地運用了越劇老生表演藝術家吳小樓的流派唱腔特點,將其融入到了我所飾演的老阿婆一角中,并加入了草原呼麥的元素,使一個世代看守昭君陵園的漢家阿婆形象瞬間豐滿了起來。
戲曲要繁榮,我們青年演員肩上的任務很重。老旦作為戲曲行當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在越劇舞臺上也應該有其發光發亮的地方。正如前蘇聯著名戲劇家斯坦尼拉夫斯基所說的:“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我相信,通過我們越劇人的不懈努力,越劇老旦在將來的舞臺上一定也會越來越輝煌,成為閃亮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