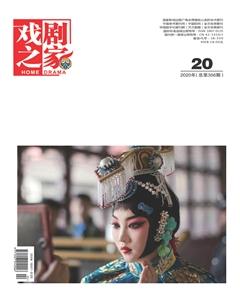主旋律電影中英雄人物的流變
蘇安琪
【摘 要】主旋律電影“影以載道”的特點與藝術性、商業性的沖突長期存在,而新時期的主旋律電影聚焦于創作觀念、創作方式進行探索與調整,實現了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講好了“中國故事”。本文聚焦于人物塑造,通過梳理主旋律電影中英雄人物的流變,探討主旋律電影在市場壓力下如何有效傳播主流價值。
【關鍵詞】主旋律;電影人物;人物塑造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20)20-0118-02
“主旋律”一詞來自音樂,是指在一部作品中再現或變奏的主要樂句、音型,在整個作品或樂章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主旋律”之于電影,是一種特殊的存在。鄧小平將主旋律電影簡單概括為:“一切宣傳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電影”。在電影市場多元化的今天,主旋律電影在國產電影的版圖中占據重要的位置,進一步被定義為“體現官方意識形態導向的電影作品”。這就要求主旋律電影不僅要融合電影本身的藝術性與商業性,還要有獨特的“影以載道”、價值倡導的特點,這兩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矛盾的。長久以來,主旋律電影的實際創作受到許多的限制,人們一想到主旋律電影就會談到“假大空”,甚至還有“手撕鬼子”、違反“牛頓定律”等笑話。
“主旋律電影”也曾被認為是沒有市場“錢景”的。而2019年國慶檔電影票房達50.49億,其中三部主旋律電影就占了97%,更不用說中國電影史上票房第一的現象級主旋律電影《戰狼2》(2017)了。一個顯著的變化在于,首先是電影,然后才是主旋律電影;進一步看,首先是類型電影,然后才是主旋律電影。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快速轉型的大背景下,新時期的主旋律電影還是能在創作觀念、創作方式上進行探索與調整,實現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講好“中國故事”的。本文將通過梳理主旋律電影中英雄人物的流變,探討主旋律電影在市場壓力下如何有效傳播主流價值。
一、從“大英雄”到“小人物”
以往的主旋律電影選題宏大,突出政治主流意識形態。其一是展現重大歷史事件類,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內容是講述一系列英雄人物在歷史發展中起到的推動作用。因人物眾多、體量龐大,創作中缺少對英雄人物心路歷程的刻畫,而天然賦予他們保家衛國的大情懷,這使得主旋律電影在觀眾心里留下了刻板嚴肅的印象,大大降低了主旋律電影的傳播力度。其二是人物傳記類,如《孔繁森》、《楊善洲》等,人物臉譜化、扁平化現象突出。電影《焦裕祿》中焦裕祿忍著肝癌的病痛在治理“三害”第一線堅持工作,是對絕對“英雄人物”的塑造和歌頌;而與之相對的吳縣長漠視生命,極其冷血。歌頌與貶低涇渭分明,使得主旋律電影說教意味過于濃重,難以被大眾所接受,主流價值傳播大打折扣。
新時期的主旋律電影卻摒棄了傳統電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模式,轉而著眼于平凡人物的塑造。從“大英雄”到“小人物”,選角的轉變不僅不受歷史人物原型的限制,充分提供了創作空間,還有益于引發共鳴。《我和我的祖國》中描寫了許多不同時代的平凡人物,他們中有意外獲得奧運會門票的出租車司機、有備飛的女飛行員、有荒野中游手好閑的兩個小伙子,甚至還有一名普通的小學生。以本片為代表的新時期主旋律電影采用輕松的風格呈現出時代浪潮中的小人物平凡樸實的生活故事,而平民化的視角又加強了觀眾對歷史的體驗感與親切感,電影想要傳遞的意識形態也能更好地被觀眾感知和接納。
二、從“外部沖突”到“內部沖突”
早期的主旋律電影中,傳統的英雄形象是十分理性的,甚至是具有了完美主義人格。《平原游擊隊》的開篇便是英雄李向陽為了趕到司令部去接受一個緊急任務,毫不猶豫地帶著同伴在槍林彈雨中穿行。把人物置于這種特殊的險境,在不尋常的外部沖突中凸現他的英雄性格,是傳統主旋律電影慣用的手法。但難免會讓人產生“主題先行”的不適感,因為此時電影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邏輯取代了人物自身的行為邏輯。
而新時期的主旋律電影,不僅用強烈的視聽效果對外部沖突進行營造,更著眼于人物的內部沖突。例如《明月幾時有》以上世紀40年代香港淪陷為背景,講述以傳奇女性方姑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熱血抗爭的故事。這里的英雄人物方姑不僅僅是有從文弱教師到熱血女英雄的轉變——類似這樣的人物身份轉變,在經典主旋律電影中已經出現太多了。作為女性導演,許鞍華還細膩而又冷靜地刻畫了方姑處于戰火硝煙中的特殊情感——在與李錦榮的愛情和與劉黑仔的戰友情中慢慢成長,內心從迷茫到堅定。方姑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就確立起來了。類似的還有《戰狼2》中富二代卓亦凡從玩世不恭、意氣用事最終成長為鐵血漢子;《紅海行動》中抗壓能力弱的觀察員李懂逐步建立自信,在千鈞一發之際最終一槍致勝。
由此可見,新時期的主旋律電影在人物塑造上都不是聚焦于外部沖突,而是以內部沖突的解決來彰顯人物的成長,更為真實感人。
三、人物視野的擴大
因為主旋律電影要對當下的社會主流價值觀進行精確反映,要符合、呼應當下國勢和民心,所以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影響和制約著電影的創作理念。從電影主題和人物行為本身來看,主旋律電影英雄人物的視野是不斷擴大并且分為三個階段的。
(一)有“民族意識”而無“世界情懷”(1949—1978年)
最早的主旋律電影受到冷戰思維困擾,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斗爭意識和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例如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鐵道游擊隊》(1956)、《地雷戰》(1962)、《小兵張嘎》(1963)和以抗美援朝戰爭為題材的《上甘嶺》(1956)、《打擊侵略者》(1965)。此間的主旋律電影多是展現著名戰役,英雄人物的行為目標只有一個——保家衛國,帶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
(二)“世界情懷”的逐漸顯露(1978-2012年)
改革開放時期,外交政策的調整使得中國外交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敵友觀念逐漸淡化,由以前側重與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友好關系轉變為與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普遍發展友好關系。處在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電影中的人物開始思考自己與世界的關系。
馮小寧的電影《紫日》(2001)三位主角分別是中國人、日本人和蘇聯人,他們拋開人物身份和國家背景的差異,由對立走向相互理解。沒有以往抗戰電影的強烈主觀性,此時的英雄人物沖破戰爭仇恨與狹義的民族主義,主動思考戰爭給世界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值得注意的是,馮小寧“戰爭與和平三部曲”(《紫日》、《黃河絕戀》(1999)、《紅河谷》(1996))的主人公都有類似的組合模式,但最終都是以悲劇收場。可以看出此時的英雄人物雖然擁有了一定的世界視野,但力量還是十分渺茫的。這也是此時中國客觀的經濟政治狀況以及國際地位所決定的。
(三)“世界情懷”的充分展現(2012—至今)
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中國力求構建一個持久和平、合作共贏、開放包容的世界,這就要求新時期主旋律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不僅要有宏偉的世界視野,還要在行動中展現中國力量。
例如《紅海行動》(2018)中爆破手徐宏沖進槍林彈雨解救外國平民,表現了他無差別地對待每個國家的人,是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從《戰狼1》(2015)到《戰狼2》(2017),冷鋒的行動由國內到了非洲,在異國他鄉救死扶傷,還收養了非洲兒童。這些都是新時期主旋律電影英雄人物視野擴大的體現——堅守“民族意識”的同時,也漸漸培養了“世界情懷”。
四、結語
從“大英雄”到“小人物”,從“外部沖突”到“內部沖突”,再到人物視野的擴大,在梳理了主旋律電影中英雄人物的流變后我們可以看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到主旋律電影傳播主流價值的廣度和深度。而面對瞬息萬變的時代環境,主旋律電影各方面的優質創新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