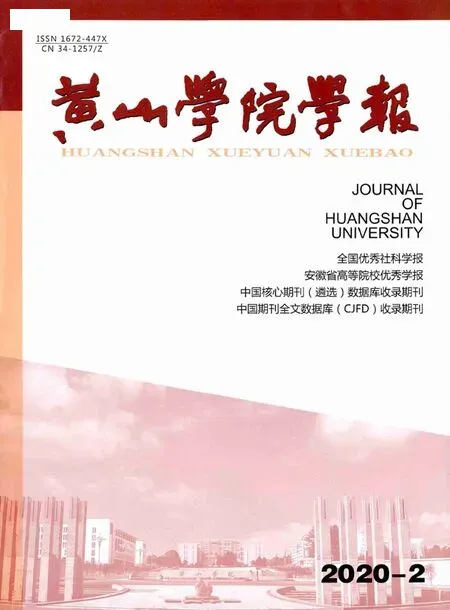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外譯體系的生態學視角研究
陳圣白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湖南 長沙410205)
一、引 言
建設“一帶一路”偉大構想是推進“四個全面”、落實“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重大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千多年中西交往歷史證明了——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由此可見,“一帶一路”的提出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對外文化傳播是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實施的基礎和保證,文化先行可積極推進我國政治、金融、貿易、設施和民心“五通”的協調發展,并能促進“一帶一路”的逐步有序發展。“一帶一路”背景下,在中華民族文化逐步融入世界和國外文化逐漸融入我國的互動格局中,如何有效實現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與研究的重要問題。
由于中國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遺產、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負有盛名的傳統技藝和民間藝術,致使中國民族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提升。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中國民族文化要凸顯自身獨有的文化特色,傳遞讓人崇敬的民族精神,體現民族文化的寶貴價值,必然需要重視文化外譯的關鍵作用。在民族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只有進行有效的文化外譯活動,才能完美傳遞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內涵。因此,結合我國“一帶一路”倡議,以生態翻譯學為理論指導,探討“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外譯體系研究,使民族文化元素快速融入到世界不同文化環境中,從而形成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和諧共處,優勢互補,實現人類文明的完美融合和共同發展。
二、“一帶一路”背景下相關研究現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帶一路”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一帶一路”是促進中國和沿線各國共同繁榮昌盛之路,是實現中國和沿線各國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之路,是倡導不同國度不同文明和諧包容和和平對話之路。在國家定位轉變的新形勢下,我國國家外語能力建設必須在資源質量、戰略導向、資源種類和能力需求四個方面轉型,并提出需要加強外語規劃和服務于“一帶一路”的對策[1]。全球化外語教育發展的趨勢就是構建和實施多語種的外語教育政策,這將強有力地促進“一帶一路”的建設,加快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2]。“一帶一路”建設的民心工程、基礎工程和先導工程就是要強調語言文化融通;只有通過語言文化交流,才能為各國的政治對話與經濟合作創造有利的條件,才能探尋出各國家在利益和文化方面的契合點,才能促進各國文化互鑒和彼此認同,才能夯實民意基礎并增進各國彼此間的了解與友誼[3]。“一帶一路”的現實問題與文化理論要從加強文化傳播、凝聚價值共識到深化經濟交往、鞏固利益共同體入手,既要“走出去”又要“走得巧”,旨在更好地發揚當代中國文化,適應世界文化發展潮流,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帶一路”的實施就是構建基于戰略選擇及其路徑實現的文化傳播與交流合作機制,并通過機制化的手段使文化傳播與交流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得以提升,這也是更好地實現并維護“一帶一路”利益共同體的有效方式[4]。眾所周知,翻譯的本質就是跨語言、跨文化的對外傳播活動。20世紀60年代國外學者就已將傳播理論與翻譯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如英國學者羅杰·貝爾認為翻譯過程包括九個模塊:源語信息接收、識別、解碼、獲取、理解、選擇、編碼、傳播與目的語接收。美國學者Montgomery 也將跨文化傳播與翻譯結合進行了大量研究[5]。而國內最早提出對外傳播翻譯的學者是沈蘇儒教授。學者羅選民則探討了翻譯與對外傳播的關系,強調了翻譯在對外傳播過程中的重要性[6]。孫英春學者提出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應突出地方文化在對外傳播中的重大作用[7]。總而言之,國內外學者都將對外文化傳播和翻譯結合進行了相應研究,但缺乏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民族文化對外傳播中的外譯體系的探討。
鑒于此,“一帶一路”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趨勢,為民族文化對外傳播帶來了廣闊的戰略視野并指引了發展方向。文化外譯在民族文化對外傳播中起著橋梁和紐帶的作用,是決定民族文化對外傳播效果的關鍵因素和首要條件。民族文化如何走出去,能走多遠,從真正意義而言取決于翻譯的質量和傳播的效果。與此同時,生態翻譯學是一個“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范式,是一個從生態學視角、運用生態理性對翻譯進行綜觀的全景性研究,其具備典型的跨學科性質[8]。因此,依據生態翻譯學從新的視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對民族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的外譯體系展開研究,不但極大地豐富了對外文化傳播中外譯體系的理論研究,而且通過構建外譯體系運用其機制并選擇其路徑對民族文化進行研究,也能更好地提升其傳播的效果,更真實地向世界傳遞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魅力。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外譯體系的構建
基于“一帶一路”的背景,隨著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重要,民族文化對外傳播刻不容緩,構建科學有效的外譯體系重要而關鍵。以生態翻譯學為理論依據,從跨文化傳播視角提出民族文化外譯體系,從微觀、中觀及宏觀三個維度進行研究。微觀外譯研究主要是外譯的本體研究,如外譯過程、外譯本質及外譯標準等;中觀外譯研究主要是從“生態美學”“適應與選擇”“適者生存/汰弱留強”“譯者責任”四個方面研究譯者角色;宏觀外譯研究主要研究外譯目的、外譯生態環境與譯語受眾需求等(見圖1)。三維一體的“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外譯體系的構建旨在使譯文化境傳神,最終實現民族文化有效傳播的目的。

圖1 民族文化外譯體系的建構
(一)微觀外譯研究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微觀外譯研究主要是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對外譯進行本體研究,重新對民族文化外譯的過程、外譯的本質以及外譯的標準進行詮釋。基于生態翻譯學理論,民族文化外譯的過程就是譯者適應外譯生態環境的選擇過程,是外譯活動中譯者適應性選擇和選擇性適應的過程。民族外譯過程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止不變的,是譯者對以原文語篇為生態要件的外譯生態環境的多維度適應,同時也是以譯者為生態要件的外譯生態環境對目的語譯文的多維度選擇。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民族文化外譯過程不僅僅是簡單的語言選擇過程,更是一種源語與目的語雙語轉換活動中多維度、多層面的復雜動態的選擇過程, 其不但具有翻譯過程的所有特點,而且還具備民族文化外譯活動自身的選擇特性,呈現出跨學科性的特征。基于此,依據生態翻譯學理論,民族文化外譯的本質就是以譯者為主導,以“傳意傳神”為核心,譯者實施外譯生態環境的動態適應與譯者對以外譯生態環境為典型生態要件的多維度選擇過程。隨著翻譯學科的不斷發展,翻譯的本質可以從多維度和多層次來進行闡釋,翻譯標準也呈現出多元化。民族文化外譯的標準就是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譯出“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而“整合適應選擇度”就是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適應”的程度和繼而依此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8]。關于外譯過程、外譯本質和外譯標準等方面的外譯微觀研究是民族文化外譯體系研究的基礎,同時也為中觀研究和宏觀研究提供理論支持。
(二)中觀外譯研究
“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對外傳播中的外譯中觀研究主要是關注譯者角色研究。譯者是譯文產生的重要元素之一。在民族文化對外傳播中,譯者在外譯過程中處于各種語言和各種文化相互交織的語境之中,既是確保文化外譯過程成功進行的決定者,又是文化外譯過程中的真正主導者。因此,譯者在民族文化外譯過程中要充分發揮主導性,正確處理好翻譯生態環境下的雙語語言與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確保外譯過程的順暢進行,并構建和諧健康的翻譯生態系統。鑒于此,中觀外譯研究主要從生態翻譯學中的“生態美學”“適應與選擇”“適者生存/汰弱留強”“譯者責任”等四個方面闡述譯者在外譯過程中的中樞地位和主導作用,建構出民族文化外譯體系中的譯者主導模式(見圖2)。

圖2 民族文化外譯體系中的譯者主導模式
民族文化外譯體系中的譯員主導模式指出譯員是整個模式的主導,而語言1、多維選擇性適應和多維適應性選擇、語言2 在譯者的主導下構建出一個三角循環的民族文化外譯過程。從“生態美學”而言,譯者始終應在原文理解釋義中保持精準美,在譯語選擇和輸出中保持邏輯美和差異美。因此,民族文化外譯是一種難以完美的藝術,是富有生態美的一種動態開放的交際活動。從“適應與選擇”而言,在民族文化外譯的過程中,譯者應適應于民族外譯的生態環境,并從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個維度選擇“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基于“適者生存/汰弱留強”的生態法則,譯者在民族文化外譯生態環境中應發揮主導作用進行多層次、多方面的適應與選擇,從而使譯文能被譯語讀者所接受并在譯語國家“生存”下來。在民族文化外譯過程中,“譯者全責”制要求譯者要協調處理好原文作者、譯語讀者、出版商、文化輸出國和文化接受國等多個生態群落之間的關系,使譯文符合外譯規范。
(三)宏觀外譯研究
民族文化外譯的宏觀外譯研究主要從外譯的目的、外譯的生態環境和譯語接受者等方面進行研究。民族文化外譯的目的主要包括語言目的和非語言目的。語言目的就是讓譯語接受者通過譯文了解原文語篇所傳遞的內容、思想和文化,而非語言目的則是實現相應的政治目的、經濟目的、交際目的和外交目的等。具體而言,民族文化外譯的政治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的和平穩定與國際地位;經濟目的在于促進國家經濟繁榮發展,國強民富;交際和外交目的則在于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民族文化外譯的翻譯生態環境是原文和譯文所展現的世界,是影響翻譯主體(原文作者、譯者、讀者、外譯發起人、贊助人、出版商、營銷商、編輯等)生存與發展的所有外界環境(社會政治環境、自然經濟環境、語言文化環境等)的總和[9]。民族文化外譯的特殊性決定民族外譯有著獨特的翻譯生態環境,主要包括內部生態環境和外部生態環境。為保證民族文化外譯內部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譯者不但要加強對民族文化生態環境的適應能力,而且也要注重與內部生態環境中的其他翻譯主體的合作共處。而民族文化外譯的外部生態環境指的就是外譯活動所融入的外部環境,如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外交環境和文化環境等。譯者只有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外譯過程中進行適應與選擇,才能建構一個和諧健康、共生發展的民族外譯生態環境。反言之,民族文化外譯的成與敗,民族文化外譯質量的優與劣完全取決于民族外譯生態環境的和諧統一,而民族文化外譯生態環境和諧統一的前提和條件就是民族文化外譯過程中譯者對民族文化外譯生態環境的最佳適應與選擇。
基于生態翻譯學,對譯文“整合適應選擇度”的評價和測定指標之一就是“譯語讀者反饋”。譯語讀者,即譯語接受者,是民族文化過程中需重視的對象,因為他們既是譯文語篇的最終接受者,也將對譯文的生態翻譯系統產生重要的影響[10]。因此,宏觀外譯研究應對譯文接受者的諸多因素進行研究,比如其文化程度、教育背景、思維方式、信息需求和社會層次等。不同社會層次的譯文接受者有著完全不同的需求和期許,譯者應根據研究結果適度地選擇和調整自身的翻譯策略,譯出能為譯語接受者所接受的譯文,完成在譯語生態環境中的民族文化輸出。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構建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微觀、中觀與宏觀三個層面的外譯體系是民族文化外譯研究的核心,其不但對民族文化外譯的實踐規范提供科學有效的途徑,而且進一步深化了民族文化外譯的理論研究。這些都將有效加快民族文化進一步對外傳播,實現民族文化的價值提升,并真正意義地推進我國“一帶一路”的建設。
四、結 語
推動中華民族文化“走出去”是“一帶一路”的核心內容[11]。“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民族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凸顯,民族文化對外傳播也刻不容緩,構建科學有效的民族文化外譯體系至關重要。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為指導思想,以生態翻譯學為理論依據,從全新的視角和開創性的思路實施一個跨學科(對外傳播學、翻譯學、生態學等)的綜合性研究來探索民族文化外譯的過程,并從微觀、中觀及宏觀三個層面來建構民族文化外譯體系的整體框架,旨在提升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效果,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中贏得文化的話語權,使中華民族文化真正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