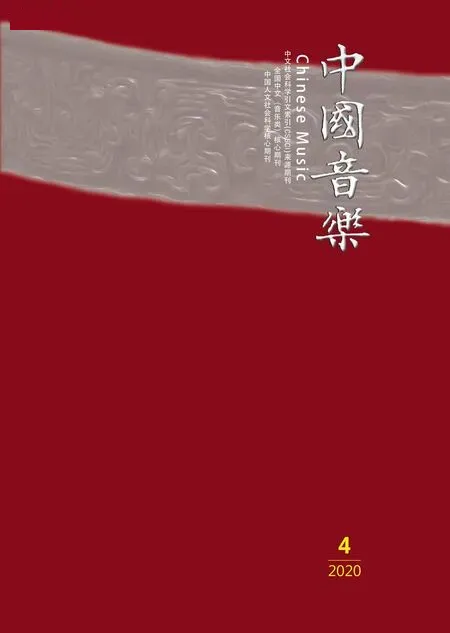石峁初音
——音樂學(xué)、考古學(xué)與語言學(xué)結(jié)出的奇葩(下)
○羅藝峰
三、口簧名稱的語言學(xué)問題
口簧極古,當(dāng)然其名稱也極為悠久。我們不知道石峁人說什么樣的話,但我們知道石峁人一定有語言,為什么?因為要組織、協(xié)調(diào)眾多人員來完成古城的建造,要完成大量物質(zhì)生產(chǎn)和工藝活動,要舉行大型祭祀和原始宗教儀式,要進(jìn)行藝術(shù)性質(zhì)的活動,沒有語言是不可想象的。
口簧名稱的語言學(xué)問題,只能是跨學(xué)科的研究課題。沒有考古學(xué),我們就沒有石峁口簧這個研究對象;沒有音樂學(xué),我們就不能了解口簧的音樂功能與性質(zhì);沒有語言學(xué),我們就難以去思考口簧的傳播及其名稱的歷史演化,進(jìn)而擬測石峁人說什么話及其語言系屬的問題。語言譜系學(xué)研究語言的演化表型現(xiàn)象,強(qiáng)調(diào)“研究語言的起源與分化對理解人類的歷史和文化至關(guān)重要”①金力等:《語言譜系證據(jù)支持漢藏語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起源于中國北方》,自然(Nature),第569卷,2019年5月2日,第112–125頁。,而這正是本文立論的理論基礎(chǔ)之一。
23年前,我曾指出:“樂器名稱的民族語言,可能是一種極為古老而又穩(wěn)定的文化要素,它的內(nèi)涵,可能暗示了使用這一樂器的民族的遷移方向和路線,證明在音樂文化的層面上照見的族源關(guān)系。”②羅藝峰:《口弦源流的歷史語言學(xué)研究》,《中國音樂學(xué)》,1997年,第2期,第21頁。比如,西伯利亞突厥人把舌頭琴(口簧)稱為“Komuz”或“Kumuz”,這與蒙古語的和屬于同一個詞根的詞,就是“咬下唇”的意思,是古代突厥語系的蒙古詞,與即“喉嚨”這個詞有關(guān),其詞根是,引申為用口彈奏、用喉嚨歌唱③策·圖爾巴特等:《考古發(fā)現(xiàn)的舌頭琴與歐亞大陸東部的古代游牧文化》,《銅仁學(xué)院學(xué)報》,2018年,第8期,第26頁。,其含義即是與口唇、下腭有關(guān),正與樂器學(xué)上所謂“Jaws’harp”(“腭琴”或“口琴”)相類,jaw也可譯為“下腭”“咽喉”或“口”,不過有人翻譯為“猶太豎琴”(Jews’harp),卻是錯的,一個字母之誤(a誤為e),惜乎失之千里。
長期生活在中國北方亞歐大草原上的阿爾泰語系民族,其口簧名稱與此多有關(guān)聯(lián)。如:哈薩克族:“哈木斯斯?fàn)柲我馈保℉amusisiernaiyi);柯爾克孜族:“奧孜考姆茲”(Aozikaomuzi);維吾爾族:“埃額茲考姆茲”(aiezikaomuzi);塔塔爾族:“科比斯”(Kobis);滿-通古斯語族的雅庫特人:“柯木斯”(Khomos);索約特人:“克木斯”(Komus)等等。這里的口簧名稱與古老的突厥語對口簧的稱呼Komuz有密切關(guān)系,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塔吉克族的口簧名稱為“庫波茲”(Kubozi),也與突厥語的komuz一致,反映出傳播影響的情況。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雅庫特人口簧名稱Khomos存在雙輔音現(xiàn)象,也就是說,突厥語的ku,可能原先讀khu,存在k、h可以互轉(zhuǎn)的情況,即蒙古語的可以讀ko或,所以,哈薩克族的hamusisiernaiyi,其實就是突厥語的komuz④參見麻赫黙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Kobuz”(“庫布茲”)條。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此意又得到新疆藝術(shù)研究所艾迪雅·買買提博士和內(nèi)蒙古藝術(shù)學(xué)院楊玉成博士的指點,特表謝意。。在歷史上,中國北方民族語言中往往存在雙輔音,后來丟掉了其中一個,甚至受到少數(shù)民族語言影響的古漢語,也存在雙輔音現(xiàn)象,西漢時王昭君的“渾不似”,即:,也有譯為“火不思”的,后來更訛為“渾撥四”,今天西安近郊農(nóng)村還有一種農(nóng)民自制的彈撥樂器叫作“琥珀”,其地方漢語音讀近似Khubo,其實是缺乏尾音的漢語雙聲詞⑤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頁。。這些樂器名稱正是北方草原上的彈撥樂器“庫布茲”,“庫”讀音為“渾”⑥[元]陶宗儀:《輟耕錄·樂曲》:“達(dá)達(dá)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diào)不同。”[明]蔣一葵:《長安客話·渾不似》:“渾不似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相傳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清]洪昇:《長生殿·合圍》:“番姬彈琵琶、渾不是,眾打太平鼓板。”[清]俞正燮:《癸巳存稿·火不思》:“俞玉吾《席上腐談》云:渾撥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也。”,可能原先讀⑦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中國音樂詞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4年,第207頁。柯爾克孜族的彈撥樂器“考姆茲”、哈薩克族彈撥樂器“柯布孜”均屬同類情況。柯爾克孜族和哈薩克族都是阿爾泰語系民族。。
阿爾泰語系諸民族的口簧讀音,其起源極古,反映了民族遷徙和融合的現(xiàn)象,歷史上中國北方草原上有許多民族在這里生息,不論是體質(zhì)的往復(fù)血緣融合還是語言的往復(fù)融合,都非常復(fù)雜。在本文看來,因為石峁人很可能向南發(fā)展,與石峁口簧更有關(guān)系的是亞洲大陸上的漢藏語系民族;與本文相映成趣的是,考古學(xué)家孫周勇更強(qiáng)調(diào)石峁口簧在4000年前從中國北方向歐亞草原的北向擴(kuò)散傳播⑧孫周勇:《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口簧研究》,《文物》,2020年,第1期,第44頁。,其實,一南一北兩個方向的傳播,更證明了“石峁遺址所在的中國北方河套地區(qū)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的觀點。本文則企圖聯(lián)系漢藏語系語言起源問題來討論石峁口簧的可能創(chuàng)造者,從另一領(lǐng)域來介入石峁口簧的起源和傳播問題。
(一)各民族語言口簧名稱
本文擬測,最古老的口簧名稱是來自漢藏語系語言,且在極古時代的中國北方形成。而其名稱演化則主要是在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中。其他語言口簧名稱不排除受到漢藏語言影響的可能。
1.中國漢藏語系藏緬語族:


2.漢藏語系漢語族

3.南島語系印度尼西亞語族

⑨至2019年夏季筆者考察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和爪哇島時,這個樂器的民間名稱還被稱為“gonggong”即“貢貢”,保留了極古的讀音,反映了口簧的傳播。
4.南亞語系馬六甲語族

這些口簧名稱,既有本語族內(nèi)部的不同或相近、相同的樣態(tài),反映出可能同源的關(guān)系,也有跨語系、語族的現(xiàn)象,反映出影響和交流的情況。此處嘗試聯(lián)系“聲”“韻”“調(diào)”的分析,結(jié)合漢藏語系語言的基本規(guī)律來擬測什么名稱最古的可能答案,而不涉及其他語言。這里涉及到的口簧名稱是民族語言名稱的擬音表型。
(二)聲、韻、調(diào)的分析
1.聲
首先,漢藏語系語言里,存在聲母G-K-H互轉(zhuǎn)的突出現(xiàn)象,這是一條重要規(guī)律。我們不難觀察到G-K互轉(zhuǎn)的現(xiàn)象,藏語的口簧名稱Gian,Gao,Kuo,發(fā)生了G和K的聲母互轉(zhuǎn)現(xiàn)象;獨龍族的Gang,也可以讀作Kang或或藏語的Kuo;珞巴族的口簧名稱Gonggong和,也是G和K的互轉(zhuǎn);納西族的Kegu,也當(dāng)然就可以讀如摩梭人的讀音Gugu;怒族的KwuoKwuo,也與Gonggong和可通,甚或可以與說回族的KouKou(口口)讀音相通。另一個重要規(guī)律是聲母G-K和H也可以互轉(zhuǎn),如彝族的Hehe與納西語Gugu、Kegu,中古或上古時期的安多藏語gonggong以及藏南的珞巴語也是可以相通的⑩藏語有三大方言語,即:衛(wèi)藏方言(拉薩話)、康巴方言(德格話、昌多話)、安多方言(甘、青方言),其中安多藏語無聲調(diào),為最古藏語,有重要研究價值和文化史意義。。G-H可以互轉(zhuǎn)這一現(xiàn)象,正如同古漢語中的“蒿”可讀“高”,漢晉時代這個字讀gau1,即所謂“從草高聲”(《說文》),用來表示“草之高者”(陸佃《詩疏》),到唐代卻讀*hɑu,今天我們也讀“蒿”(hāo)。這就反映了真實的古漢語音韻演變,有G-H互轉(zhuǎn)的現(xiàn)象存在。
其次,在漢藏語系語言中,存在k-g-h三個聲母的清濁配對現(xiàn)象,有發(fā)音愈靠后愈古老的規(guī)律。上文藏緬語各族口簧名稱的讀音,除怒族的kwuokwuo帶有kw這樣的復(fù)輔音聲母外,其它均含有k、g、h這幾個單輔音聲母,k是清塞音,不送氣,g是濁純?nèi)簦ú粠П枪谝簦琸-g正是清濁配對,符合藏緬語特征,且都在舌根部位發(fā)聲。而h則是清擦音,送氣,但沒有濁音配對,這也符合本語族特點,發(fā)聲部位在喉。k、g、h三個聲母它們的位置均靠口腔后部,而這正是安多藏語發(fā)音愈靠后部愈古老的規(guī)律。
再次,從清濁配對和轉(zhuǎn)化的現(xiàn)象可知,藏緬語族中有許多口簧名稱是同源詞,使用濁聲母g的口簧名稱反映了最古老的語言規(guī)律。羌語和嘉戎語保留古藏語、羌語原始面貌最多,且都含有k、g兩個單輔音,又可對應(yīng)、互轉(zhuǎn)、濁聲清化,與藏語、普米語、景頗語、彝語有許多同源詞,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參見孫宏開:《羌語支屬問題初探》,載《民族語言研究文集》,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我們可以從以下語言規(guī)律里獲得對口簧名稱研究有意義的認(rèn)識:
清濁聲母對應(yīng)。如:綠春哈尼語gu亅,在碧約哈尼語中讀ku亅,意思是“縫”;濁聲清化。如:哈尼語ga亅,拉祜語讀ka,意思是“聽見”;濁音對應(yīng)濁音、清音對應(yīng)清音。如:彝語gu┤,哈尼語ry亅,傈僳語ku┤,納西語gu┤,藏語dgu,羌語xgue┤,意思是“九”,等等。語言學(xué)家指出,這種對應(yīng)決非偶然,而是歷史上的g濁音聲母詞演化為k清音聲母詞的遺跡,故使用濁聲母g為聲母的口簧名稱安多藏語的Gonggong可能更為古老?參見馬學(xué)良、戴慶廈:《彝族支語音比較研究》,載《民族語言研究文集》,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這對于本文關(guān)于口簧起源的擬測有重要意義。
另外,彝語支語言和藏緬語族其他語言有共同來源,其聲母清濁狀況可能反映了上古語言未分化前原始母語中k-g可以互轉(zhuǎn)的狀況。(1)本語族同源詞中k-g對應(yīng)?參見趙衍蓀:《白語的系屬問題》,載《民族語言研究文集》,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如:白語ko,撒尼語ga亅,納西語go┘,哈尼語ga亅,藏語ka,意思是“愛”;(2)白語中的濁音清化g-k對應(yīng)。如:大理話ga亅,劍川話ka亅,意思是“說”;(3)白語中的漢語借詞g-k對應(yīng)。如:漢語gan,白語ka┐,意思是“甘”;(4)與藏語十分接近的門巴語方言中也有k-g對應(yīng)的現(xiàn)象。如:文浪話gor,麻瑪話kor,意思是“石頭”;(5)基諾語中漢語借詞讀音g-k對應(yīng)?參見蓋興之:《基諾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如:漢語gāo,基諾語ku┤,意思是“高”,等等。至此,對于本語族里諸語言的口簧名稱的清——濁,即k-g對應(yīng)關(guān)系已多有舉例,這一類例子還有不少,茲不再贅。不過,我們可以肯定藏緬語言中存在清——濁互轉(zhuǎn)或濁音清化的事實,所以,結(jié)論必然是:
藏緬語族群語言,與古漢語關(guān)系是同源共祖的。我們以下集中討論漢語中的情況。迄今所見到的介紹各民族口簧的文獻(xiàn),往往把它的讀音對譯成如下漢文:

?李卉(臺灣):《臺灣及東亞各地土著口弦之比較研究》,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xué)研究所圖書館抽印本。引劉咸(1940):“每天我在樓上寫作時,索郎仁清的七歲幼女榮中,時常上樓,倚在扶梯腳邊彈‘貢貢’,洋洋的音調(diào),有點象琵琶……‘貢貢’是西戎小兒女們必有的樂器……‘貢貢’是青海西戎形聲的名稱,實際上是一個竹制口弦。”青海西戎,就是今天稱為藏族的安多藏區(qū)土著人民。
以上漢字字音今古音韻對照如下(古音以《切韻》為準(zhǔn))?參見丁樹聲:《今古字音對照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并把同組字排在一起,便于比較:


?參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0年。中古以后,輔音韻尾r失落,實際成為ga,可參考哈尼語maga和其它一些帶ga音節(jié)的口簧名稱。中古以前,何、賀讀音為gar和garh。?參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0年。
以上字音可依古漢語音韻指出如下特點:
這些字多在喉位發(fā)音,匣紐字在深喉,見紐字、溪紐字在淺喉,古漢語深喉字比淺喉字古老,故匣紐字“貢貢”一定比溪紐字“口口”早,其他見紐字、溪紐字同理。上古發(fā)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諧,是古漢語一條規(guī)律?參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故匣紐字可以互諧通轉(zhuǎn),因此,禾、何、和、賀、黃、簧、洪等作為樂器名稱讀音的記寫漢字,在音、韻上是同源、同一的。同理,這些溪紐字、見紐字,在音、韻上也是同源、同一的,讀音通假是為必然。
2.韻
在藏緬語族各語言中,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就是:聲多則韻少,聲少則韻多?參見瞿靄堂:《藏語韻母研究》,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年。。
藏文單元音韻母有五個:*i、*e、*a、*u、*o。復(fù)元音韻母有三個:*iu、*eu、*au。輔音韻尾有九個:*-b、*-d、*-g、*-r、*-1、*-s、*-m、*-n、*-η。由五個單元音韻母與九個輔音韻尾結(jié)合成四十五個帶輔音韻尾的韻母,由五個單元音韻母與七個復(fù)輔音韻尾結(jié)合成三十五個帶復(fù)輔音的韻尾。這其中,安多方言沒有復(fù)元音韻母,也沒有鼻元音,元音不分長短,它帶輔音韻尾的韻母比其它方言穩(wěn)定、并且輔音韻尾最多(即:-p、-1[~-t]、-k、-r、-m、-n、-η)。安多方言另一特征是只有e、a、u、o四個元音能與輔音韻尾結(jié)合。在本章特別關(guān)注的是青海省藏區(qū),農(nóng)業(yè)地區(qū)只有-k、-r、-η或再加一個-n作為輔音韻尾,有33個帶輔音韻尾的韻母,口簧名稱藏語韻母-an、-oη即在其中。而上述所有這些特征證明,安多藏語是保留古代面貌最多的藏語方言。之所以從藏語韻母開始進(jìn)行探討,是因為藏緬語系各族(包括說漢語和漢藏雙語的人群——回族/穆斯林)的口簧名稱韻母的變化和對應(yīng),符合古藏語(公元9世紀(jì)時)的韻母對應(yīng)規(guī)律,從而標(biāo)示出它們共同的語源。藏族口簧名稱gao、kuo同韻,而聲母k-g已證明可以互諧,故gao就是kuo,殆無疑義。在康方言中,o對應(yīng)oη或aη,所以gao、kuo必然可以與同韻,因為在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中,o-u可以對應(yīng)互諧,故可知,單音節(jié)口簧名稱gao、kuo與雙音節(jié)詞同源。
根據(jù)藏語韻母規(guī)律,-n和-η為互補鼻音韻尾,并且前元音i、e只與-n結(jié)合,后元音a、o、u只與-η結(jié)合,所以-an韻實際上是oη或aη韻,故gian就是Koη或,它的聲母無須再證對應(yīng)關(guān)系,而其韻尾aη-oη也與a-o-u對應(yīng),這樣一來,Koη也可以是ko-go-ku-gu,對照納西族口簧音讀kegu和gugu,參考安多方言馬蹄寺話u可以是e,則可斷定,kegu也就是gugu,而它們也一定與ko-go或koηkoη同源。彝族口弦音讀Hehe其聲母h上文已證明可通諧g-k等聲母,而按藏語韻,e對應(yīng)o-u,則hehe也可以是gugu或kegu了。回族之koukou,照理也可以與koηkoη、gugu、kegu、hehe壓韻互諧、對應(yīng)通轉(zhuǎn)了。另外,or韻則又可對應(yīng)o-ε或-i-u-?,則甘肅地方稱口簧為Haorhaor,其韻尾按藏語韻可以對應(yīng)o-ε,故也可以通轉(zhuǎn)諧韻于以上各韻了。Haorhaor(“嚎兒嚎兒”)的語源不正暗示了其與藏語的聯(lián)系嗎?按古漢語音韻學(xué),koukou、hehe與古“簧”字讀音相諧,或竟可讀若gar即中古時代“何”“禾”“和”。民俗學(xué)資料顯示的,甘肅地方叫口簧這件樂器為“簧簧”(Haorhaor、“嚎兒嚎兒”),則hehe也就是“賀”“何”“禾”“和”或“簧簧”。?參見牛龍菲:《古樂發(fā)隱》,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頁。“今甘肅省通渭一帶地方,至今仍有鼓動之簧的遺存。通渭老鄉(xiāng),將這種樂器叫做‘嚎兒嚎兒’(讀做haorhaor)。此,當(dāng)是‘簧’字的一音之轉(zhuǎn)。”“彝語將‘簧’——口弦稱做‘洪洪’,也就是‘簧’字的一音之轉(zhuǎn)。”而洪洪、嚎兒嚎兒,正與前文所證之禾、賀、和等字諧韻對應(yīng)。牛龍菲(隴菲)在本文作者發(fā)表口弦名稱的歷史語言學(xué)研究之前就已指出這些現(xiàn)象,有很高的歷史語言學(xué)價值。
3.調(diào)
藏緬語族語言中,最古老的形態(tài)是無調(diào)的語言,如藏語安多方言,音節(jié)也十分簡單。普米語只有兩個聲調(diào),獨龍語有三個聲調(diào),而且許多語言用聲調(diào)區(qū)別詞義的詞只占全部詞匯的極小比例。本語族口簧名稱音讀,只有單音節(jié)詞、雙音節(jié)詞,并且大多無聲調(diào)變化,顯示了它們的古老面貌?王遠(yuǎn)新:《中國民族語言學(xué)史》,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93年,第51–54頁。;可以相信,那些帶聲調(diào)的口簧名稱,必晚于無聲調(diào)者。值得注意的是,珞巴語沒有聲調(diào),其口簧名稱音讀與安多藏語相同,按漢藏語系語言規(guī)律,Gonggong最為古老,后來演化為 KoηKoη、納西族的Kongkong、怒族的 KwuoKwuo、古漢語的“簧簧”(huanghuang)、今天民間漢語的“嚎兒嚎兒”(haorhaor),展現(xiàn)出G-K-H語音演化歷史,毫無疑問,這些名稱其間必有深遠(yuǎn)聯(lián)系。
四、漢藏語言表型與口簧的起源與分布
金力院士團(tuán)隊關(guān)于漢藏語系語言起源和分化問題的研究報告?英國《自然》雜志,第569卷,2019年5月2日,P.112-P.125。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Menghan Zhang 1,2,8 ,Shi Yan 3,4,8 ,Wuyun Pan 5,6 & Li Jin 1,3,7。,有兩個最為主要的要素:時間與空間,即:漢藏語言的起源和分化、地理分布與擴(kuò)張問題,同時也討論了分化擴(kuò)張的動力。對于本文的意義在于:這兩個要素正與口簧起源時間和空間分布有深刻聯(lián)系;其擴(kuò)張動力帶來人口的流動與口簧今天可以觀察到的分布有關(guān)。
漢藏語系語言起源的主要假說有兩種:一是南方起源說,一是北方起源說。與本文的擬測有關(guān),北方起源假說認(rèn)為漢藏語系最初的擴(kuò)張是在距今4000-6000年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這種擴(kuò)張與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或馬家窯文化的發(fā)展有關(guān),比石峁遺址要早,但本文認(rèn)為,這里顯然有時間上的連續(xù)性和空間上的重合性存在。根據(jù)金力團(tuán)隊的報告,漢藏語系語言起源之地,正是在甘、寧、青、陜北、內(nèi)蒙南部的大河套地區(qū),“黃河上中游地區(qū)的人說的是漢藏語系的原始語言,他們被分為兩組,在距今4000-6000年前的時間里,有一群人向西遷移到了西藏,向南遷移到了緬甸(成為說藏緬語的現(xiàn)代人口的主要祖先),而另一個族群(說漢語的祖先)向東和向南遷移,最終成為漢人”。大多數(shù)歷史語言學(xué)家傾向于這一假設(shè),認(rèn)為漢藏語系的發(fā)展與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大約距今5000-7000年)或馬家窯文化(約距今4000-5500年)的發(fā)展有一定的關(guān)系。該項研究對漢藏語系的109種語言的949個詞根意義進(jìn)行貝葉斯系統(tǒng)分析法測算?譯者注:Bayesian analysis,屬于進(jìn)化生物學(xué)的貝葉斯方法是基于貝葉斯定理而發(fā)展起來用于系統(tǒng)地闡述和解決統(tǒng)計問題的方法。一個完全的貝葉斯分析包括數(shù)據(jù)分析、概率模型的構(gòu)造、先驗信息和效應(yīng)函數(shù)的假設(shè)以及最后的決策。貝葉斯推斷的基本方法是將關(guān)于未知參數(shù)的先驗信息與樣本信息綜合,再根據(jù)貝葉斯定理,得出后驗信息,然后根據(jù)后驗信息去推斷未知參數(shù)。這些方法允許靈活的進(jìn)化模型,是推斷全球語言譜系進(jìn)化速度和變化模式的有力工具。,估計漢藏語言的分化時間約為距今4200-7800年,平均約為距今5900年,這與石峁口簧的確定考古學(xué)年代——距今4300年,以及石峁口簧的地理分布區(qū)域的關(guān)聯(lián),可能是巧合嗎?
在語言傳播區(qū)域和傳播動力方面,該報告認(rèn)為,漢藏語的傳播可能與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和人口快速增長有關(guān)。谷物農(nóng)業(yè)的傳播主要發(fā)生在距今5000年之后,從現(xiàn)在的中國北方(特別是黃河流域)的西南部,沿著青藏高原的邊緣向南傳播。一系列考古證據(jù)——如建筑形式、陶器的圖案和形狀——也顯示出沿著藏彝民族走廊向南連續(xù)不斷地擴(kuò)散到川西和滇西省份,該報告所附圖表清晰地表明了這一認(rèn)識。這種分散在時間上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一種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文化,在大約距今3500-4300年的歷史上繼承了馬家窯文化)。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時間要素正是在石峁口簧發(fā)生和活躍年代前后,而其分布則也正是沿著今天的縱向河谷地帶,所謂藏彝民族走廊向南擴(kuò)散,帶來了這一廣大地區(qū)的口簧及其演化形態(tài)今天的遺存。在古代,樂器和音樂的傳播,完全是隨人而擴(kuò)散,因此該報告還涉及了體質(zhì)人類學(xué)的遺傳染色體(y)的研究,這與石峁考古報告所認(rèn)為的,創(chuàng)造石峁文化的是根植于河套地區(qū)仰韶文化晚期以來久居于此的土著人群的認(rèn)識,也是可以相互映證的。方言地理學(xué)的研究,同樣給予了我們類似的認(rèn)識,中國語言地圖的形成,與人口流動有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參見周振鶴:《中國的方言為何如此復(fù)雜?》,《地圖》,2009年,第5期。。金力團(tuán)隊報告指出,在黃河流域,考古遺址數(shù)量的迅速增加和持續(xù)的森林砍伐表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從大約距今6000年開始到距今5000-4500年加劇,這個時間軸與他們的研究中對漢藏語和藏緬語差異的時間估計一致。
按前文關(guān)于口簧名稱的歷史語言學(xué)研究獲得的認(rèn)識,聯(lián)系漢藏語系語言的一般規(guī)律,我們擬測安多藏語-珞巴語的口簧名稱“Gonggong”為最古,可能在漢藏語系語言尚未分化的時期就已形成。而其后隨著人群的移動,由縱向河谷地帶——藏彝民族走廊向南傳播,伴隨著語言的演化出現(xiàn)了口簧名稱的同步演化和傳播。根據(jù)金力團(tuán)隊的報告,漢藏語系之間的大量語言接觸可能發(fā)生在這些語言多樣化的早期階段,并可能持續(xù)到今天,進(jìn)而發(fā)生南中國廣大地區(qū)各民族口簧名稱的相互影響;漢藏語系各成員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它們與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苗瑤語系、壯侗語系和南島語系等鄰近語系的相互作用,可能導(dǎo)致口簧名稱在亞洲大陸各民族和南島語系各民族間的同源和演化形態(tài),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前文所列臺灣的高山族和東南亞南島語民族存在著與漢藏語族口簧名稱相同的問題。
金力團(tuán)隊報告指出:“研究語言的起源與分化對理解人類的歷史和文化至關(guān)重要。”對于音樂史當(dāng)然也是如此,中國音樂史上留下了許多古老的語言痕跡,值得我們?nèi)ヌ接憽?/p>
就本文討論的對象而言,語言的歷史變遷與人類的遷徙,語言的分布與口簧樂器的分布,有著高度重合的歷史現(xiàn)象,這個認(rèn)識在目前的知識水平上是可以成立的。但筆者希望有新的音樂學(xué)、考古學(xué)和語言學(xué)、人類學(xué)的成果繼續(xù)就此問題展開研討,筆者并不希望自己的認(rèn)識是結(jié)論性的,而是開放的,發(fā)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