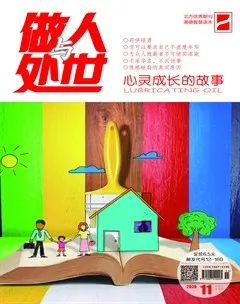相思始覺海非深
潘彩霞
1946年,年輕的軍官饒平如收到父親的來信,希望他請假回家,一則參加弟弟的婚禮,再則完成自己的定親大事。自從18歲考入黃埔軍校,他就決心投身到抗日的浪潮中,如今,24歲的他已經是個老兵了。對家里安排的相親,他曾因抗戰而拒絕,可是抗戰已結束,這次他沒法推脫了。
“屋子很大,我走過第三進的天井,正要步入堂屋時候,忽見西邊正房小窗正開,一位面容姣好、年約20歲的小姐在窗前借點天光攬鏡自照,左手拿了支口紅在專心涂抹。”跟著父親走進毛美棠的家時,這一幕躍入眼簾。因為兩家是世交,兒時曾見過面,他記得她的聰慧,她也沒忘記他好看的眼睛。
戒指一交換,情定三生。幾日相處中,毛美棠卷起紙筒唱歌,饒平如吹著口琴伴奏,她唱“白石為憑,明月為證,我心早相許;今后天涯,愿長相憶,愛心永不移”,他則含蓄地回應:“Oh,Rose marry,I Love You!”
饒平如假期結束返回部隊時,同樣的一江水、一艘輪,心緒卻與來時大不同,“在遇到她以前我不怕死,不懼遠行,也不曾憂慮悠長歲月,現在卻從未如此真切過地思慮起將來。” 因不想參加內戰,饒平如申請了閑職,于1948年回到南昌與毛美棠完婚。一個身披白紗含羞帶俏,一個穿著軍裝英俊挺拔,在著名的江西大旅社,賓客200余人見證了這場盛大的婚禮。
時局動蕩,國民政府幾近癱瘓,饒平如帶著毛美棠在亂世中東奔西走。在貴陽,住在家徒四壁的涼亭改成的房子里,昔日的大小姐學著洗手做羹湯。受“歷史原因”影響,饒平如求職屢屢被拒。幾經輾轉,在舅舅引薦下,他到上海一家醫院做會計,并兼出版社編輯。伉儷情深,嬌兒承歡,日子雖平淡,卻心甘如飴。
1958年,政治運動風起云涌,因為“偽軍官”的身份,饒平如被當成“反革命”送到安徽勞教。毛美棠上有年邁老母,下有5個未成年的孩子,全部的家庭重擔一下子都落在了她的肩上。那時,有太多的夫妻反目,而她選擇信任、等待。當出版社的人找她談話,要求她與他“劃清界限”時,她的答復是:“他不是漢奸賣國賊,不是貪污腐化,不是偷竊扒拿,我為什么要離婚?”
他們無法預料的是,這一分開,竟長達22年。家里沒有收入,生活陷入困窘,全家每天只能吃兩餐,主菜就是咸菜。為了補貼家用,毛美棠去旅社做勤雜工,去月餅廠做女工,去紙廠做揀紙工。上海自然博物館建造時,還去工地背幾十斤一袋的水泥,從此落下腰傷。除了生活的苦,作為“勞教分子”家屬,毛美棠還要承受冷落和歧視。世態炎涼嘗盡,她給饒平如的,卻始終是微笑。為了安慰他,她給他寄去一張全家福,照相時,特意叮囑大家都面帶微笑。相片背后還寫了一行字:“平如,你看我們全家都很好,你只要好好改造,未來我們還會團聚在一起的。”
饒平如因缺乏營養,全身浮腫,無藥醫治。恰恰這時,她寄來了一瓶魚肝油。物質缺乏的年代,她是怎么做到的已無從知曉。奇妙的是,腫脹的癥狀真的隨著吃下去的魚肝油消失了。而他不知道,那時的她,為了省2元6角錢,堅決不去看自己的腰痛,以致為身體埋下了隱患。
22年間,相互通信成為彼此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孩子們的童年記憶里,她永遠是在燈下寫信的樣子,以致鋼筆筆尖都磨平了。給他的信中,無一例外都會在信末加一句“我們很好,勿念”。而他亦同樣靠讀她的信抵御寒冷和孤獨。那些信,他一封都沒有丟棄,看完就鎖在木頭箱子里。1979年回到上海時,兩人間的通信多達千余封。當他終于被告知撤銷處分決定、恢復工作時,已是1980年深冬。那年,他57歲,她54歲。
歲月靜好,兒女立業成家,孫輩繞膝,雖不是曾經向往的田園生活,總算祥和寧靜。他兩次手術,她細心照料;她有糖尿病,他畫了一個大表格,把每種食物的含糖量記錄下來嚴格控制;多年操勞讓她患上尿毒癥,80多歲的他親自學了“腹膜透析”,短短幾秒鐘就完成腹腔管和引流管的連接。彼此陪伴,就是幸福。
原以為只要用心對她,便能永久相守,誰知命運的不公來得那么突然。樂觀的她變了,性情乖僻,不通情理,說話也開始前言不搭后語,直到有一天,她躺在床上說:“去拿把剪刀來,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一點。”心轟然倒塌,一時之間,他絕望至極,坐在地上失聲痛哭。她患了癡呆,說話總是沒頭沒腦,而他每每當真。她夜里要吃杏花樓的馬蹄小蛋糕,87歲的他騎了車去買,送到嘴邊她又不吃了;她要找黑底紅花旗袍,他記憶中并沒有,明知幾分鐘后她就忘記了,還是想著找裁縫去做一件。她糊涂了,可是腦海深處,仍是牽掛著他,偶爾清醒時便會叮囑他:“你不要亂吃東西,也不要騎腳踏車了。”病重昏睡時,她也會突然醒來,對照顧她的女兒說:“你要好好照顧你爸爸啊!”
最后的時刻還是來了。像有心靈感應,昏迷很久的她突然睜開眼睛,看到人群中的他時,眼眶漸漸濕潤,緩緩凝結成一滴掛在眼角的淚。悲傷難抑,他剪下她的一縷頭發,用紅線扎起來,作為余生的紀念。送別時,他用了3天時間寫了一副挽聯:“坎坷歲月費操持,漸入平康,奈何天不假年,慟今朝,君竟歸去;滄桑世事誰能料,閱盡榮枯,從此紅塵看破,盼來世,再續姻緣。”最后一句寫完,眼淚早已洶涌而出。
毛美棠去世后,饒平如唯一的事是寫她念她想她。他不顧耄耋,獨自去找尋他們的曾經。當年攜手的江西大旅社已變成南昌起義紀念館,物不是人也不是,然而看到那一檐一柱,當年結婚時的情景歷歷在目;南昌湖濱公園長椅上,吹口琴的人還在,那個卷起紙筒唱歌的人卻永遠離開;走進上海自然博物館,他會想,哪塊水泥是她背起來的。她沒有離開,他要讓她活在心里。“死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們記錄下來。”4年時間,他們的故事變成300幅畫作,并輔以詩文。《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面世了,畫冊的扉頁,他親筆題詞:“同生死,共患難,以沫相濡,天若有情天亦老;三載隔幽冥,絕音問,愁腸寸斷,相思始覺海非深。”
2020年4月4月,饒平如與他的美棠團聚了。所有美好,都不會結束,穿過生死和悲喜,愛無別離。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