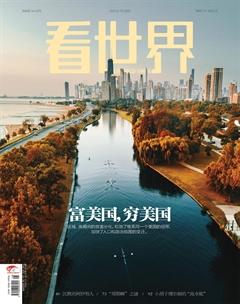“周期蟬”之謎
菲力

2016年,昆蟲學家和愛好者期待著一個特殊且篤定的時刻:深度為8英寸(20.32厘米)的土壤,連續四晚溫度達到17攝氏度—很快,這一刻隨著初夏來臨。
一夜之間,異乎尋常的躁動充斥了北美。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馬里蘭,到西弗吉尼亞和俄亥俄等地區,大批蟬破土而出,密度達到每英畝150萬只。每一鏟鐵鍬都能挖出數百枚蟬蛹,每一棵樹上都攀附著數百只振翅鳴叫的蟬。那是一種壓倒性的、不容置疑的聲勢。
生命之歌
今天,全世界范圍內有超過3000種蟬。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數字每年都在增加。除南極洲外,這種渺小的昆蟲遍布地球上的所有大陸。其中,2016年在北美大量暴發的,是一種遵循著某種特定生命周期的蟬,它們上一次集中出現是在17年前的1999年,人們將之與另一種生命周期為13年的蟬共同命名為“周期蟬”。
周期蟬只存在于北美大陸,生命里的絕大多數時光都蟄伏于地下。一朝破土,即進入生命最后一個月的死亡倒計時,遂瘋狂繁殖,而后決絕死去。
破土后,剛褪去若蟲舊皮的幼蟬有一對紅色復眼,周身黝黑,背上長著一對金色薄翼。只需要5天,幼蟬迅速成熟,身體變大轉褐色,翅膀變長。一場生命之歌的演奏會準備就緒。
每只雄性蟬都將高聲發出80分貝至100分貝的交配鳴叫聲,相當于運轉著的汽車發動機或剪草機的噪聲。一時間,這些數量達到百萬之巨的17年蟬瘋狂交配、產卵、鳴叫,仿佛一艘裝載著巨大引擎的外星飛船不斷逼近地球—它們從1999年就開始等待這一刻。
但大量周期蟬的暴發給當地居民的生活帶來很大不便,人們甚至在出門時需要打起傘來遮蔽這些小昆蟲。蔥綠的草坪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蟬蛻,踏在上面就像踩上了影院散場時一地的爆米花。對于密集恐懼癥患者甚至普通人來說,這樣的場面難免引發生理不適。
美國蟬分類學實驗室創始人克里斯·西蒙博士,接到市民的求助電話,后者尋求快速清除蟬的方法。但西蒙博士對此很不滿意:“太荒唐了,它們每17年才不過帶給人們兩周的不便。”要知道,對于昆蟲愛好者來說,這可是17年等一回的好運氣。
超量滿足
時間倒退回1999年,這批新蟬還是剛剛孵化而出的幼蟲,剛開始樣子像瘦弱的白蟻,但很快就長得白胖。它通常從較小的草根開始,一直摸索到其宿主樹的根部,一頭鉆入地下,靠吸食樹根汁液存活。地下的生活既黑暗又溫暖,既安全又孤獨,唯一的問題是,太久了—即便在人類的生命尺度上也堪稱漫長,更何況是昆蟲!
數量多到讓掠食者敞開肚子也吃不完,于是剩下的蟬就能夠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
確切的時間早已寫在基因里。不同種類的周期蟬都在體內安裝了走時準確的生物鐘,最長可達17年,使其成為昆蟲界最長壽的物種。關于17年蟬最早的記錄可以追溯到1633年,有人描述了一種產自北美的蟬,周期極長。但直到18世紀初,美國昆蟲學家才最終確定了這種蟬的周期:17年。一百多年后,又有一種周期為13年的蟬被發現。科學家才正式將這兩種擁有漫長周期的蟬,命名為“周期蟬”。今天,在耶魯大學皮博迪自然歷史博物館還保存著1843年的17年蟬標本,是所有博物館藏品中最古老的。
永遠不要小看長者的智慧,即便是一只小昆蟲。今天人們普遍認為,周期蟬的周期性是一種長期進化形成的生存策略,目的也很簡單:活下去。蟬的天敵很多,作為一只小小的昆蟲,不僅是幾乎所有食蟲鳥的盤中餐,甚至也包括人類—美國卡爾頓大飯店在2016年特別制作了一道“蟬菜”,把蟬裹上面粉用橄欖油炸,再配以白酒和蔥等調味,頗受歡迎。
大多數物種躲避天敵的方式,不外乎偽裝、躲避或干脆把自己變得難以下咽。但“好吃的”周期蟬不走尋常路,它們的策略是“超量滿足”,在短短兩周內大量暴發,數量多到讓掠食者敞開肚子也吃不完,于是剩下的蟬就能夠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犧牲一些蟬的生命,換得整個物種存續的機會,這種“敢死隊”式的生存策略,悲壯而決絕。

大量周期蟬暴發后草坪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蟬蛻,對于密集恐懼癥患者甚至普通人來說,這樣的場面難免引發生理不適
周期蟬的另一個謎團是13與17的“質數之謎”,這兩個數字都只能被其自身和1整除—如果人們不想用“巧合”這種偷懶的借口來解釋的話,這一事實確實困擾了科學家很多年。
直到1977年,古生物學家史蒂芬·杰·古爾德提出了一種假說,周期蟬獨特的質數生命周期,是為了避開有著偶數年生長周期且生活史較短的掠食者。例如,倘若有一種8年蟬,那么它將遭遇的是所有生長周期為2年、4年、8年的掠食者。對于17年蟬來說,即便在大暴發的年份里,使掠食者獲得了超量滿足、種群擴張,但在此后的16年間還是會由于食物不足慢慢回落到正常水平。除非天敵每年都繁殖,或恰好17年繁殖一代,否則周期蟬的暴發幾乎不會成為天敵種群擴張的助力。
迷幻蟬生
數以億萬計的蟬慷慨赴死,讓每一個活下來的蟬都明白生命之不可辜負。
據統計,北美有2%~5%的周期蟬在鉆入地底前已沾染蟬團孢霉,并在破土時逐步侵入腹部。真菌在蟬的肚腹內快速滋長,導致蟬身體膨脹甚至會斷開成兩截,露出白色粉末般的孢子散播到空氣與泥土中。研究人員稱之為“會飛的死亡鹽罐”。即便如此,感染蟬團孢霉的蟬仍然具有生命活力,并不妨礙其持續瘋狂交配,產下后代。
2016年5月,西弗吉尼亞大學真菌專家Matt Kasson搜集了150只不幸感染的周期蟬,檢驗當中的化學成分,終于對這種“喪尸霉”有了更多了解。他們在感染蟬團孢霉的標本中發現大量迷幻蘑菇的主要迷幻劑成分“裸蓋菇素”。這是學界第一次在迷幻蘑菇以外的真菌中發現裸蓋菇素,而蟬團孢霉與迷幻蘑菇的共同祖先要追溯至9億年前。換言之,蟬團孢霉在蟬體內開了一間迷幻劑生產工廠。
這是一群嗑了迷幻劑的蟬,食欲不振,卻性欲不減。在死亡也不能戰勝的青春里,它們依靠幻覺交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沒來由地興奮,卻也難免在生命盡頭令人感傷。
周期蟬的生命既野蠻又智慧,既瘋狂又精確,既孤獨又喧囂,它們奇特的生存方式令生物學家們著迷了數十年。直至今日,仍存在很多未解之謎。比如,人們尚不確定周期蟬的產生是否與古代的冰川氣候存在一定聯系?為什么會有少量周期蟬提前或推遲4年破土?這是否與若蟲的地下生存資源競爭有關?沒有什么是理所當然的,每一個進化至今的物種都經過深思熟慮。
而另一個叫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是: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種群正在減少甚至滅絕。原因與土地開發有關。城市擴張,水泥鋪地,若蟲鉆不到地下,生命孵化的路徑被阻斷。例如,1945年至1979年,美國康涅狄格州蟬的數量減少了5%,大部分是開發州際公路系統的結果。
周期蟬之謎,是生命之謎。這份驚嘆與不解,是造物主的禮物。它讓人類在某一片刻,將目光從公路、電視和促銷傳單上移開,投向柔軟的泥土深處,探尋一種更為神秘、幽深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