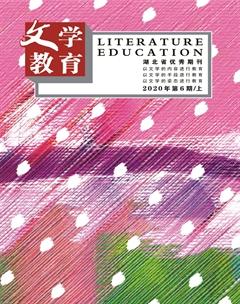信息十六則
新聞一束
本刊發表的《由“佛鉆”引起的聯想》入選《2019中國雜文年選》
本刊2019年第1期發表的范軍教授的雜文《由“佛鉆”引起的聯想》(發表時署名維成)入選向繼東先生主編《2019中國雜文年選》(花城出版社2020年1月版)。《2019中國雜文年選》是“花城年選”中的一種,選輯2019年度中國優秀的雜文作品,全都發表于公開出版的報刊等傳媒上。全書稿分為“浮世繪”“雜感錄”“隨想記”“溫故坊”“新視點”等五輯,即五個部分。所選文章涉及廣泛,內容豐富,歌頌真善美,鞭撻假惡丑。《由“佛鉆”引起的聯想》從清代王世禎《香祖筆記》中的《佛鉆》一文出發,作者浮想聯翩至現今社會,文章寫道:“君不見,眼下‘牌鉆、‘球鉆、‘棋鉆、‘歌鉆、‘舞鉆、‘詩詞鉆、‘書畫鉆、‘攝影鉆、‘徒步鉆、‘網游鉆等等已是層出不窮,且‘一人數鉆、‘集眾鉆于一身的與時俱進者大有人在,如此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真是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鉆在成長。”文章借古諷今,針砭時弊,具有極強的藝術性和現實性。
第七屆“中國童書榜”發布
第七屆“中國童書榜”日前揭曉2019年度“最佳童書獎”“優秀童書獎”“最佳編輯獎”評選結果,并發布年度“中國童書榜”一百佳書單。受疫情影響,本次頒獎典禮采用網絡視頻直播的方式進行。書榜所涉及童書,是從全國近80家出版社報送參評的602本(套)童書中,經過初評、網絡復評、專家推薦、終評四輪次精心甄選產生的,其中《一條大河》《蘇丹的犀角》《有鴿子的夏天》等12種童書獲年度“最佳童書獎”,《游俠小木客》《茶》《云三彩》等12種獲年度“優秀童書獎”。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總社編輯出版、于大武著繪的原創繪本童書《一條大河》獲本屆“中國童書榜”榜首。這是中國首本寫給孩子的以黃河為主題的原創繪本,展現出一條古老而漫長的黃河,也呈現出一條跟我們每天生活息息相關的大河。“2020年的冬天和春天,我們是特殊地度過的。可是,文學、藝術、兒童閱讀,終究是一條不可停下的大河。中國人的生活和精神,更是大河般熱情和澎湃的。”新閱讀研究所所長、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梅子涵在致辭中說,“此次榜單以一條大河為首,設立了一個無意的象征:偉大的中國是壯闊的。也如同獲獎童書劉海棲《有鴿子的夏天》小說中的鮮亮含義:任何時期,中國天空總有鴿子飛翔,中國是美麗的。”首屆上海文學藝術翻譯獎評選啟動
首屆上海文學藝術翻譯獎評選曰前正式啟動,由市委宣傳部指導,市文聯、市作協、上海翻譯家協會聯合主辦,將對標國際最高水平,打造高規格、高品質、高影響力的文學藝術翻譯獎項,計劃每三年評選一屆。首屆評獎范圍為2014年1月l曰至2018年12月31日出版、演出、播映的作品,設文學翻譯獎和表演藝術翻譯獎兩個類別,參評作品申報截止時間為今年8月31日。業內認為,上海文學藝術翻譯獎的創辦,一方面將提升上海作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碼頭”能級,推動上海國際文化翻譯中心建設,讓中國和世界優秀文藝作品更多地來滬出版、展出、展演、展映;也將助推上海原創文藝作品“源頭”建設,進一步用好用足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資源,著力推出更多“上海原創”,推進新時代的上海文藝創作更好地走向全國、擁抱世界。據悉,首屆上海文學藝術翻譯獎評選不接受個人申報,僅限機構推薦,范圍如下:文學類翻譯作品的出版單位推薦本社出版的作品;表演藝術類翻譯作品的演出、制作單位推薦本單位演出、制作的作品;其他相關部門或機構推薦的作品。文學類翻譯作品以成書形式參評,必須為公開出版物并進入正規市場。書籍以版權頁標明的第一次出版時間為準,表演藝術類翻譯作品以首次正式公開演出、播映為準,不接受重譯作品參評。
90后作家吟光《上山》研討會舉行
深圳市90后新銳女作家吟光的長篇小說《上山》專題研討會,日前在她的家鄉安徽省安慶市舉行。吟光,本名羅旭,早年曾獲安徽省高考文綜單科狀元,后獲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發表有短篇小說《港漂記憶拼圖》《浮焰沉光》《抱兔的靈力少女》等,作品曾獲香港大學文學獎、臺灣金車奇幻小說獎、2019年中國網絡文學“年度新人”獎等。小說《上山》系作者吟光第一部長篇敘事文學,作品以王維在安史之亂中的經歷為主線,通過云起(原型王維)與枯淵(原型陶淵明)兩個核心人物的穿越對比,講述了一代文人群體在官場與亂世險境中的自保與堅守。小說同時以獨特的視角、宏大的筆法,向讀者解讀了王維為何在安史之亂后不惜自毀名節,接受安祿山的偽職這一歷史之謎。除了別出心裁的歷史視角,作品還以現代社會的眼光,全面還原并傳遞了一個錯綜復雜、多方博弈的唐代文人及權貴階層的朋友圈,有評論者稱其為“一部了解大唐盛世的百科全書”。
作家聲音
王蒙自稱文學是他給生活留下的情書
王蒙日前在新書《笑的風》發布會現場笑稱“文學是我給生活留下的情書”。他說:文學對于我來說是什么?把我所珍惜的、所感動的、所熱愛的一天一天的日子鐫刻下來,書寫下來,制造出來,然后你看到這些作品的時候就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樣。這樣我不光是過了這個日子,我還愛了這個日子,還想了這個日子,還寫了這個日子,還描畫了這個日子,我還反復琢磨了、咀嚼了、消化了、整理了、梳理了這些日子,在某種意義上挽留了這些日子。如果沒有《青春萬歲》,我盡管沒有忘記1948年到1953年的這些日子,但是慢慢就記不太清了,總不能說我85了還跟15歲一樣激動、一個勁頭,那不也有點鬧笑話嘛。所以文學的好處就是它把生命挽留了一下,它把經驗挽留了一下,它把我自己的愛情,對土地、對國家、對人、對歷史的這種愛情挽留了一下。所以文學還是挺有意思的。要沒有《青春萬歲》,我再說起那幾年來就沒有現在這么多詞。要沒有《這邊風景》,我說起新疆的生活來跟現在也不一樣。
馬原認為“先鋒”其實是一種革命
馬原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說:中國的文學在整個歷史進程當中,革命創新的時候并不多。“先鋒”其實是一種革命、一種創新,是一種對原有秩序的拆解和重構,我剛好趕上了那個歷史階段。過去的小說強調“文以載道”,要有明確的立場、觀點;而新的小說——后來被稱為“先鋒小說”的,剛出來的時候,文字全都懂,但主旨是什么、意義是什么,大家一下子找不到閱讀的方向。先鋒,首先是價值觀方法論的革命,背后有強大的哲學作為支撐,然后才是審美的創新,我個人認為這是先鋒小說最大的貢獻。現在的小說也有敘述方式的花樣翻新,但是沒有新的哲學,沒有那種徹底的拆解和重構。我不是那種有很強時間性的作家,幾十年后,我的書還可以被閱讀,被重印,但每次也不印很多。我認為小說是人類生命悠閑階段的一部分內容——首先你得有閑暇,讀小說是一個打發時間的方式。就像“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這詩說啥呢,不知道說啥,也沒有多少教育意義,但是它的節奏、它的構思、它的詩意,就在那兒。作為讀者,我就是想領受一種詩意、一種愉悅、一種傾盡其中。我一直不喜歡看那些弄得太深奧的,就像我一直認為意識流是小說歷史上的一個大倒退,因為它在和讀者為難。我也不喜歡宏大敘事,不做大時代中的弄潮兒。我覺得像一片葉子,在時代洪流中順流而下,是我人生的一種理想狀態。
徐則臣自稱被文學的神奇拴上一輩子
徐則臣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說:1997年8月的那個黃昏至今,一晃22年過去。就像在決定寫作之前一門心思要學法律當律師一樣,22年里我沒再想過要做作家之外的任何一件事。當年我以巨大的激情發現了這個職業,該激情延續至今不曾有過絲毫減弱。我要做的就是把文學這件事干好。此后的求學、工作,也都是基于這個愿望展開。如果這算初心,那我可以不謙虛地說,我不存在“忘初心”之虞:文學的神奇足以拴上我一輩子。我的主業是編輯,做文學的生產、管理和服務工作。有足夠的創作經驗和信譽,才能令人信服地從事文學生產、管理和服務工作;反之,在15年的編輯、管理和服務工作中,我又汲取了大量可以反哺自身創作的營養。在文學的道路上前行,要說一點沒感到苦,那肯定是睜眼說瞎話,但我的確在感到苦的同時發現了樂,而這個樂足以包容和覆蓋掉苦,所以一覺醒來,睜開眼就深知這又是精神高昂、氣力飽滿的一天。那么就一個寫作者而言,使命究竟是什么?讓你的藝術盡善盡美;你的寫作能使你更好地與你的讀者站在一起;你要在史的向度上自覺推進你所從事的這門藝術。
麥家認為寫小說要對生活進行改造
麥家日前接受采訪,被問到《人生海海》中“上校”的原型時說:我小時候在一次勞動中,看見一大人,四十來歲,挑一擔糞桶,在百十米外的田埂上向山腳下走去,陽光下他渾身發亮,腰桿筆挺,步子雄健。我不認識他,因為他是隔壁村的。有個同學似乎很了解他,向我兜了他不光彩的底:是個光棍。為什么光棍?因為他的“棍子”壞了;為什么“棍子”壞了?因為他當過志愿軍,“棍子”在戰場上受了傷,只剩下半截。以后我再沒有見過這人,但他渾身發亮、腰桿筆挺的黑影一直盤在我心頭,給了我無數猜測和想象。這就是小說的“第一推力”,像鬼推磨,經常推得我暈頭轉向。他的真實情況我不知道也無需知道,但我想肯定和上校不一樣。我也不相信生活中能尋到像上校一樣的人,這全然是我創造出來的一個藝術人物。其實,這里面的父親和上校是我真實父親的一體兩面,我是把我父親打碎了,然后挑了一些碎片造了兩個新人。兩個人都不是我父親,但都有我父親的一些元素和我的個人情感。寫小說就是這樣,要對生活進行改造,要依靠記憶,又要擺脫記憶。記憶有時是一種情感,沒有形象的,但小說必須要有形象。
作品信息
雪漠攜新書《山神的箭堆》上線直播
“疫情是一塊試金石,它可以試出一個人生命的韌性和強大。”日前,作家雪漠攜新書《山神的箭堆》第一次上線直播,通過屏幕與讀者進行了閱讀交流,在線觀看人數逾9萬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位傳統型作家的直播帶貨效果出人意料之好,新書《山神的箭堆》預售單日銷量過萬冊,成為作家中名副其實的“帶貨王”。《山神的箭堆》是雪漠最新出版的甘南藏地文化游記,講述神秘的藏地故事。該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和已經出版的河西走廊文化游記《匈奴的子孫》、即將出版的嶺南文化游記《帶你去遠方》一起,構成了“雪漠帶你去遠方”系列。雪漠表示,疫情給社會和個人帶來了方方面面的變化,作為一名寫作者,參與這次直播就是一種全新的嘗試,“我非常珍惜和讀者相遇的每一個當下”。
《應物兄》入選“2019年度十佳數字閱讀作品”
日前,2020年中國數字閱讀云上大會上線開幕。會議發布了《2019年度中國數字閱讀白皮書》,白皮書中揭曉了“2019年度十佳數字閱讀作品”。十佳數字閱讀作品聚焦“堅定文化自信、踐行核心價值、注重社會效益、弘揚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關照特殊群體”六大方向,包括《平“語”近人——刁近平總書記用典》《未來學校:重新定義教育》《此生未完成》《詩詞來了》《中華先鋒人物故事匯》《網絡英雄傳之黑客訣》《應物兄》《中國鐵路人》《繁星織我意(上)》《學懂漢字》,充分展現了數字閱讀內容創作堅持社會效益優先、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趨勢。李洱的《應物兄》入選,其推薦理由為:作品通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商業運作奇跡,描繪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社會生態畫卷,串連起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群體活色生香的生活經歷,勾勒出他們的精神軌跡,并最終構成了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
敬一丹推出《床前明月光》懷念母親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近日出版新作《床前明月光》,抒寫自己的失親之痛和對生命的思考。2017年,她的媽媽確診患上癌癥,敬一丹用心陪伴老人走過最后一段溫情時光,后來將其中的點滴記錄成書。敬一丹稱寫的過程有些艱難,幾次因為過度悲傷中斷寫作,“當我終于寫完時,我覺得完成了一種對生命的再認識,也完成了和媽媽的一次靈魂對話。”新書取名《床前明月光》,這是以前夜深人靜時,在病床前陪伴媽媽時想到的,“那是一個很痛苦的經歷,覺得媽媽一點一點地走進暗夜。但即使是至暗時刻,在人生最后一個階段也是有光的,那就是月光。”實際上,敬一丹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一直有一個很清晰的思路:失親之痛不能分擔,但生命的體驗可以共鳴。“在寫作過程中,我更清醒地認識了我的至親,認識了我自己,認識了血脈,所以即使很痛苦,這種記錄也是有價值的。”“以前覺得夕陽、黃昏啊,那還不屬于我,那是屬于我的父母。然而我媽媽去世以后,我覺得我一下子就站在了夕陽里,一下子就望到了月光,也望到了天慢慢黑下去的那一步。”她說。“媽媽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她的生活態度。她是一個特別積極的人,頭腦很清晰,很有方向感。”回憶起母親,敬一丹的難過幾乎掩飾不住。之前,敬一丹曾把媽媽68年留存的1700封家信編成了一本書,“把這本書送給媽媽時,她正在做放療。我一直覺得這些家信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希望媽媽看到它成為一個作品時,在精神上會得到一種力量。”“我們做兒女的未必能夠感覺到,當父母老去,慢慢失去一些能力時,他們也是需要肯定、鼓勵、贊賞的,就像我們小的時候經常得到他們的肯定、鼓勵、贊賞一樣。這是我做的讓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敬一丹說。
蔡測海推出最新長篇小說《地方》
長篇小說《地方》是全國少數民族駿馬獎得主蔡測海最新長篇小說力作,費時十多年始成,是“三川半三部曲“中繼長篇《非常良民陳次包》《家園萬歲》后的第三部,也是“三川半”系列最厚重最扎實的一部。該書圍繞作者創作的文學故鄉三川半幾十年的歷史展開,以詞條的形式將三川半的人、事、景、物、情等分割成一個個小點,分篇講述,重疊交錯又各自獨立;既交織,又疏離;如同張合有力、綿密厚實的一張大網,將作者對“理想故土”的熱愛、疼痛、悲憫、感懷和人情世故、一山一水精彩描繪出來。歷史與傳說、現實與幻想、夢境與非夢、個人和家國、民族和世界、地方和遠方,都在作者出色的想象力與深厚的文字功夫中有獨到的見解和新穎的思辨。三川半是作者魂牽夢繞的地方,一個草木生靈、畫意山水、家常倫理、入神共享的世界。小說敘述簡潔凝練,字字珠璣,筆鋒精到,可分節分章讀,又可前后串聯讀,重建漢語風骨,重現漢語之美;小說關注自然風物、人神鬼畜,氣息古樸、奇崛鬼魅,有楚騷之風、巫儺之氣;是一部展現南方獨特地域博大精深、意蘊豐富的寓言小說;也是一部魔幻抒寫三川半自然生命、人物命運的地方志。
海外文壇
科爾森·懷特黑德再次獲得普利策小說獎
當地時間5月4日星期一,普利策行政管理人員達娜·坎迪通過視頻在Pulitzer.org上宣布了2020年普利策獎。小說獎頒給了科爾森“懷特黑德,獲獎作品是小說《鎳幣男孩》。小說通過兩名生在JimCrow的佛羅里達州男孩被判在一所噩夢般的學校就讀展開。這部小說去年也曾得到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的推薦,他評論道,這本書“是一本必讀之書,它詳細描述了種族隔離和大規模監禁如何撕裂人們的生活并造成了今天的連鎖反應”。懷特黑德此前因其2017年出版的《地下鐵路》獲得普利策獎,該書正由《月光》編劇導演巴里·詹金斯改編成亞馬遜系列。《地下鐵道》還曾獲得2016年度美國國家圖書獎,小說中文版由世紀文景出版。《地下鐵道》成為21世紀唯一一位同時獲得美國國家圖書家和普利策獎的小說家。懷特黑德畢業于哈佛大學,寫過六部小說,兩部非虛構作品。1999年處女作《直覺主義者》一經發表即引起廣泛關注。他創作題材廣泛,風格各異,被《哈佛雜志》稱為“文學變色龍”。2017年4月,他來到中國參加上海書展的活動,與讀者面對面,在上海科學會堂,懷特黑德舉行了一場自問自答式的分享會。
2020國際安徒生獎揭曉
北京時間5月4日晚8點半,國際兒童讀物聯盟官網宣布了2020年國際安徒生獎、IBBY-朝日閱讀促進獎、IBBY-iRead愛閱人物獎三大獎項。美國的杰奎琳-伍德森與瑞士的艾伯丁分獲國際安徒生獎作家獎、插畫家獎。阿根廷的機構“房子、搖籃、故事人”獲得IBBY-朝日閱讀促進獎。中國的朱永新與荷蘭的瑪麗特-托恩奎斯特獲得首屆IBBY-iRead愛閱人物獎。往年的國際安徒生獎都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童書展期間宣布,今年該展由于疫情原因取消原定時間轉為線上虛擬書展,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宣布本屆國際安徒生獎也延期至5月4日揭曉。國際安徒生獎由國際青少年童書聯盟于1953年在瑞士蘇黎世創設,其中,作家獎創設于1956年,插畫家獎設于1966年,每兩年頒發一次。需要注意的是,安徒生獎并非評選某部作品,而是頒發給某個作家或者插畫家的終身成就獎,一生只能獲得一次。2016年的國際安徒生獎作家獎為中國作家曹文軒。今年國際安徒生獎作家獎獲得者杰奎琳·伍德森出生于1963年,是美國當代知名兒童、青少年讀物作家,作品多次獲獎,包括2014年“國家圖書獎”。她也是美國目前極少數將非洲裔、女性、兒童、青少年讀物等標簽集于一身的作家。在獲得本次獎項提名后,她表示自己一直以來都關注著年輕讀者的內心,尤其是目前許多年輕人對未來抱有強烈的壓力感,失衡于自我與現實之間,而她最大的目標是希望用自己的寫作讓他們保持希望。
波伏娃未發表小說《難舍難分》將出版
據《衛報》《紐約時報》等多家外媒近日報道,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一部未發表作品即將在今年首次出版。這部名為《難舍難分》的小說講述了兩個年輕女子之間的一段“激情而悲慘”的友誼,并以對波伏娃最有影響的一段關系為基礎,并揭示了波伏娃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的成長過程。波伏娃在1963年出版的回憶錄《環境的力量》中,曾提及這部她已經放棄的小說。波伏娃寫作這部小說的時間是1954年,在她發表開創性女權主義論著《第二性》的五年后。她為此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然后拿給她的長期伴侶讓一保羅-薩特看。薩特的反應動搖了她。波伏娃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她同意薩特的評價。“這個故事,”她寫道,“似乎沒有內在的必要性,未能抓住讀者(指薩特)的興趣。”如今,波伏娃的養女兼文學遺產繼承人勒龐·德·波伏娃決定從她繼承的檔案中發布小說作品,《難舍難分》終于將要重見天日。這部176頁的小說將于今年秋天在法國出版,明年將在英國和美國出版。它講述了波伏娃早年生活的一個重要的章節,它與波伏娃對性別不平等和性別歧視的種種觀點密切相關。
最果夕日《愛的接縫在此處》簡體中文版上市
近日,最果夕日的中文出版方世紀文景繼《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后,出版了詩人又一重磅詩集《愛的接縫在此處》。《愛的接縫在此處》集結了圍繞“愛”的43首詩篇。沒有人與生俱來攜帶著愛,與生俱來彼此了解的人,更是哪里都不存在。縱然有相互理解的意愿,當伸出指尖試探的瞬間,便已是愛情的、溫柔的、體恤的、所有一切的終點。而在這漫無邊際的可能性中,我們,竟得以相遇。如果說《夜空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帶有些許厭世意味,就如譯者匡匡的評論“她揣著冷卻的心窩,對這個世界決絕地說著狠話,以為這樣就沒人注意她隱蔽的熾熱,圖謀著剝奪她的余溫”,那么《愛的接縫在此處》,則更多的是關于溫柔,關于愛與關懷。詩集關注細小事物、日常生活背后蘊含的巨大能量和新鮮啟示,最果的詩思精確、細膩、獨特,呈現出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年輕一代在社會化過程中,面對種種壓力和困境時產生的抒情沖動和思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