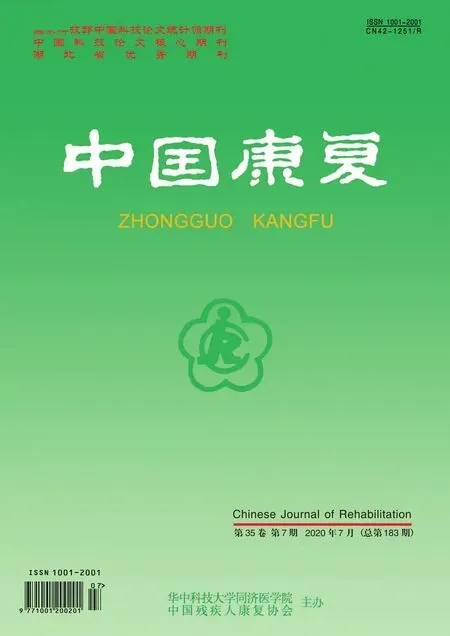1例重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康復治療體會
李磊,李靜,喻鵬銘,何成奇,何竟,王任杰,魏全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19, COVID-19)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播疾病,它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致病因子同屬β冠狀病毒,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現有研究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與來白中華菊頭蝠的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最為相似,核苷酸同源性達到85%以上[1]。COVID-19常見癥狀包括發熱、干咳、乏力,少數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肌痛和腹瀉等[2],重型患者易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急性心臟損傷和繼發感染[3],這些癥狀會導致COVID-19患者通氣血流(V/Q)比值失衡,呼吸順應性降低,分泌物潴留,患者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受限。物理治療中的體位管理、呼吸訓練、活動訓練、胸科物理治療可緩解患者癥狀,改善V/Q比值,提高患者的活動能力[4]。現就1例重型COVID-19患者的康復治療給大家分享,以期為一線物理治療師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患者劉某,女性,78歲,體重64kg,身高1.50m,BMI指數28.44kg/,因發熱15d于2020年2月12日入院。伴咳嗽,少量白痰,2020年1月26日接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后第3天開始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7.8°C,無乏力、胸悶,腹瀉等不適,予以隔離觀察。入院1d前新冠病毒核酸陽性轉入成都市公共衛生醫療中心重癥一科。入院胸部CT示右肺中葉、右下葉前、后基底段及左肺下葉見磨玻璃樣影、細網格狀影、斑點片影、條索影,密度欠均勻,邊界模糊。中性粒細胞百分比略偏高,為76.1%。既往合并有慢性支氣管炎病史20年;冠心病史20年,受涼感冒后偶有胸悶;糖尿病病史16年,血糖控制可;高血壓病史10余年,長期服用降壓藥物血壓控制在130/80mmHg;腎功能病史10余年,長期口服腎病藥物,近年伴有尿量減少,每天800ml左右;15年前左乳腺癌切除術,術后放化療治療,左上肢靜脈回流受阻,長期左臂水腫。臨床診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重型)[2];慢性阻塞型肺疾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2型糖尿病;高血壓2級極高危;慢性腎功能衰竭CKD5期;乳腺癌切除術后。臨床予以重組人干擾素霧化、達蘆那韋抗病毒,倍他樂克降血壓,氨溴索化痰,規律CRRT透析等對癥支持治療。
1.2 方法 根據物理治療評估結果,該患者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呼吸困難、氣道廓清能力下降、分泌物潴留、通氣/血流比值失衡、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降低、輕度焦慮、輕度抑郁。康復治療目標為:緩解呼吸困難,提高氣道清潔能力、改善通氣/血流比值、提高活動能力、緩解焦慮和抑郁狀態。康復治療措施:①教育:給予患者對于COVID-19疾病的正確認識,如何正確和堅持用藥,并進行放松訓練等心理干預[6]。②體位管理:白天間斷進行仰臥位→側臥位→俯臥位通氣。仰臥位時,床頭抬高40~60°,在腘窩下墊一枕頭,充分保持下肢和腹部肌群的放松,30min/次,3次/d[7]。側臥位按照右側臥位→左側臥位進行,每2h一次,側臥位時在背部墊楔形枕,上方上肢下放置軟枕進行支撐。俯臥位的目的促進塌陷的肺泡復張,改善通氣/血流比值,提高呼吸的順應性,并幫助外周細支氣管分泌物引流[8],俯臥位時,頭部偏向一側,避免眼睛和呼吸導管受壓,2h/次,2次/d。③呼吸控制:采取舒適放松體位,以半臥位為主,訓練時放松肩頸部輔助吸氣肌群,經鼻緩慢吸氣,經口緩慢呼氣,并注意觀察下胸部擴張情況。在物理治療師的指導下由患者自行完成,以緩解氣短癥狀,10min/次,2次/d。④轉移訓練:床上轉移到椅子→椅旁的站立→椅旁的踏步進行轉移訓練,20min/次,2次/d。⑤胸廓放松訓練:采用雅各布氏漸進性肌肉放松法[9],患者在物理治療師的言語指導下,自腳趾到頭部依次收縮放松身體的每一部位,10 min/次,1次/d。⑥氣道廓清技術:教會患者使用主動循環呼吸治療技術(active cycle of breathing techniques,ACBT),每小時進行一次。教會患者使用震蕩呼氣正壓裝置Acapella,阻力設置為3檔,8~10次/h。在俯臥位和側臥位時,由物理治療師沿著支氣管走行的方向,進行手法或機械式扣拍振動,2次/d。患者對上述治療方案知情同意,符合國務院頒布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10]。
1.3 評定標準 患者在康復治療前(2020年2月15日)、出院時分別采用標準化合作能力評分(5 standardized questions for cooperation,S5Q)[5]、Borg呼吸困難評分、呼氣峰值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PEF)、莫頓活動指數(The de Morton Mobility Index,DEMMI)、改良Barthel指數(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Scale,SDS)進行物理治療評估,并對患者的呼吸支持、肺功能報告、胸部CT進行前后對比。①S5Q:讓患者回答5個標準問題,每個問題為1分,最高5分,≥4分時患者合作能力良好。②Borg呼吸困難評分:無呼吸困難0分;輕度呼吸困難1~3分;5~7分中度到重度呼吸困難;8~10分非常嚴重呼吸困難。③PEF:采用袖珍式呼氣峰值流速儀進行評估,大于180L/min時,咳嗽效力好。④DEMMI:評估患者活動能力,包括床上活動、椅子活動、靜態平衡、步行、動態平衡5個大項,15個項,最低0分,最高100分,分數越高活動能力越好。⑤改良Barthel指數:評估患者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包括進食、洗澡、修飾、穿衣、大便控制、小便控制、如廁、床與輪椅轉移、平地行走、上下樓梯共10項內容,總分100分:>60分為輕度依賴,生活基本自理;41~60分為中度依賴,生活部分自理;0~40分為重度依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信度和效度高,評定方法較為簡易。⑥SAS和SDS:分別評估患者的焦慮和抑郁狀態,最低0分,最高100分,焦慮評定臨界值為T=50分,抑郁臨界值為T=53分,大于T值存在焦慮和抑郁,分數越高,焦慮和抑郁傾向越明顯,小于T值屬于正常群體。評定結果見表1,2。
2 結果
在多學科協作下,經過21d物理治療,患者于2020年3月6日兩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康復出院。康復治療前、出院時物理治療評估見表1,呼吸支持、SPO2、氧合指數、肺功能見表2。結果顯示,患者吸氧方式由40%經鼻高流量吸氧轉為自發吸氧,氧合指數由282提高到429,呼吸困難分級由7級降為3級,肺功能中的第1s時間肺活量占預計值從52%提高到72%,患者DEMMI評分由48分提高到74分;改良Barthel指數由50分提高到72分,提示患者的自主活動能力大幅提高;SAS和SDS分數分別從60分和57.5分下降到40分和35分,提示患者心理狀態也有所改善。

表2 患者康復治療前、出院時呼吸參數比較

表1 患者康復治療前、出院時物理治療評估比較
治療前的胸部CT為:右肺上葉、中葉、右下前、后基底段及左肺可見斑片、磨玻璃影,密度不均,邊界模糊。出院時胸部CT為:左肺下葉見少量斑片影、磨玻璃影,密度欠均勻,邊界欠清,對比之前吸收明顯。治療前痰液為P1型,粘痰,肺部聽診集中于外周細支氣管,無法自行有效咳嗽。出院時患者肺部聽診無痰鳴音,胸部CT顯示病變明顯吸收,提示該患者肺部情況較治療前明顯改善。
3 討論
新型冠狀病毒對人體有很強的傳染力,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在相對密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于高濃度氣溶膠的情況下,還存在氣溶膠傳播的可能性[2]。COVID-19患者的病死率較低,但重型及危重型患者的病死率較高,最近一項對于52例的重癥患者研究發現重癥患者死亡率超過50%,存在基礎疾病和合并有ARDS的老年患者(>65歲)死亡率更高[11]。本患者并發癥多、年齡大、病情加重死亡風險高,結合《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呼吸康復指導意見》第2版推薦建議[12],對該患者進行了早期心肺康復治療。
該患者在物理治療開始前呼吸困難評級7級,氣短明顯,神志清楚,合作能力好(S5Q=5分),在經鼻高流量吸氧的基礎上,選擇呼吸控制(Breathing control,BC)和放松體位管理(床頭搖高40~60°坐位,在腘窩下墊一軟枕)緩解氣短癥狀。大多數COVID-19患者以發熱、咳嗽和氣短癥狀為主,分泌物較少,而該患者有分泌物集中于外周細支氣管,分泌物粘稠,可能是因基礎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引起,該患者咳嗽效力弱(PEF=160L/min),無法自行咳出痰液,在結合藥物化痰的基礎上(氨溴索霧化和靜滴),物理治療采用了ACBT、震蕩呼氣正壓(oscillatory positive expiratory pressure,OPEP)、體位引流、手法和機械式胸部扣拍/震動幫助患者進行排痰,單次可排出痰液2~5ml,當把痰液移動到大氣道,患者進行自主咳痰時,應用密閉的塑料袋遮擋,避免造成病毒向外傳播[4]。物理治療師在進行胸科物理治療操作時應佩戴頭罩,做好三級防護,防止職業暴露。除上述胸科物理治療技術外,第二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呼吸康復指導意見推薦使用高頻胸壁振動(high frequency chest wall oscillation,HFCWO)幫助患者排痰[12],因無需治療師長時間與患者接觸。
因隔離病房場地的限制,無法對該患者進行6分鐘步行測試評估心肺耐力,DEMMI活動量表在評估亞急性住院期老年患者活動能力方面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13],可較準確地反映該患者的活動能力和功能狀態。經過21d的早期活動訓練和轉移訓練,患者的DEMMI評分從48分提高到74分,改良的Barthel指數評分從50分提高到72分,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從中度依賴改善為輕度依賴,提示早期活動和轉移訓練可有效提高該患者的功能能力,但應注意活動時應充分保證患者氧供,SPO2較基線值下降不超過4%,同時不引起氣短和疲勞癥狀。
部分COVID-19患者在隔離治療期因無法與外界接觸以及對疾病的未知性容易出現焦慮、憤怒、抑郁、失眠、恐懼,甚至放棄治療的想法[14],本患者在物理治療干預前呈現中度焦慮(SAS=60分)和輕度抑郁(SDS=57.5分),不良的心理狀態易導致免疫力的下降,會影響疾病的恢復,可采取深呼吸放松訓練,軀體活動,根據患者能接受的程度,客觀如實交代病情和外界疫情,協助與外界親人溝通,轉達信息,盡量改善環境適宜患者的治療需求等方式改善患者心理狀態[15-16]。
通過本病例可看到物理治療對重型COVID-19患者的有效性,但應注意針對COVID-19患者需采取謹慎的個體化康復治療,物理治療師應在做好充分自我防護的前提下根據物理治療的評估結果有序開展工作,以減少患者的組織器官進一步受損為目標,改善生命體征,提高活動能力,為患者轉入普通病房或出院后的繼續康復治療奠定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