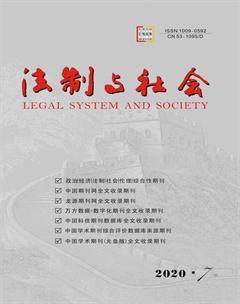繼子女、繼父母間扶養關系的認定分析
關鍵詞 扶養關系 繼父母子女 認定分析
作者簡介:葉思剛,廣東三民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合伙人、副主任、廣東股權交易中心掛牌審核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民商事。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101
扶養關系的認定涉及到很多法律內容,尤其是在繼承權的確定上,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如果不具備扶養關系的成立條件,那么一般情況下繼子女就不具備遺產繼承權,但就當前法律關于扶養關系的具體認定而言還存在不明確性,以至于經常出現繼承權相關糾紛案件,尤其在當下社會轉型時期,再婚家庭較多,明確扶養關系的認定標準,更對家庭穩定以及當事人權益維護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應結合《民法典》的要求對扶養關系加以詳細而全面地探析,以促進繼父母子女扶養關系認定的準確性、合法性。
一、繼父母子女扶養關系認定的相關法律規定
在對扶養關系認定分析時,要先明確繼父母子女關系的法律定義,其同樣屬于親屬關系,如果出現父母離異或父母間一方死亡,經歷再婚之后,繼父母與繼子女就可以依據相關法律規定構成該親屬關系,這也是扶養關系認定的基礎內容。當然,這里所說的扶養指的是親屬法上的扶養,雙方主體必須具有特定親屬關系,為法律限定范圍之內,所以要將之與一般的道義上的扶養區別開。《民法典》明確規定,具有扶養關系的繼父母和繼子女間存在合法繼承權,所以扶養關系的明確認定有其必要性,更有助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一般來說,對扶養關系的認定主要從“承擔撫養義務”“存在足夠長度共同生活時間”“承擔教育責任”等多個方面入手,但因為法律規定并未對其展開明確標準限定,所以在具體實踐認定中常出現各種問題,比如很多時候審判機關在認定時只將目光置于繼子女年齡上,如果構成繼父母子女關系時繼子女尚未成年,即年齡少于18周歲時,可以認定為扶養關系,而年齡超過18周歲時,就不能認定扶養關系,因為此時繼子女已為成年人,撫養義務不再存在,也就不能認定扶養關系[1]。這種扶養關系認定并未充分考慮關系認定的全面性,很容易出現各種不當問題,而更應重視其中撫養與贍養的共性,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生活上的維護與供養等作為關鍵標準。
二、案例分析
以筆者代理的某遺產糾紛案件中涉及扶養關系認定問題,其中就重點以年齡認定問題的解析為關鍵點,具體案情如下:
陳某去世后,未對其自身遺產留下遺囑或遺贈協議,其親生女兒起訴陳某再婚配偶張某、繼女李某1和李某2。根據當時的《繼承法》規定,形成扶養關系的繼子女與親生子女同樣具有第一順序繼承權。該法院認為,《繼承法》第十條規定:“本法所說的子女,包括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養子女和有扶養關系的繼子女。本法所說的父母,包括生父母、養父母和 有扶養關系的繼父母”,該法條使用了“扶養”一詞,其立法本意為“撫養、贍養”,既包括成年子女對父母的贍養,也包括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本案中,陳某與張某 1 結婚時,李某 1 年滿 19周歲,已成年,李某 2年滿 17 歲余,即將成年,陳某對她們不再具有撫養的必要,因此李某 1、李某 2與陳某之間均不成立有扶養關系的繼子女關系,不屬于陳庭耀的法定繼承人;但是另一方面,被告方提交的多份親屬、鄰居的證言、照片等物證,均證明李某 1、李某 2 姐妹對陳某扶養較多的事實。原告雖對上述證人證言有異議,但也并無反證否認該事實。且陳某 去世時已 83 歲高齡,當時張某 1 也已 84 歲,梁某又長居外地,故陳庭耀晚年主要由李某 1、 李某 2 扶養符合常理常情。故此,法院雖然認定李某1、李某2與陳某間并不構成扶養關系,不具備法定繼承權,但依據《繼承法》第十四條規定:“對繼承人以外的依靠 被繼承人扶養的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或者繼承人以外的對被繼承人扶養較多的 人,可以分給他們適當的遺產”,仍為李某1和李某2給予適當的遺產繼承。
該案中,法院僅考慮年齡作為扶養關系的認定標準顯然是不全面的,就我國國情而言,雖然法定成年為18周歲,但很多子女仍需要父母長時間的扶養,所以該認定需適度延長,在加上李某1和李某2為陳某提供長時間的生活照料,盡到了贍養義務,在扶養關系的認定上應結合具體情況給予更全面的分析考慮。所以筆者認為,在扶養關系的認定中,應綜合考慮共同生活時間、生活照料、關系維護等多因素內容,以此保證扶養關系認定合理性[2]。
三、繼父母子女扶養關系認定的適用內容
在對繼父母子女扶養關系認定時,要結合實際生活、教育狀況等綜合考慮,而不能單純以年齡為界線“一刀切”,本文結合案例分析及相關法律內容,對扶養關系認定的適用加以明確,希望能在司法實踐中提供一些參考。
其一,在繼父母子女扶養關系認定中,繼子女未成年雖然是重要條件,但不是扶養關系的唯一條件。正在案例中陳某與張某再婚時,繼女一個已經成年,另一個也接近成年,若按年齡劃分,法律上的“扶養”關系基本不存在,但也要考慮到我國實際情況,子女18歲之后多會仍在求學,并且無自我生活能力,依舊以父母撫養為主,在共同生活中,陳某為繼子女生活、教育、成長、結婚各個方面都進行了照顧,不能因繼子女已年滿18周歲就否認陳某與李某1與李某2存在法律上的“扶養”關系,而隨著子女的成長,父母年老,李某1和李某2也在陳某年邁時為其提供悉心照料,生養死葬,這種情況下不能僅依靠單純的年齡限制否定扶養關系的存在。
其二,扶養關系認定標準中,應將物質幫助作為認定的客觀條件。無論是在繼子女對繼父母的贍養亦或是繼父母對繼子女的撫養,都要有一定的物質支持與生活照料,比如承擔生活費用、為繼子女提供教育資源等,只有充分滿足這一條件才真正認定扶養關系,正如陳某為繼子女提供生活及教育費用,繼子女也為陳某提供晚年照料,以此構成扶養關系的客觀標準[3]。在這方面有些問題需要考慮:在持續時間以及共同生活上,如果對其嚴加限定,顯然是比較困難的,時間起止以共同生活范圍等,都無法準確判斷,再加上再婚家庭中關系的復雜性,也無法單純從三五年生活時間的標準加以明確,所以就物資支持而言,應從宏觀角度考慮,以盡到撫養或贍養義務為基礎,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綜合判斷。
其三,除物資幫助外,重視情感交流在扶養關系認定中也是重要條件,其應是主觀認定的核心點。單純物質經濟支持無法滿足扶養關系的認定要求,繼父母與繼子女應具共同生活、扶養認可方面的情感思想,才能保證扶養關系不為經濟物質所把控。一方面,從共同生活上考慮,這是生活照料、教育培養等家庭活動開展的基礎,如果繼父母僅為繼子女提供生活和學習的經濟支持而不與其共同生活,沒有情感交流,扶養關系就喪失其應有內涵,當然,共同生活也不是要求繼父母與繼子女完全生活在一起,保持物質支持與情感交流應作為其中關鍵要點。另一方面,從扶養認定上考慮,主觀扶養的意愿同樣會對扶養關系產生一定的影響,處于共同生活狀態下,并提供一定的物質支持,但是繼父母抱以惡劣態度,不情愿撫養繼子女,或是繼子女不注重老年父母的心理狀態,忽視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等,同樣也是撫養與贍養的缺失,“精神撫養”或是“精神贍養”需作為扶養認定的重要參考點[4]。
其四,扶養關系的認定需根據實際情況綜合分析,對于一些特殊家庭生活狀態也要全面考慮。比如,如果繼子女已經獨立生活,但是因為生病等原因而出現生活狀態艱難的情況下,無力維持正常生活,也難以贍養繼父母,而繼父母為其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持,這種情況下也應視為扶養關系,是繼父母對繼子女的扶養。如繼子女因讀書、工作、結婚等無法維持與繼父母的共同居住,這種情況并不對其扶養關系的認定造成影響,保證繼子女成年獨立后與繼父母之間維持良好的情感交流與互動,能夠滿足繼父母情感需求,給予繼父母一定物質支持,這樣的情況也可以認定繼父母子女間形成扶養關系。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繼父母、繼子女扶養認定上,雖然《民法典》并未給予明確標準,而且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在新時代背景下,簡單以年齡作為判定依據已難以滿足當前時代需求,也不符合《民法典》的立法原意,故此,應從物質幫助、情感交流、共同生活等多個方面作為認定扶養關系的標準,為解決當前繼父母子女繼承權問題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歐陽翠.繼父母子女“有扶養關系”的認定標準[J].法制博覽,2020(9):186.
[2]徐鑫.關于繼子女、繼父母間扶養關系的認定[J].法制與社會,2016(10):58.
[3]吳國平.論繼父母子女關系法律規制的立法完善[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17(1):38.
[4]陳堯.我國繼父母子女間形成扶養關系的認定標準[J].品牌研究,2018(4):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