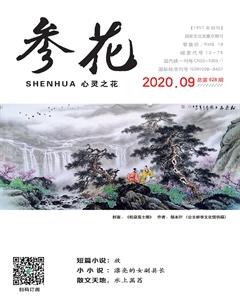遺失的花朵
摘要:在張愛玲軼作《郁金香》問世之際,學者就其小說中的形象、筆觸探討過張愛玲創作的風格和特點,《郁金香》也被認為是張愛玲創作高潮期的一個收尾之作。它在題材、人物、描寫上都承接了以往文章的風格,小說中將青年女性處于情感糾葛下的內心隱秘在以往情感的基礎上進行更加細膩的描繪,尤其是在表現女主人公的性別訴求上,體現出女性作家愛情創作中敏銳的觀察力和獨到的見解。
關鍵詞:《郁金香》 女性心理 愛情創作 性別訴求
張愛玲的軼作《郁金香》是2005年經吳福輝學者及博士生李楠發現的,發表于1947年的《小日報》上,其文風以及內容都與張愛玲以往的筆調十分貼切。這篇小作的題目為“郁金香”,不由得令人想起《紅玫瑰與白玫瑰》《花凋》一類的作品,同樣是以花朵命名,同樣描寫了在愛情中令人心碎的花一樣的女子,我們依舊沉迷于張愛玲筆下“千瘡百孔的感情”故事,沉迷于她忽明忽暗的敘述描寫,沉迷于那些躊躇于金玉和悲風的癡情男女。不得不承認的是,更為吸引人的是這些看似經歷內容相似的故事中卻各自存在濃得化不開的情調和特色,如果說《紅玫瑰與白玫瑰》是一曲高低起伏的挽歌,那么《郁金香》則是一首連綿凄涼的江南小調,淡雅、哀傷、令人唏噓。下面我們將這篇小作細讀加以分析。
一、女性的心思——明暗的花朵
將小說以隱喻的方式加以呈現是張愛玲一貫的表現手法。設置意象也是張愛玲小說給人虛實結合奇妙感覺的原因,而“蒼涼”更是張愛玲小說的一種美學風貌,因此,張愛玲筆下的人物總是籠罩著淡淡的憂愁,即便是描寫喜悅、嬉鬧場面也會有一絲悲涼的氣息,女性形象更是如此。在小說《郁金香》中,金香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丫鬟,她的名字“金香”與小說的標題“郁金香”呼應,那么作者究竟是想表達一種怎樣的意義呢?
我們聯想到《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經典語句:“……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圣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女性在張愛玲的筆下一如既往如同盛開的鮮花,或貞潔或熱烈或明朗,都是綻放的不同方式,這一點在《郁金香》的開篇更是明確地表達了出來,“那時候女太太們剛興著用一種油漆描花,上面灑一層閃光的小珠子,也成為一種蘭閨韻事。”首先這里就寫出了這個時代的女人們是愛花的,她們愛的不僅僅是花,更是一種“花樣”的精巧與美麗,因此描花上都是閃光的珠子,不僅如此,她們更為細心精巧的是:“鞋頭畫了花,沙發靠墊上也畫了同樣的花。”然而,這一切的女性獨有的細密與心思卻只能隱藏在陰暗下面了。通過這些描述,我們漸漸能領悟到張愛玲用淡淡煙霧勾勒出的女性繪圖了,女人天生是敏感而細心的,她們會在自己身上或周圍細節上下功夫,小說中的金香便是這樣一個女孩。首先,她的貌非常能契合她的名兒,擁有名副其實的花朵般的“紅顏”;她的穿著也費了一番功夫:“穿著套花布的短衫長褲,淡藍布上亂堆著綠心的小白素馨花”。不僅如此,她心思細膩且心靈手巧——她會明白自己如今處境的不易而寸步留心,她會在心愛的人看見之前搽一下紅胭脂,會自認為給心愛的人精心準備自認為最為大方得體的東西,在常人眼中姑娘的那些機靈、聰敏便盡數體現在了她身上。張愛玲如此便把日常女性中最為隱秘的心思表現了出來,她稱之為“女性的手觸”,女性就是這樣一種生物,費盡腦力與心思如全身長了觸手一般的敏感。但是文中的金香所處狀態并非一般女性的日常狀態,她是一個處于戀愛中的女孩,更為特殊的是,她是一個與“大舅老爺”陳寶初相戀的婢女,顯然她心里的的確確是明白自己的身份與處境是不能同心愛之人在一起的,但依然愛得深切。她明知不可為,卻依然為之,而且花盡心思,費盡氣力。但這心思得來的效果卻是“實在有一點寒酸可笑,也不大合用”,結局更是波折:先是因為麻煩而忽略了它的作用與信紙一類的東西放在一起,而后便在亂七八糟的抽屜中被翻出且一看見心里就一陣凄慘,隨后想了一個曲折的辦法總算送走了——夾在小說的高潮那頁,希望被人取走并扔掉,本抱著一點能夠被懂得的人發現引起一些惆悵的想法,后面也衍生成了十分無聊可笑的了。這一段描寫十分貼切傳神,向讀者展現出了男性視角下的女性心思是如何被對待的,贈物一波三折的去處也體現了男性心理下的處理機制和情感走向,性別轉位體驗之間不免帶有殘忍的意味,這也表現出作者敏銳的觀察力和獨特的描寫手法。
看到如此,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心思契合文本便是——處于明暗之中的,乍一看,他們如同閃著珠光的花朵一般,明朗精致,實則暗淡無光,隱匿在黑暗之中。女性看似美麗、朦朧又精巧的心理在男性粗糙視角的對比下顯得十分卑微,這里也象征著小說中的女性金香幻滅的人生。在小說中還出現了其他女性形象,如阮太太、老姨太、閻小姐等,描繪刻畫得也是十分獨特以及別有用心。如果說金香在文中的描寫中有“明”的一面的話,那么阮太太則是徹底的“暗”的對照,文中的阮太太出場是這樣的:“面色蒼白,長長的臉,上面剖開兩只炯炯的大眼睛。”有關她的幾處描述也是十分暗沉的,如“一醒就撳鈴叫人”“照例沉著臉冷冷地叫一聲‘媽”“她是一個無戲可演的繁漪,仿佛《雷雨》里的雨始終沒有下來”“她因為瘦,穿襪子再也拉不挺,襪筒管永遠嫌太肥了,那深色絲襪皺出一抹一抹的水墨痕”“她雖然終日在家不過躺躺靠靠,總想把普天下的人支使得溜轉,”再加上文中經常出現卻從未露面的阮先生,缺席的形象總是引人深思,我們便可這樣下結論:阮太太是一個填房,家中丈夫常年缺席,她是已婚多年,平日里的形象居然是冷漠、薄弱、孤單,可想而知這個女人是已經獨守空房終日疲倦不得面了,這與小說中屢次描繪的女性細密的心理相呼應,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女性在巧弄心思后終究疲倦,在家無所事事使喚他人,無非是求存在感罷了,但早已挖空心思的她心如死灰儼然一個“無戲可演的繁漪”了。
二、變換的敘述角度——黑白兩面
張愛玲的敘事角度常為第三人稱,似乎以上帝的目光注視著她筆下的癡男怨女們,不過在敘述方法上卻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在作品中呈現出不同的敘述效果,“某些場景既似主人公視覺又含有敘事人目光,這種敘事角度的有意混淆,是張愛玲小說的重要技術特點”,研究者早已開始重視張愛玲小說中敘述視角的獨特性。不同主觀敘述視角的呈現,會使得小說中的情景及矛盾更為豐富化、立體化。而小說《郁金香》展現出的獨特敘事角度也十分值得探究。
小說總體的敘事視角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由“次日,他獨自到閻家去赴宴,寶初就沒去”劃分開來。我們可以看出,前半部分的敘述視角主要是在金香身上,其間夾雜著寶余和其他人的描寫,后半部分從“寶初就沒去”這里開始,才真正轉化為以寶初為主的敘述視角,真正開始以寶初為中心勾勒出文中人物后半生的命運。那么作者這樣寫的意圖和作用又是怎樣的呢?縱觀全文,我們可以在小說結尾處發現一句這樣的話:“這世界上的事原來都是這樣不分是非黑白的嗎?”背景是他聽見閻小姐說金香是那個原先喜歡寶余的金香,而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的確著重描寫了寶余與金香的嬉鬧,從金香的細密心思寫起,到寶余三番五次逗弄金香,我們眼中望到的便是一個淘氣的“二舅老爺”與丫鬟金香打鬧的鏡頭和場面,再加之在小說前半部分里寶初的形象為一個“靜悄悄的人”,他在二弟調戲心上人金香時也只能暫時不作聲,實在看不下去了才呵斥一句,可想而知,寶初本身在家中也是處境艱難不敢放肆的,加上他唯唯諾諾的性格理所當然在金香忙碌又被動的生活中放不了光彩,他與金香的愛情也未被人知曉過,一直埋藏在兩個人中間的地底深處。而下半部分中寶初敘述視角的呈現,給人以恍然大悟之感,原來他們竟是一對,但即便是在房間里單獨相見時,他們依然沒有表現出愛人之間的應有的甜美和親密,看到的只有金香敏感卻怯弱的心思以及寶初斷斷續續、猶猶豫豫的承諾。失望和懦弱徘徊在他們的影子里,使得兩個相愛的人就這么被迫分離。
全文從開篇到末尾,寶初和金香兩個本應該真正相愛的人之間碰觸的片段還不及寶余對金香的調戲之多、印象之深,也難怪會發生最后的黑白顛倒了。他們之間的愛情暗得不能再暗,隨著那夾進小說里的玻璃紙罩子一起曲折地消散了,他最后連她的一面都沒有見上,有的只是一道極真切的影子,仿佛窗上鑲著的一枝鐵梗子的花,一瞥就隱沒了。到頭來,寶初與金香兩個人的愛情便在他人的調侃中失了真,徹底沒入黑暗中了。小說中由于兩部分文本敘述視角的不同,而使得寶初和金香兩個人的地下情更為莫測和悲情,不同視覺的轉換,讓讀者將兩個人的錯過與埋沒體會得更為深刻,從而更能領悟張愛玲筆觸之下反復想訴說的悲涼的愛情;也將寶初這個封建家庭背景下成長的男子對愛情猶豫、懦弱的性格刻畫得更為全面,我們并不是在抱著批判封建的態度去看待小說中人物的命運,我們所感受的是時代風云下人物的悲、真、怯,體會那個年代里殘缺與暗淡下的真情。
《郁金香》問世以來已經過了十余年了,研究者也專門撰文列舉其為張愛玲軼作之證據,也有研究者就這篇小說中的細節、人物名稱等與張愛玲其他作品加以對比,但是還有一些人依舊認為這是一篇仿作,拋開這些不談,我們僅細細品味這則小說,女性心理之含蓄、優美或大戶家庭之紛爭、起落無不在情節中虛虛實實為我們展現一幅淡影朦朧之蒼涼悲景,而我們所做的除了繼續考證和探索發現以外,更為重要的是沿著這條道路去領會、感受,感受這獨有的女作家留下的每一絲風情。
參考文獻:
[1]馬春景,金宏宇. 《郁金香》為張愛玲所作真偽辨[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0(04):220-226.
[2]沈佳梅.郁郁金香 悠悠流年——張愛玲軼作《郁金香》解讀[J].語文學刊,2006(17):87-89.
[3]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51、222.
[4]許子東.張愛玲小說中的敘述角度混淆[J].文藝理論研究,2018,38(05):77-90.
(作者簡介:陳奕希,女,碩士研究生在讀,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