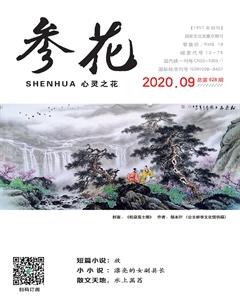故土情結:客家文學評論的文化心態視角
摘要:本文以布迪厄“生存心態”概念為切入點,充分審視客家文學的故土情結,尋找客家文學評論中的文化心態視角。在此過程中,發覺在不同歷史時期下,評論心態出現了從認可型、反思型再到超越型的演變。
關鍵詞:客家文學評論 文化 心態
從“少小離家老大回”,到余光中的鄉愁,這種難以擺脫的故土情結在長期顛沛流離的客家族群身上體現得尤為顯著。從客家文學創作開始,便有著顯著的故土情結烙印,故土情結很自然地延伸到了客家文學的評論中,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獨特的文化心態視角。
一、文化心態觀照下的故土情結
客家文學評論的文化心態需要引用布迪厄的結構動力學中提到的“生存心態”概念,與傳統理論心態概念分離,形成行動者動態精神生命的存在形態。“心態”是流動不居、充滿活力的精神生命存在形態,既有持續穩定的特點,又有動態流變的特點。運用到客家文學評論心態解釋中,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心態,這一心態也可以引入布迪厄關于穩定和動態矛盾統一的雙重特性。
在文化心態的觀照下,文學評論的故土情結一方面從穩定性出發,在創作機制層面上挖掘作者在創作心理學上的穩定特質;另一方面,從動態性出發,探尋在環境的影響下呈現出來的對于故土情結心態的動態演變。程賢章文學書寫的鄉土情結評論、鐘理和文學創作的原鄉情結評論都是在文化心態觀照下的結果,且具有典型性。在張炯主編的《新中國文學五十年》中,因寫作中鄉土味濃厚,將程賢章、賈平凹、劉紹棠等作者劃歸為地域文學中的鄉土派,程賢章立足的即為鄉土客家的寫作。曾令存《客家、文學、禪——與程賢章對話錄》中收錄的程賢章的談話也印證了鄉土情結的發現——“沈從文也好,賈平凹也好,他們的創作都不能離開自己的土地,那是一種割舍不下的鄉土情懷。我最先也不知道什么是‘客家文學,而只是以一種鄉土情懷進行創作。”大陸對于臺灣作家鐘理和研究主題集中在命運悲情意識、原鄉情結、傳統文化習俗等問題上。藍天、蔡登秋先后指出,鐘理和原鄉情結研究中簡單地把原鄉等同于祖國大陸偏離了作者創作的真實心理,需要充分考慮到鐘理和客家人身份以及具有的源于中國傳統鄉土族群觀念的臺灣客家人原鄉意識。在此基礎上,再來探尋鐘理和超越客家人原鄉意識的真實創作觀念。
二、不同歷史時期下文化心態的演變
歷史環境的改變和社會風氣的變化,甚至作家創作都對評論心態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客家文學評論中,評論家的客籍或非客籍身份、個人性格、接受文學理論教育以及所處社會歷史背景等方面的差異,不同狀態的文化心態得以呈現出來,從評論心態的情感傾向入手,可以歸納出一定的規律性,并展現出不同的評論行徑。客家文學帶有故土情結的評論心態可分為認可型、反思型、超越型,三者之間呈現出互動性發展態勢。
(一)以黃遵憲詩歌評論為代表的認可型心態
這種類型的評論心態與早期客家文學的評論實踐接近,致力于挖掘客家民俗的古樸特質,帶有很深的客家身份認同感或推崇感。黃遵憲是晚清著名的愛國詩人,自小深受客家民謠、山歌的感染和熏陶,以至于后來在文學道路上極力推崇客家山歌且做出了高度評價。在他創作的詩歌中,充分地吸收、借鑒和轉化了客家歌謠。邢麗鳳在黃遵憲詩歌評論中認定“黃遵憲詩歌與客家歌謠的審美互動,體現了詩人將中國詩歌傳統與民間優秀形式融會貫通,進而推陳出新的創造意識與文體追求”。在輯錄整理客家歌謠過程中,黃遵憲根據自身詩歌創作實踐,提煉出“我手寫我口”的創作理論,提倡直抒胸臆,不拘泥于格律用典,如客家歌謠般將自身情感無阻礙地抒發出來。因此,黃遵憲詩歌中充滿了客家人文精神景觀的審美呈現,形成了直接的文化透視,并在詩歌的現代化進程中有一定的影響。周曉平、邢麗鳳等展開黃遵憲評論活動遵循了認可型態度,遵從了作者的視野與感官,致力于感受詩歌帶來的清新純樸的客家民風。這類評論心態并不局限于早期的評論實踐,張貴泉評論吳爾芬小說《雕版》時強調,“他用小說家獨有的銳力,挖掘出潛存在古雕版印刷中未被人挖掘的客家人的精神本質——人的精神”,也秉承了認可型評論心態。在客家文學評論中,有一部分評論家是出于提煉客家文化的目的而展開的文學評論活動,這類研究也可以歸結于此類心態。如段馨君的《臺灣客家文學中的客家婚禮儀式》,對臺灣客家文學作品《寒夜》《笠山農場》《相親》與《福春嫁女》等展開評論,運用了布西亞的“模擬”和葛特瑪的“本文與詮釋”等概念,但最終目的在于提煉臺灣客家婚禮儀式的變更,也遵從了認可型評論心態。
(二)以張資平小說評論為代表的反思型心態
反思型評論心態與一定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相關,在現代化全面推廣的啟發下,以反思的意識對客家傳統中潛在的不恰當習俗展開批判。20世紀初,為了與封建文化徹底決裂,進步作家接受西方先進的民主與科學理論,致力于號召個性解放主題,在封建婚姻陋習的抵制中扛起爭取婚姻自由的大旗。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張資平更多關注到的是自小生長的客家地區存在的某些封建習俗給人們帶來的傷害和苦痛,如《梅嶺之春》中“童養媳”保瑛在追求愛情中遇到傳統風俗的重重壓力。張資平在創作意識上與其學術背景息息相關。李長之在《張資平戀愛小說的考察》一文中曾指出,和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同期作家相比,張資平展現出真正“受過自然科學的訓練”,真正“干過自然科學的工作”。聯系到國外留學生身份和地質自然科學專業背景,在張資平的寫作中,現代科學意識和故土情結形成了一定的張力結構,這一張力結構也形成了反思的導向。崔向敏對張資平小說的評論中指出:“(張資平小說)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揭示出鄉村婚俗壓抑人性、阻礙婚姻自由的一面。”崔向敏認為張資平的客籍身份使得反省中做出的人性剖析交織在故土習性中。
(三)以譚元亨小說評論為代表的超越型心態
認可型和反思型心態形成一對具有張力結構的矛盾體,兩者之間相互對立、碰撞和互動;超越型心態建立在前兩種心態的基礎之上,巧妙地將兩種力量化解并結合起來,就如主觀與客觀被化解并統一一般建構成完整的心態結構。隨著現代化程度的加快,現實矛盾和心靈迷失凸顯,個人價值的找尋與回歸成為主題。評論家的知識結構也漸趨完善,越來越多學者關注到客家文學范疇,并能夠靈活地運用文學理論開展評論活動。在社會和學術雙重背景推動下,這種心態融合了認可型心態的深厚情感和反思型心態的審慎思考,直面客家文學本身,形成深沉的個人情感體悟,實現評論家個體價值和所處社會價值的深刻嬗變。劉國鈺對譚元亨《客家魂》的評論展現了超越型心態的傾向,一方面通過解析《客家魂》中婚嫁、喪葬禮俗等獨特民系風俗的嫻熟描寫,蘊含著對客家民系的深刻了解,體現了譚元亨小說創作中對客家文化的推崇和對客家地域鄉土風情的溫情留戀;另一方面也充分關注到作品中滲透出對客家傳統文化不成熟的反思,包括傳統文化對客家女性的不合理約束,客家文明在傳承中的遺落。此外,劉國鈺還特別指出,客家傳統生存狀況中女性教育機會的缺失或不平等,停滯了女性意識覺醒的腳步,在譚元亨《客家魂》中卻忽略了這一現象,客家知識女性的塑造,“把客家女子惡劣的生存環境轉嫁于生命意識追尋的那坎坷的道路之上了。”當前的評論實踐不能看作超越型心態的完成,更多的是評論家個體的有效嘗試。超越型評論心態的實現和客家文學評論話語建構密切相關,并需要漫長的歷史階段來完成。
參考文獻:
[1]劉國鈺.譚元亨與《客家魂》論[D].廣西師范學院,2011.
[2]邢麗鳳.黃遵憲與客家民間文化[D].山東師范大學,2003.
(作者簡介:曾熙,女,碩士研究生,江西環境工程職業學院,助教,研究方向:文藝學)(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