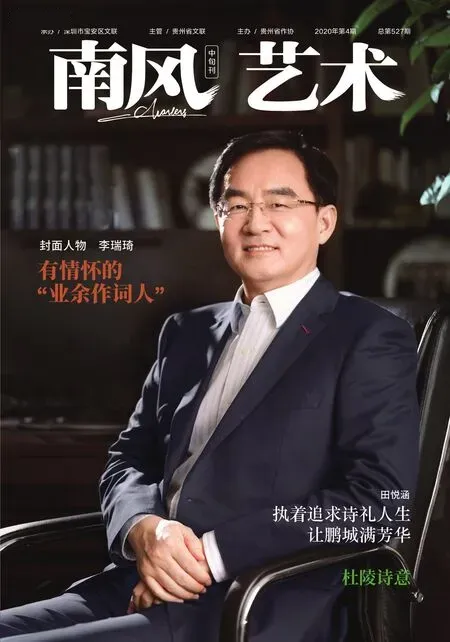清峻綿柔寫春山
——劉維陽山水畫芻議
文/盧向前

劉維陽的攝影很專業,為圈內外稱道。在2003 年12 月的“城市零件”的攝影展中,他的作品《我的父母》,摒棄一切華而不實的形式,以畫面的極其真實性打動了觀眾。在病榻上相依為命的雙親日常生活,通過他的記錄,觀眾好像親臨了事件現場,在片刻間就感受了生命的滄桑。這看起來很容易,實則不然,須知畫面本身的呈現即是作者感動并選擇后的結果。只是樸素的心性一直都流淌在維陽的血液里,一如現實生活并不都驚天動地,并不都那么艷麗,以質樸的方式演繹生活中的每一個瞬間,是他的生活態度,也是他的藝術態度。

豐年祥瑞 2018 34cm×138cm(指畫)
然而攝影只是維陽的愛好之一,準確說是他24 歲以后生活方式之一種。從他出生起就注定與另一種生活方式——書畫生活密切相關。父親劉知白先生是大書畫家,一生筆勤耕不輟,成就卓越。維陽年幼即承蒙父親講授書畫,成人后又常常侍奉父母雙親在側,深受家學熏陶,可謂得天獨厚。他回憶道,父親下放洗馬勞動期間,因鄉鄰照顧,父親仍有機會提起畫筆,老人就曾帶著年幼的他,立于風雨之中觀察山水晦明變化。現在也還保存有劉知白先生不少課子畫稿。筆者見過維陽13 歲時近四尺山水畫作,全用家法,筆致綿密松動,意境清靈恬淡,實在難以想像乃是一少年所為。畫上并有其父題云:“幾重煙樹幾重山,云影朝朝筆底還。喜得阿兒初解趣,試將赭綠寫蒼顏。(丙辰十二月中浣十一維陽畫 如蓮老人題于筑市 ”。)知白先生去世后,維陽又一直參與父親藝術及生平事跡整理發揚工作,其實是重新認識父親藝術價值的過程,也是再次學習父親卓越藝術的過程。
維陽喜歡上了攝影,有20 余年竟然很少提筆繪畫,其中緣由讓人難以理解。筆者揣度其天性中定然有一絲不羈,青春年少的他就像一匹野馬一樣,要去他所向往的天地馳騁一番。哪怕只凝眸到一片悠悠白云,何嘗沒有收獲!帶著相機上路,不管是旅行,還是為了生存,觀山玩水,閱讀塵世,品味歲月,在不經意間就完成了古人所云行路萬里的課業。某年到昆明,得知有一代大家擔當作品展出,他即不辭旅途勞頓前往一觀,且流連再三。以這樣的閱歷,繪畫技法可能一時荒疏,但于繪畫精神氣韻必定有增。
重拾畫筆,腕下指尖,心隨筆動,幽幽墨香襲來,人到中年的維陽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時光。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不必都需要體現高漲的情緒,但對于他所衷愛的藝術,還是需要激情作動力的。維陽從來不缺乏激情,就像他的朋友所說“充滿激情的人卻能穩靜端方,清空無塵”(清一)。因心性的成熟而把激情淡淡地流露,褪去了狂躁與不安——如果要看他激情四射,就要在酒桌上,那種豪飲不是我輩所能勝任的喲!
他的山水畫有清峻綿柔之氣,惹人喜歡。清者,清遠也;峻者,峻潔、崇高也;綿柔者,綿遠和順,不激不厲也。維陽秉性耿介,不尚巧飾,時見俠骨柔腸,然而每每低調行事。他的畫也如此,于峻拔之中蘊涵清朗腴潤之氣,此類作品,構圖迂徐盤桓,多以粗筆折帶皴法勾勒山石,以細筆蘆草、松竹、流水點綴其間;或者以披麻、米點皴法或渲染之法構形,這類作品于綿柔之中隱含錚錚氣骨,有如打太極,一團和氣,自有雄風隱隱而生。

劉維陽
字恒之,號怡堂、樂山,山水畫大師劉知白之十一子。安徽鳳陽人,1963 年生于貴陽。現供職于貴陽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喜攝影,擅山水。自幼秉承家學,隨父習畫,多年來在傳統山水畫的審美境界與藝術語言方面探索不輟。其畫作氣息古雅,筆墨老辣,手法靈動,意境古雅清遠。近年傾力指畫山水,甲肉并施,指擬筆意,既具有傳統山水畫的文化內涵,又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
其手段當然主要源自家法。父親劉知白先生山水畫上承宋元,下及明清,但影響先生一生最大的還是二米、石濤與黃賓虹。二米創米氏云山,有潑墨山水存世;石濤宣言:“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在繪畫中強調主觀能動性,一掃前人程式化的一味摹古風氣;黃賓虹窮畢生精力于理論與實踐創“五筆七墨法”,將筆墨的獨立審美價值發揮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劉知白先生學習三家,并不作一般意義的融合,命運給他安排了“洗馬寫生”以效法自然的經歷,退休后且能有閑更有膽魄作各種形式的嘗試、探索,最終成就了同樣前無古人的大潑墨山水畫法。維陽幾乎見證了父親繪畫由繼承到創新變法的各個時期。運用到維陽自己的繪畫中,在圖式上,他打破了“景在下,山在上,云在中”的兩段式和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的“三疊式”構圖俗套,而是用截取法從中間局部取景,注重協調疏密、欹正、曲折、隱現等關系,圖式多變,立意新穎。這與其說從石濤得法,不如說是他多年旅行與野外工作中攝影取景經驗的潛移默化。在用筆上,他不拘一家一式,勾勒點染隨形而賦,長線短筆,濃淡干濕,自然生發,不以奇怪為能事。他的設色也多變化,有淺絳淡青的,也有賦色極明麗的,筆者認為這很大膽,與時下“主黑”一路山水迥異其趣。但他用色雅致,有清貴之韻,與臟亂、污濁之輩自許為情緒宣泄高下立判。
他的繪畫始終持守著傳統文化的品性,從容嫻雅地敘述著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他喜歡中醫,喜歡道家養生法,逢人便講其中種種妙用,也修禪習佛,以滋養他空靜清和的心性,識者可以從他的繪畫一望便知他對于傳統的尊崇。他的繪畫語言看起來很“舊”,但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用摶和的方法取法前賢,比如他喜歡黃賓虹,卻只取洽合他脾性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亦古亦新。我輩所在的時代,每視傳統為“陳舊”“過時”,其實傳統是一條“不舍晝夜”而流動的大河,割裂傳統、臆想自造無疑是十分淺薄的,歷史已然有慘痛教訓為鑒。有朋友問維陽:
“你的畫很傳統,為什么不加一點新的東西呢?”
“加哪樣呢?新的東西是加出來的嗎?”他反問。
是的,中國畫要真正能夠發展,還得走進我們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去找尋出路,黃賓虹、劉知白的意義就在于中國畫可以由其內部的強大發出生生不息的力量。維陽尊重傳統并不是固步自封,尊重他的父親并不唯上是從。

前面談到過他的秉性里有俠義精神,此處且揭他一回老底:他少時極頑皮,見他人欺侮弱小,就好打抱不平,將人打得頭破血流,鄰居上門,溫和的劉老先生也只能以畫解氣,有題畫語為證:“十一子維陽氣我,氣發之筆墨,即寫是圖為快,不知氣飄何處矣。如蓮老人記,以待癡兒他年笑之若何。”“癡兒”如今已中年,隨著歲月的磨礪,年少的頑皮早已如云淡風清般化作紙上清峻綿柔的筆墨,以其對藝術的明了,傳統性的繪畫語言只是他暫時援引的“工具”,由心而發,畫出他山水的“這一個”一直是他在做、將來還要做的;而“工具”的更新只有不斷地摶和熔冶,并沒有時間表。

金筑雅韻圖 2016 66cm×44cm(指畫)

騰云涌煙 2018 44cm×66cm(指畫)

云去云來 2018 44cm×66cm(指畫)

春江月明 2017 68cm×68cm(指畫)

遙知登高處 滿眼菜花黃 2016 66cm×44cm(指畫)